漢學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鉅著《宋徽宗》讀到一半時,我突然想放下不讀。不是因為書寫得不好,恰恰相反,我很久沒有讀過這麼豐沛周詳的歷史傳記了,只是當史稱奇恥大辱的靖康之難即將發生,歷史的頭上烏雲盤亙之際,我不忍檢點下去。
猶記我最初接觸宋朝悲劇的細節,卻是來自南宋詩人、音樂家汪元量的《增訂湖山類稿》。當中有中國詩歌史上罕見的長篇組詩,是詩人作為隨謝太后為首的南宋降元宗室隊伍裡一位不起眼的「弄臣」,發揮了莎士比亞戲劇裡那些歐洲弄臣的職責:言說歷史,間以俳諧,荒唐言與辛酸淚俱下,發人深省。又多年後,我讀了關於北宋之亡更細緻的《靖康稗史箋證》,尤其當中引古書《甕中人語》記述甚詳,方知崖山之恨,早已在靖康時埋下。
《宋徽宗》固然有恨,但恨之中有愛,有伊沛霞對宋徽宗的愛,因而更寫出宋徽宗對周圍的人的愛——仁者愛人,如此說來,這個一直被目為昏君的藝術家皇帝,竟是中國史上難得的仁君?讀這本書讓人平心而論,宋徽宗起碼絕非昏君——「昏德公」那是毀滅北宋的金國皇帝以羞辱性的賜封來暗示後人的,而後人竟也信之,何故?不就是因為基於儒家偏見:藝術家肯定不善治國,藝術精湛如李後主、宋徽宗者,更是注定的亡國君。
其實按現代人的標準,宋徽宗只不過是一個正常的有錢人,他喜歡收藏藝術品和奇異石頭,喜歡和朋友(他希望他們不只是他的臣下)唱和,喜歡一點虛榮,借道教來安慰自己,善待家族中的女眷和幼輩……按伊沛霞的比較,他沒有比同時代的歐洲君主更為奢侈,也比不上漢唐的君主好大喜功,更談不上他們的殘暴。
宋徽宗半生沒有踏出皇宮禁苑,在金人囚禁他之前,他已被自己崇尚儒家的大臣以奇怪的道德囚禁在他的小世界。正如伊沛霞點出,大臣們更喜歡他作為國家的象徵存在,而不是西方君主或者古代君主那樣遊獵四方認識自己國家的獨立意志個體。於是宋徽宗只好經營他藝術裡那個虛幻而完美的世界,當他被迫面對金人帶來的現實殘酷世界時,他選擇了過分樂觀,假裝一切還會完好如初,因此招致了更大的悲劇。
 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對瓷器、茶學、音律、金石學有所研究,並擅長古琴、蹴鞠、擊鞠、打獵、射箭、馬術、繪畫等,自創「瘦金書」字體。(圖/wiki)
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對瓷器、茶學、音律、金石學有所研究,並擅長古琴、蹴鞠、擊鞠、打獵、射箭、馬術、繪畫等,自創「瘦金書」字體。(圖/wiki)
伊沛霞嘗試讓一個現代人理解一千年前的宋朝,羅列比如國家經濟的收入和支出等等不厭其煩,但同時證明了宋徽宗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親力親為的能幹統治者;就像她強調他的藝術家形象經營,不只是浪漫即興的,而是成竹在胸志在千古的。不過他生不逢時,遼金西夏等強鄰在側虎視眈眈、方腊等民變莫測,他的籌劃能力再好也無法預計什麼是壓倒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宋徽宗》以北宋皇宮的介紹開篇,以北地五國城的流放結尾,顯出了何謂天壤之別。上半卷的國與民越是太平,後半卷他們的命運越是淒慘——最文明的國度引來了最野蠻的入侵者,野蠻感到了落差反而要極盡野蠻,不排除金人的施虐是帶著如此變態的心理,玷污、毀滅美好的事物是魔鬼的快感所在。這時回看書中著墨甚多的徽宗君臣結盟金國的外交努力,可以看到神的冷笑,尤其是他們越努力反而把自己送進地獄,就像在流沙裡的掙扎一樣。
目擊這沉淪需要強大的心臟。伊佩霞關注女性命運,但她也沒忍心像舊時野史那樣逐一檢點那些帝姬的悲慘結局、更遑論被囚禁於所謂「洗衣院」的女奴們的命運。「靖康恥,猶未雪」,對南宋的男子來說,多少是關於自己的女性親人、同胞受辱之恥感,多少是關於亡國失君的呢?宋徽宗的存在彌合了這兩者,伊佩霞寫出在巨大的厄運面前,宋徽宗保持了最基本的尊嚴與文明的超然,雖然對於亡國無濟於事,但在他關注比他更不幸的宋俘、流民之時,他依然是一個「天子」。
《宋徽宗》還有一個特色,乃傳中有傳,令人得見「聖宋」的存在,不只是由宋徽宗的個人魅力獨撐的。比如作者寫及那時重要的建築師李誡,相當於從亂世中鉤沉出另一個勤勉又專注的藝術家,後者何嘗不是宋徽宗想過的另一種人生呢?點出他們相當於在暗黑中留了一個平行宇宙,讓我們回望黑暗的時候不只看見靖康之劫的絕望,也能看到另一個宋朝的切片依然鮮活。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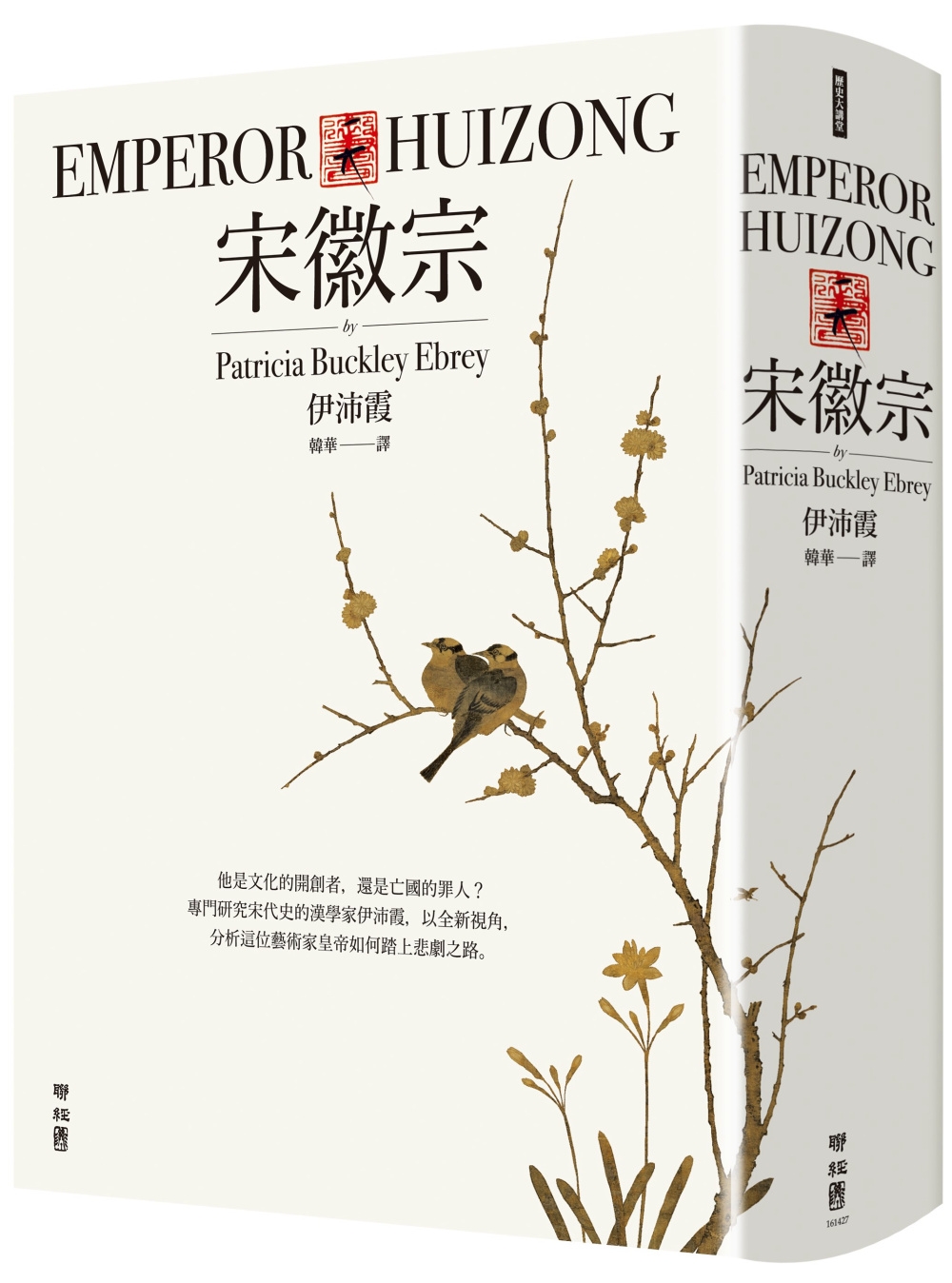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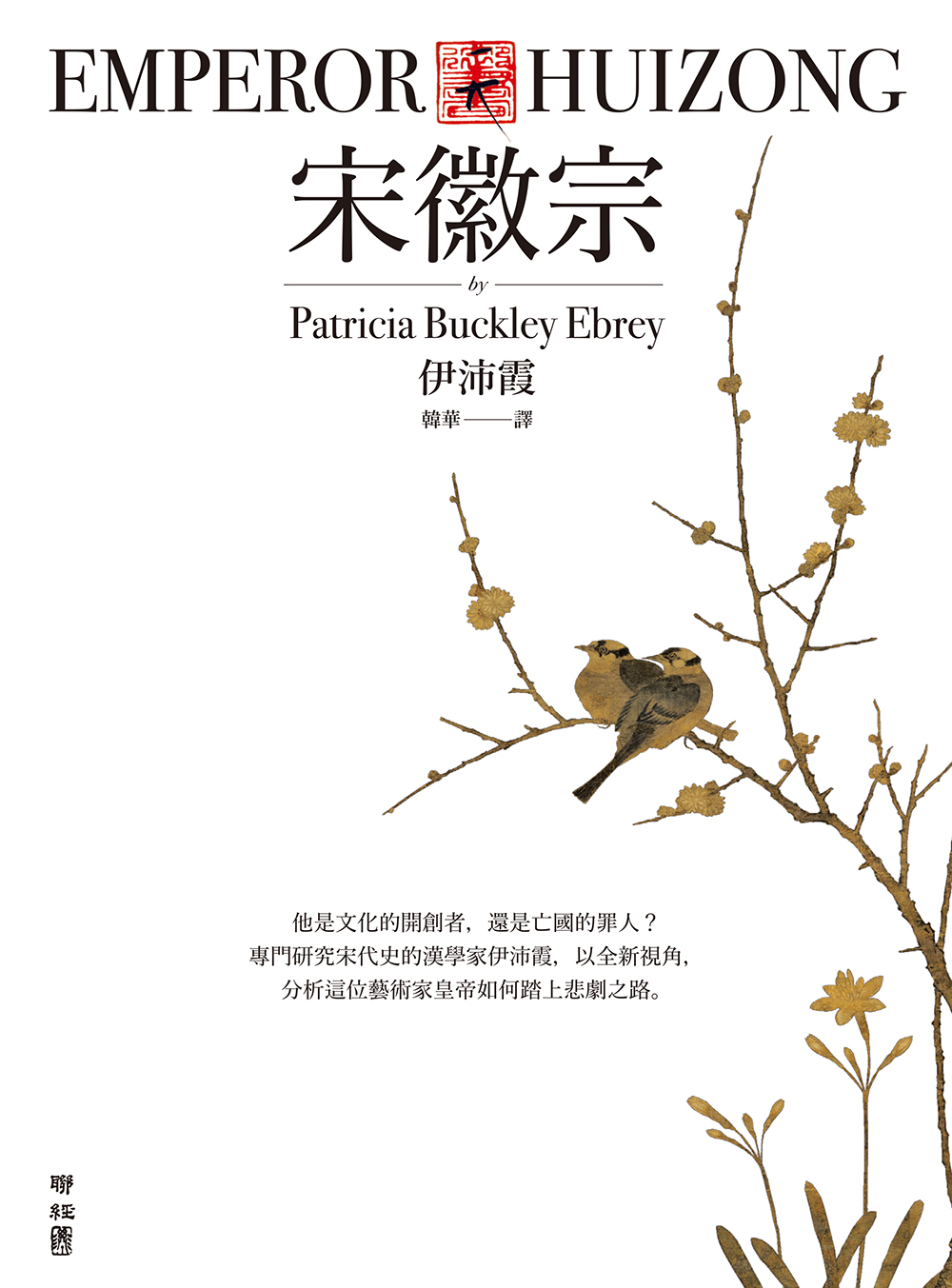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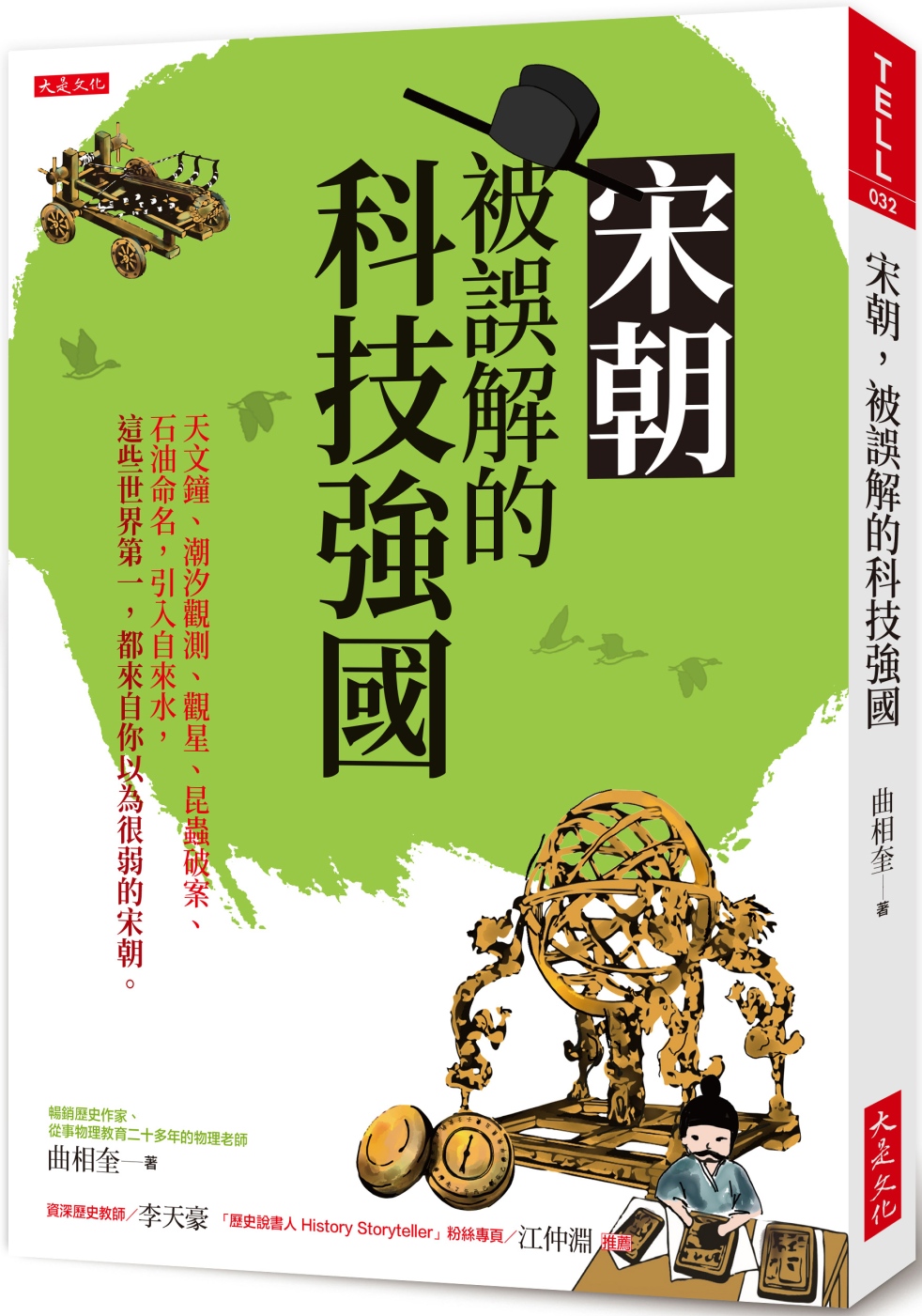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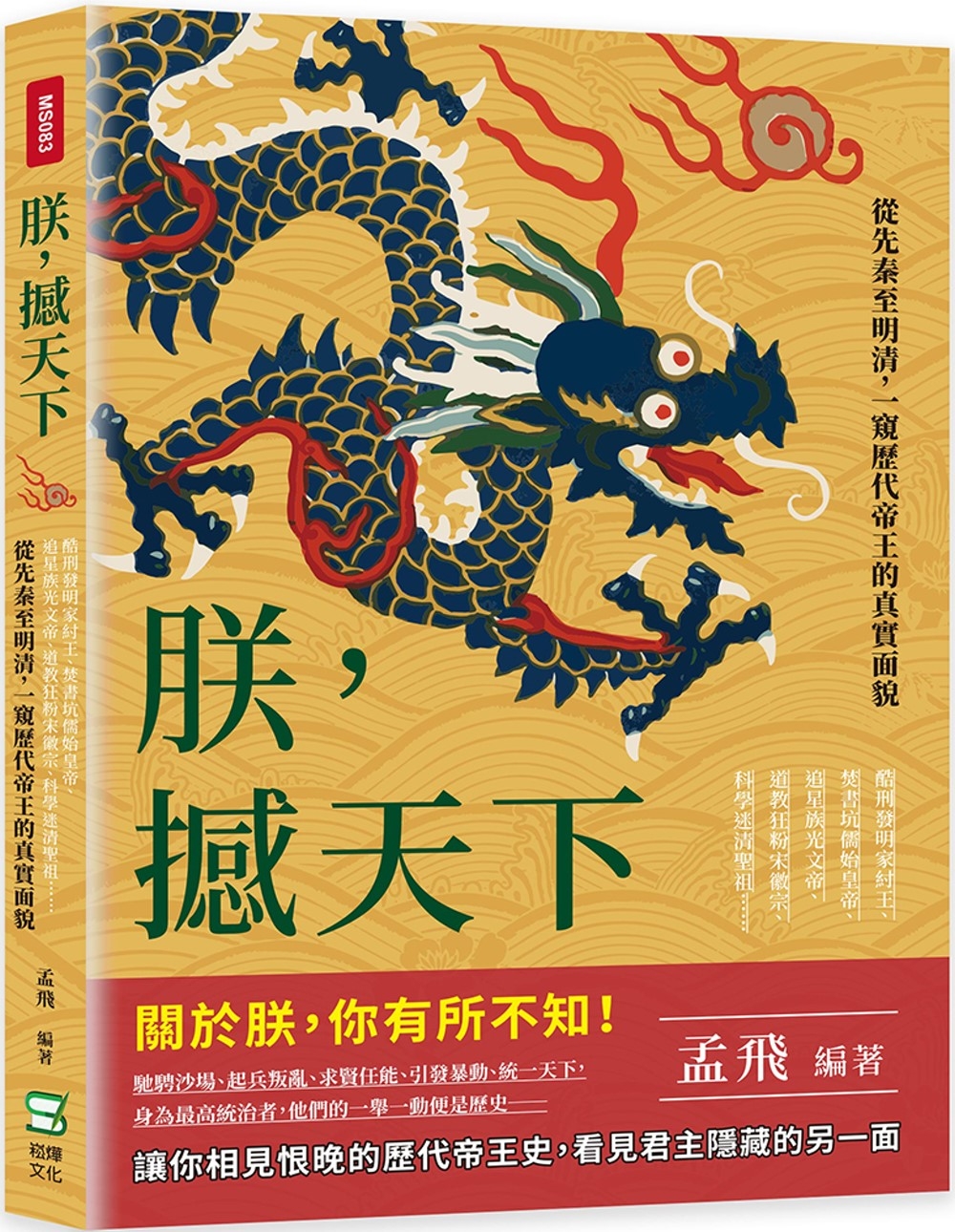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