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是國內同志研究的重鎮,參與的多位學者都以旺盛的學術生產力著稱。其中,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黃道明於2011年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專書《Queer Politics and Sexual Modernity in Taiwan》 (本人將書名暫譯為《在台灣的酷兒政治與性的現代性》,並擅自簡稱為《性現代》)就是讓人拍案叫好的近作。《性現代》除了提及光泰《逃避婚姻的人》之外,重點放在白先勇的《孽子》;此書封面「似曾相識」,原來取自於曹瑞原在2003年推出的《孽子》電視劇劇照。
為了這個OKAPI專欄的調性,我只能把焦點放《性現代》的核心課題上,亦即:男同志和娼妓之間的關係。至於《性現代》對於多種議題的犀利批判──從兩蔣時期對於國民性欲的控管、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對於公娼的壓制、「國家女性主義者」(在扁執政時期,與國家機器合作的女性主義者),到中產階級價值觀等等,很難在OKAPI的篇幅內顧及,只好留待學術場合討論了。
我在OKAPI曾寫過〈同志和娼妓〉,認為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中娼妓常常隱喻了(女、男)同志(如:情欲生活活躍的同志常自比為妓女);不過《性現代》從珍貴的史料下手(我敬佩作者找到許多我找不到的史料),指出台灣歷史中的娼妓跟男同志長久以來是苦命共同體。也因為《性現代》看重娼妓的歷史,所以它在進入《孽子》的討論之前,並不多談《孽子》之前的文本(如白先勇在1960年代初的短篇小說 ),而細究了《孽子》之前的史料(如1950到1980年代的社會新聞)──白先勇的早期短篇小說並沒有將男同志等同於娼妓,可是1950年代的舊剪報卻將同性戀者當作娼妓來報導並加以嘲笑,而當時的警方也以處制妓女的方法來對待當時的同性戀者(當時法令罰了妓女但沒罰男同性戀,但警方用罰妓女的條文來罰男同性戀)。
《性現代》把《孽子》放在娼妓史之內來看(而不是像我或許多文學研究者一樣把《孽子》放在白先勇寫作年表之內來看),是因為它認定《孽子》中的新公園內無家可歸的男同志少年們就是男妓。(也就是說,娼妓並不是這些男孩的隱喻,而是他們的真實身分。)《性現代》指出,《聯合報》在1959年就宣稱台北新公園是「男娼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的前身))在1961年就議論萬華三水街(在龍山寺附近)的男妓──在白先勇小說中,三水街的男孩們就是新公園孽子們的競爭者。《孽子》也白紙黑字寫出這些少年以性交易作為求生的手段。
《性現代》敏銳發現,各界都勸孽子們「從良」,把他們轉變成跟性交易無關的同性戀者──這種態度,呼應了社會規畫娼妓「從良」成為「良家婦女」、藉此端正「善良風俗」的大趨勢。首先,孽子們在《孽子》後半就從良了:他們從賣身場所新公園轉移到可以正當賺錢的小酒館。根據《性現代》,1986年由虞勘平導演的電影《孽子》,為了因應當時新聞局和「各界賢達」對於同性戀的恐懼,不但淨化、簡化了小說原著中的新公園齷齪眾生相,而且把書中的男娼現象全都略而不談。2003年曹瑞源導演的電視版,則將小說詮釋得更加乾淨。(我在這裡插嘴一下:小說開頭的「老工友跟阿青上床」和小說中段「龍子在紐約收容波多黎各少年」,原本各有老少戀、戀童癖等等意味,但這些「不正派的同性戀行為」在電視版中都被淡化到無色無臭。)1990年代同志運動興起,運動者偏愛貢出《孽子》做為同志圖騰,卻又同時否定、拒斥了小說原著中固有的黑暗(環境、內心的黑暗,以及男妓的黑暗行當)──這個運動傾向也是《性現代》所批判的:某一些同志好像從良上進了,但其他不願/不能從良上進的同志和娼妓(或同志兼娼妓),又該如何?
1986年電影版《孽子》主題曲《哦!你也在這裡》
(男聲是主演的孫越,作詞者為陳克華)
曾有好一段時日,評論者讀《孽子》只看見書中的國仇家恨,而看不到書中明寫的同性戀。如今想起那年頭的偏頗讀法,只覺荒唐。但也有好一段時日了,讀者讀《孽子》只看見書中的同性戀,卻看不到書中明寫的同性戀從娼,以及從娼背後整個台灣大環境對於男女娼妓的矛盾心態:既需要她們,卻又滅絕她們。黃道明的英文專著點中了我們的偏頗。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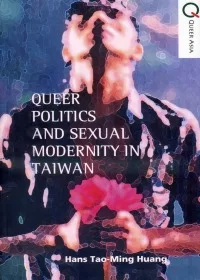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