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被《愛的歷史》(The History of Love)緊緊揪住心臟,捲入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旋風的華語讀者,無論有沒有隨著長篇小說《大宅》(Great House)、《烏有》(Forest Dark),成為死忠克勞斯粉;今年同樣由施清真以優美譯筆翻譯,在夏天推出的短篇小說集《成為一個男人》(To Be a Man),將再一次於我們內心颳起風暴。《華盛頓郵報》形容閱讀這本小說集「感覺像跟一個優秀的朋友聊一整晚」,又盛讚克勞斯的文字具有使人信賴的強度,因為她的作品像是「活過的」。
《成為一個男人》輯錄的十篇小說,創作時間從2002年至2020年,橫跨18年;18年間,卸下妻子角色,恢復獨身的妮可.克勞斯,與她創造的那些既敏感、眼光銳利又在困境中迷惘的角色們,共同經歷關係從激情,至動盪,到破裂的旅程。她們一起「活過的」證據,正是18年間在小說敘事中永遠保持好奇心,直直看進親密關係、身分認同裂毀處,細細為讀者從瓦礫堆中描摹出一條掘墾生命真相的軌跡。
試圖、不敢、生怕、說不定
即使如此,妮可.克勞斯真正為文字注入「使人信賴的強度」的原因,絕非竭力在小說中提供一套解謎公式。她深知小說家的責任不在「給方便」,因此,閱讀《成為一個男人》感到的諸多「不方便」,其實就像吳明益形容《大宅》設下的門檻:「那就是小說彼此聯結的線索如此隱晦,如果漫不經心可能無法將這些線索統整出全貌」。
《成為一個男人》敘事者皆非全知全能,且經常後知後覺,因此讀者必須全神貫注,否則容易錯失克勞斯布下的線索,而短篇小說的形式,使得前述特點更加鮮明。即使如開篇〈瑞士〉(Switzerland)中的「我」,敘事者成年後憶述13歲在瑞士寄宿家庭結交的朋友索拉雅,與中年荷蘭銀行家的危險畸戀,遲來30年的後見之明,也不見得透徹明晰。事實上,克勞斯一開始就已經預告敘事者將帶讀者走進迷霧:
我和索拉雅已經三十年沒有見面。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試圖打聽她的下落。我想我不敢見到她,我生怕年歲漸長的我會想要了解她,說不定甚至看懂了她,換言之,我生怕看懂了我自己,不願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種種。
「試圖」、「不敢」、「生怕」、「說不定」,恐懼橫亙在事發現場與記憶之間,她不斷聲稱自己即使以最間接的方式嘗試靠近索拉雅,也會感到心驚。但「沒有辦法太投入」、「沒有那樣的勇氣」卻又加劇記憶的不穩定性,使得這一場追索注定只能在恐懼的周圍,迂迴、游移。然而,透過敘事者娓娓加添的細節,專注的讀者也能慢慢抵達「隱藏於其後的種種」。如日內瓦街頭陌生歐洲男子悄聲夾帶英語口音對她說:「我一隻手就可以把你折成兩截」;如索拉雅失蹤兩天之後自行返家,一片慌亂騷動中,沉默地經過敘事者身邊,停下來,摸摸她的頭髮,然後非常緩慢地繼續往前走,成為一道謎。正是這些看似不經意埋下的細節,一次又一次摩擦生熱,讓害怕看懂索拉雅,也看懂自己的真相水落石出時,火花四濺:「世間有種遊戲,它攸關權力與恐懼,它不願屈從人們與生俱來的脆弱與善感」。30年來,敘事者逐漸認識到,看似玩得太投入而毀壞的索拉雅,其實不曾被荷蘭銀行家一手折成兩截。因為「要麼她已經折毀,要麼她就是不會。」至於這個遲來的認識為什麼重要?《成為一個男人》創作於不同時期的小說,彷彿都圍繞著這個問題,分進合擊。
推擠過鑰匙洞的胖女人
細究《成為一個男人》的角色,大多是「要麼已經折毀,要麼就是不會」的倖存者,或其後代。雖然以色列特拉維夫對猶太裔妮可.克勞斯創造的人物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一如長篇小說處理猶太歷史的「節制」,她並沒有選擇讓浩劫來到幕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篇短篇小說中,災難都是不容忽視的悠遠襯樂。〈瑞士〉的敘事者,來自猶太大屠殺倖存家族,短暫地來到中立國瑞士德語區,處在是否能繼續與德語絕緣,脫離家族傷痛的境況。索拉雅一家則是從德黑蘭出逃,流亡巴黎,她早早就被連根拔起。敘事者害怕看懂對方,也看懂彼此的伏流呼之欲出。〈愛〉的敘事者與蘇菲重逢在難民營,回憶的卻是帕索里尼、《E.T.外星人》以及「與誰墜入情網,與誰廝守終生」的問題。〈翁婿〉則是分處紐約、以色列特拉維夫的一家人,為是否接納突然被政府帶來的匈牙利猶太老人發生爭執。〈成為一個男人〉用一種令人不忍直視的詼諧,讓猶太倖存者後代與德國拳擊手、以色列特種兵在親密關係中談論人的暴力如何生成。
妮可.克勞斯的小說似乎擅長顧左右而言他。記者曾經問她構思小說是否考慮反猶太主義的問題,她回應,小說本質應該是使人更密切地了解個人生活。《成為一個男人》當然犀利地觸碰美國、歐洲猶太社群與流亡者內/外部問題,也敢於對以巴關係、猶太復國主義提問。但我認為,妮可.克勞斯小說可貴之處,在於她始終關注的不是此前已然發生的巨幅浩劫史,更多是歷史災難如何一點一滴滲透進個人生活,致使倖存者「未來劫難難逃」?因此,她的人物總是「在他方生活」,流浪並不為追尋青春反叛的靈魂。他們總是在離開,用非母語交談真正重要的事,總是在戀愛,做愛,分手,然後哀悼,「思緒只會遊走於哀傷的邊際,而不會被深深捲入」,與人發生關係,亦近乎「無意做出任何補償,也不想從中得到什麼」。
正因為小說探究的是「成為一個○○」,to be,正在發生,尚未有定論;重大事件的決定性轉折,毫無來由地,經常只是卡在輪底的一隻雞(〈成為一個男人〉)。身體與身體,國家與個人,命運與災禍之間的摩擦力永遠不會停歇。就像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大疫之年讀起來彷彿是預言的〈來日的急難〉中,長居紐約的法國移民維克「拒絕接受一個規避衝突且迫使人人趨近平庸的體系,就好像硬要把一個胖女人推擠過鑰匙孔」。有些角色正擠過鑰匙孔,有些角色正透過孔洞觀望,無論如何,目睹一場艱難的穿行,都讓這份理解的努力變得不可能舒適。
克勞斯在訪談中形容自己十幾年來,始終在寫充滿力量與智力的女性聲音,而這些女性角色「毫無歉意」,卻也能引發讀者共感。《成為一個男人》裡的女性聲音不吝於展現機趣,但並不總是討喜可親。如此一來,「毫無歉意」又能引起共感,恰恰是《成為一個男人》最令人驚異之處。這麼多年過去,閱讀妮可.克勞斯的小說,確實還是感覺與一個睿智的朋友,膝蓋抵著膝蓋聊一整晚。這位朋友會擾動你,挑戰你;而最終,你會感謝擁有這樣的夜晚。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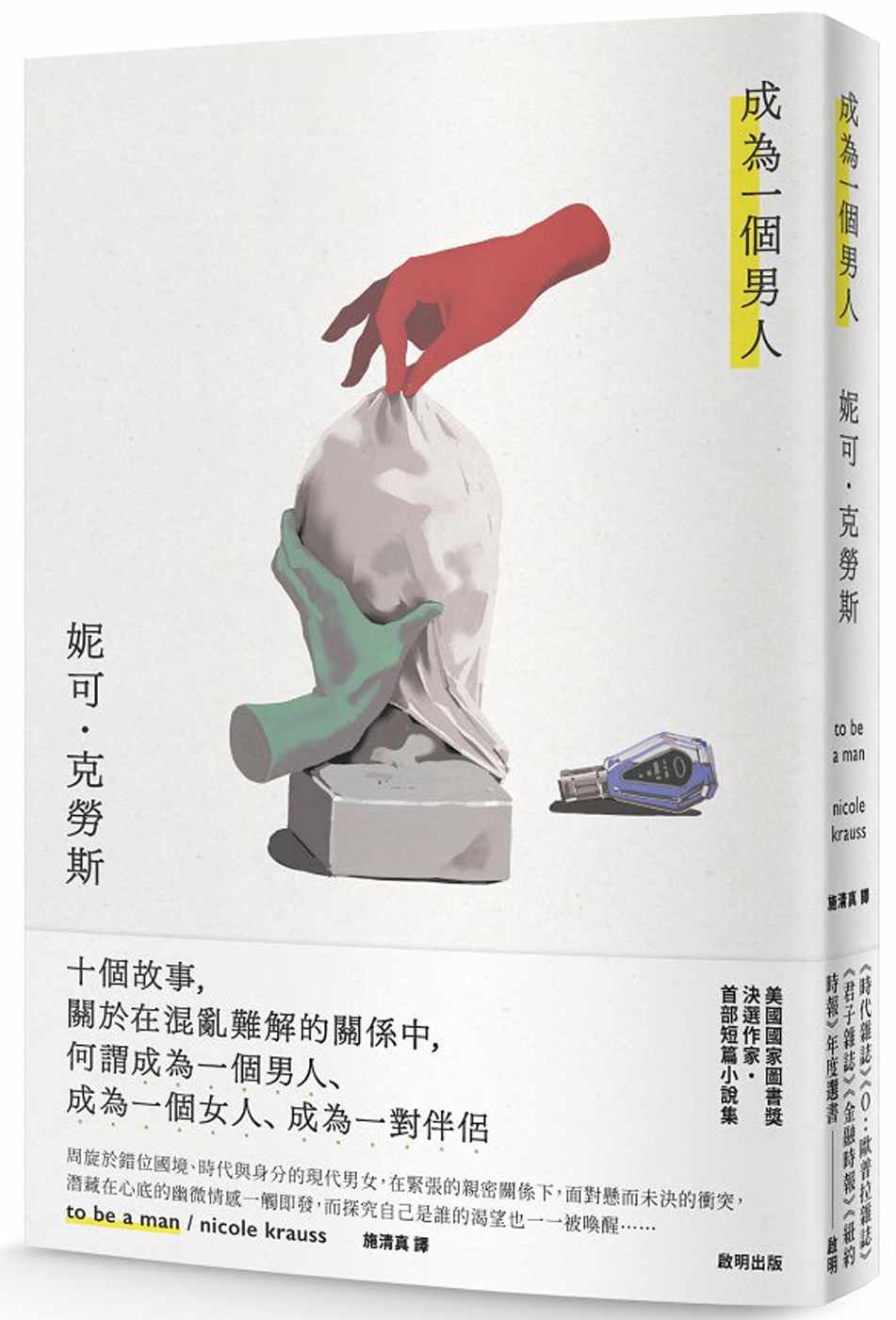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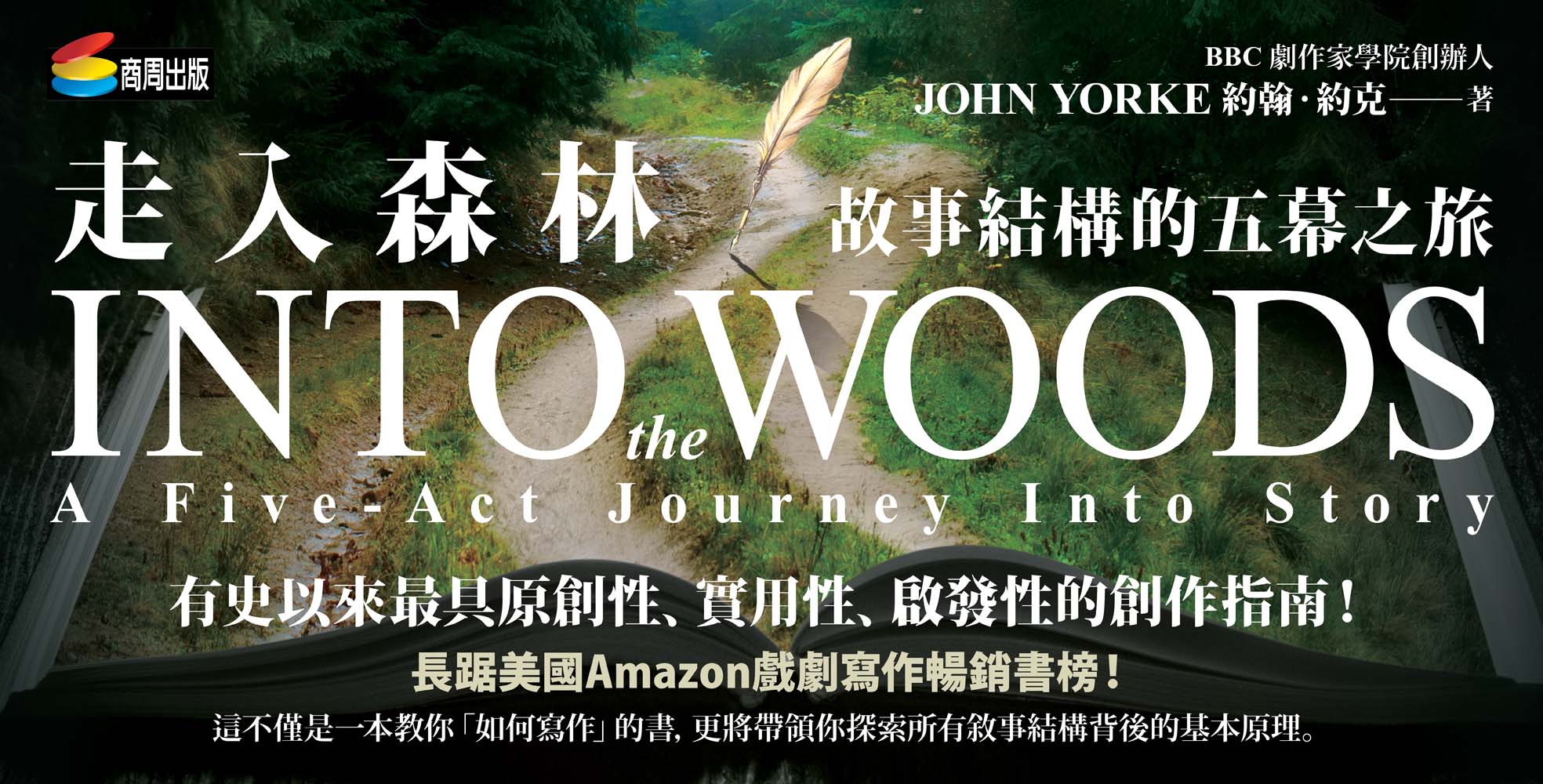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