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培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留下的獄中手稿寫著:
再見,我所關心的一切——你們記憶著我,我也永遠懷念著你們。
然而這份記憶在長久的沉默後可以延續多久呢?除了最親密的人之外,他的朋友、鄰居、親戚在緊繃的戒嚴氣氛之下,是否自行過濾、刪除了關於一位懷有理想的青年的記憶?或者該問,沒有了記憶,歷史還能夠存在嗎?
這些,都沒有信手捻來的答案。
《無法送達的遺書》第一次出版是在二○一五年,七年後重出增訂版,新增一百多頁的篇幅。在編輯的過程中常想,這一百多頁重重的紙,是後人重新發現了歷史,或是沉默的記憶原來就佇立在那?
林傳凱老師寫完新收錄的、關於王文培與王大銘父子的故事〈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後,我們仍舊聯繫不上王文培的家人。做為一個研究者,老師可以就他的專業和歷史考據,以現代學術自由之名發表研究。不過,編輯小組(包含主編胡淑雯、研究者林傳凱、春山總編輯小瑞和做為責編的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務必細緻小心、不要造成善意的傷害,即便所謂「政治犯家屬」的樣貌多元、對自己家人所發生的政治苦難理解也不一,但我們還是認為在不過度打擾家屬的情況下,應該要親自表達出版《遺書》的初衷——這不是一本收集故事並以故事來達到某個政治目的的書,而是謙卑思考歷史、反省歧異,並期盼記憶得以有機延續的書。
一個關於記憶/故事的線頭冒出來了,寫作者/研究者的興奮之情可想而知,甚至作為一位編輯,也有欲望將動人的故事收納進書裡,濫情容易收斂難,儘管初衷是帶著善意,仍然必須小心翼翼,不要造成消費。
後來,記憶回來找我們了。
透過各路親友的協助,我們與王文培高齡八十多歲的妹妹一家聯繫上了,她是王文培僅存於世的手足,也是王大銘最年幼的女兒。原本希望低調的妹妹家讀了傳凱老師的文章後,竟整理一疊遠自七十年前的文書與照片,慷慨且無保留地出借。我們帶著虔敬的心情請專業人士掃描、數位化,並由設計王小美將部分影印文件「還原」成當時的色彩,於是有了讀者現在可於《遺書》第252-263頁所見的珍貴圖頁,包含:王文培幼年期的全家福、出遊照、畢業照、獄中手稿、王大銘給女兒的信,以及使人不忍直視的掩埋證書。
 王文培照片(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照片(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槍決前手稿與給母親的信。(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槍決前手稿與給母親的信。(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後來,我們帶著甫印製完成的書去拜訪王文培的外甥女黃小姐。記憶似乎以我們無法預期的方式蔓生著。
黃小姐說:「爸爸打電話來告訴我舅舅的事,我才漸漸把以前的一些事串起來。」黃小姐自小與外婆(王文培母親)住在一起,外婆總是打扮得整齊潔淨,茹素念佛,從不與鄰居說三道四,出門只去菜堂及市場,與外界始終保持著不易受傷害的距離。幼年頑皮的黃小姐有天在菜櫥中發現一只刻著「王文培」的印章,心想「家裡沒這個人啊」,好奇問母親,卻被母親驚慌失措並且責備似的臉孔嚇著了,從此不敢再過問。「我從來沒看過媽媽有這樣的表情,所以到現在還記得。」
直至我們拜訪當天,也過了幾十年,「爸爸告訴我這些事情,讓我記得,現在我知道自己家族的事,也想告訴我的孩子。」黃小姐這樣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許攪動了深潭裡的記憶,它慢慢浮上水面,與蹲在潭邊的我們相視,也許它會長出草、生出葉,或許也會成為新生記憶與行動的滋養之處。
龜山曹家
《遺書》新收錄的文章還有〈白色畫廊——一九五○年代的遺書群像〉,林傳凱老師分析31封政治犯的遺書,其中之一是曹賜讓留下來的文字。
爸媽:我為了愛您們為了愛兄妹為了愛天下人,此刻我的心已亂極了。我要說的話也多透了,可是我再也無法往下寫了。就讓我們在此絕談了吧!敬祝爸媽身體健康。
兒賜讓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僅寫
 曹賜讓遺書。(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曹賜讓遺書。(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二○二二年,距離曹賜讓絕談七十年後,我們帶者甫出版的書來到年近百歲的曹耀東先生家。
他的咬字吃力,但記憶仍非常清楚。不只談起被槍斃的弟弟,也談起那個時代。
他巍巍顫顫地起身,踱步到房裡。櫃子裡收著一、二十本相冊,抽出其中幾本,翻來整整齊齊依照時序貼著相片,一旁還有文字說明,一九三○至一九四○的曹家子弟求學時期影像就這麼展現在我們的眼前。一張學校宿社照片的上方頑皮地寫著:「地獄一丁目 舍監室」。再翻幾頁,一張十六名學生的團體照,上方寫著:「一九四四.十 謝傳祖、吳邦基兩君特幹送行紀念」曹老先生說,謝傳祖也被槍斃掉了……
當下我突然反省到,我們並不只在拜訪「政治犯家屬」,曹耀東先生本就是一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遺書》成書時,編輯小組就有意識,這不僅是關於政治犯的書,也是以家屬為主體的書。然而當我有幸親自拜訪「家屬」,才更深刻體認時代中個別主體的重量。
又如後來去拜訪曹賜讓的妹妹曹素雲女士,她身體硬朗,頭腦清晰,於抄經本上勤勉的字跡秀麗大方。曹賜讓被關押期間,家中男性深怕再被牽連,所以都是還在上學的素雲女士每個星期送食物、物品到看守所給哥哥,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年多,直到哥哥被奪去生命。
她還提到二二八當天老師讓他們提早下課去搭火車,場面混亂,有人甚至爬上火車頂,於慌亂中被來去驅趕,終於在晚間九點回到龜山老家,若有差池,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個經驗似乎也揭示著,每一個在時代裡的人都有可能「正巧」遇上劫難,而這些偶然性也正正形塑了時代的「必然」,人與時代往復交錯前進著。
曹賜讓留下來的文字、曹耀東先生與曹素雲女士的回憶,都是無比珍貴的時代記憶——當然我們也承認,記憶有錯置、模糊、尚須核對的可能性——例如曹素雲女士說十年前左右各手足皆拿到遺書影本;但曹耀東先生則說,在我們帶著書到訪之時,他才第一次看到弟弟寫的遺書……。縱然我們惋惜於曹賜讓「再也無法往下寫了」,但也無法保證接著寫下去還有什麼,歷史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七年前《遺書》甫出版時,小瑞寫到這是「一份艱困的歷史作業」;七年後我們有幸碰上回來找我們的記憶,也繼續這份未完的作業。
莊舒晴
春山出版編輯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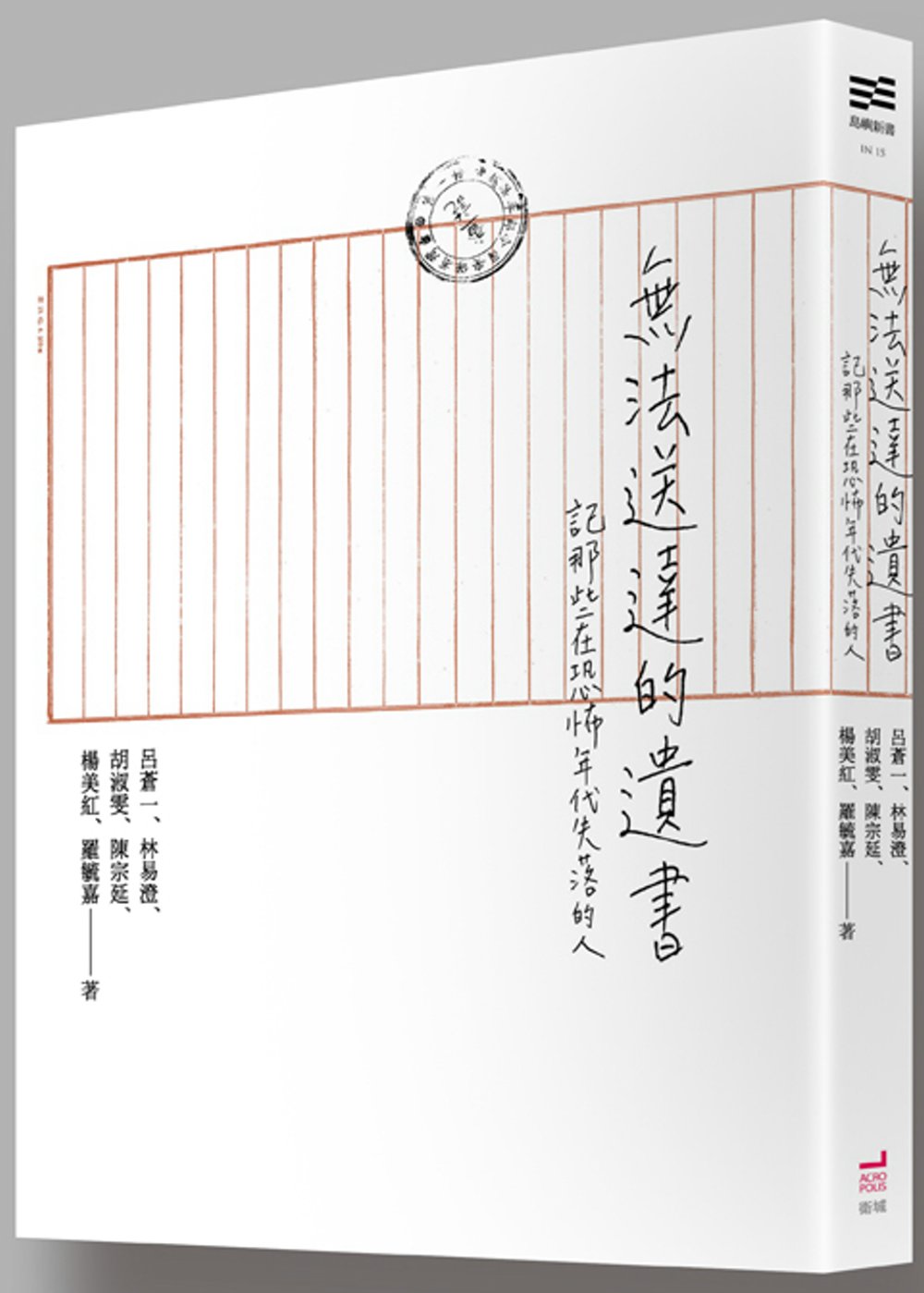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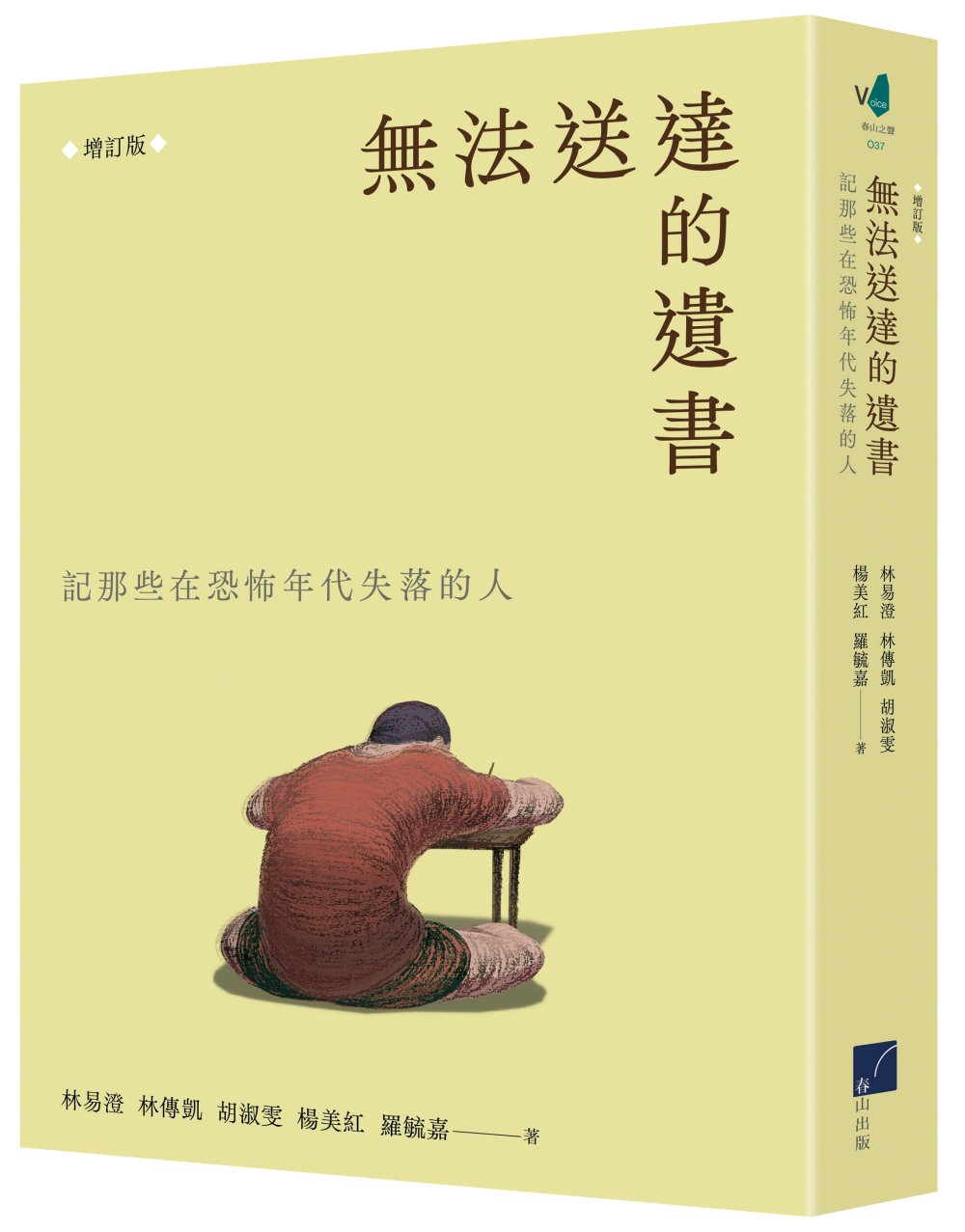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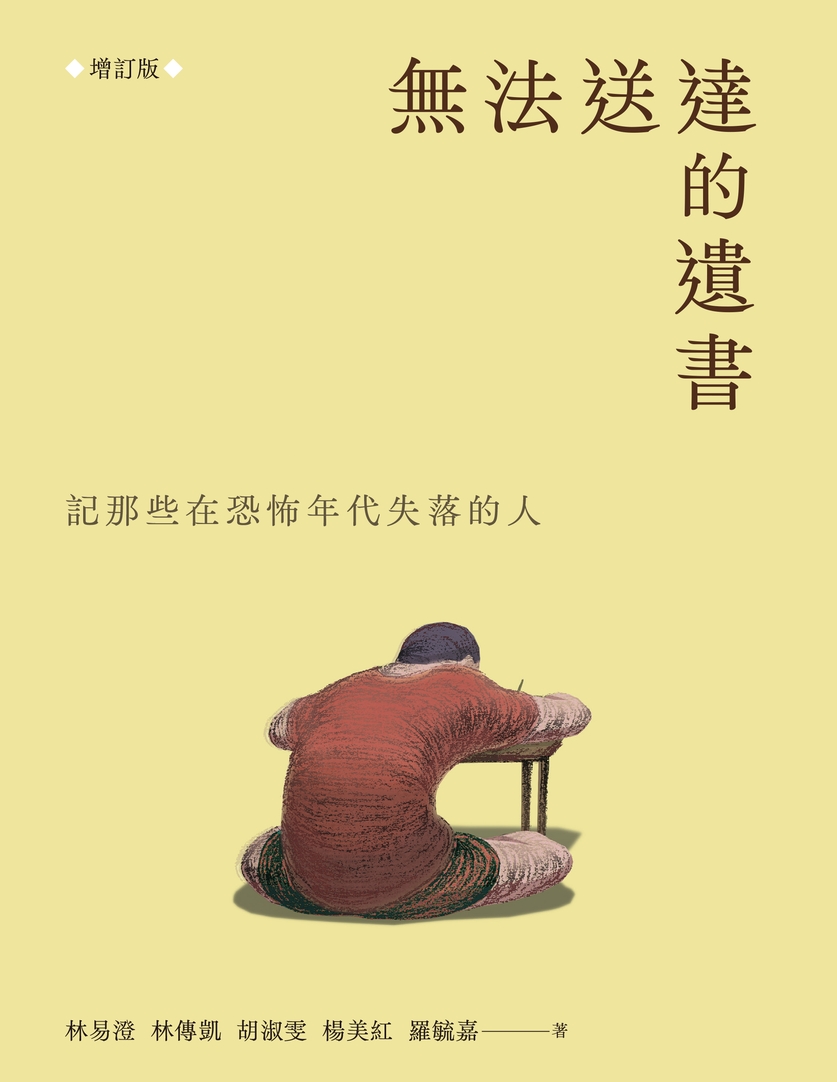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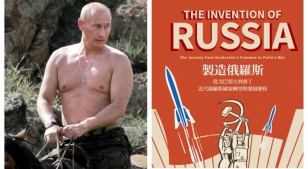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