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算牠沒有臉》是黃宗慧與黃宗潔聯手對寫的新書,是一本談動保的書,但剛開始我不太懂這個書名。沒有臉?誰沒有臉?沒有臉是什麼意思?後來我才明白書中的「臉」指的是──你是否「認識」這隻動物?你是否看過牠的眼睛?是否與牠建立了連結?人們容易對自己認為「有臉」的動物寄予情感,而對「沒臉」的動物則可以煮牠吃牠弄死牠。但如果動保是愛護動物關心動物,那麼對於有臉/沒臉的差別待遇豈不矛盾?
可是,「我」就是會對某隻動物有某些特別的情感不行嗎?「差別待遇」難道就是偽善嗎?
黃宗慧與黃宗潔不僅討論了有臉沒臉的動物,也討論了「可愛動物」與「厭惡動物」,「食用動物」與「寵物動物」。他們的對談非常吸引我──因為我也經常陷入這樣的矛盾,而且是自己也不明白的矛盾。
看見眼睛了,然後……
有沒有臉,我第一個想到的是「眼睛」。一旦看到眼睛,就不行了。我想起兩年前的一隻八哥。家裡的庭院突然很吵,八哥叫叫叫叫;八哥叫並不奇怪,但那天聲音特別大。我走到院子,發現我們家的貓正準備撲向一隻八哥,那隻八哥已經受傷,一跛一跛跌進草叢。家裡的貓是放養,是自來貓,平日會捕鳥追蜥蜴捉老鼠一點都不稀奇。那麼,那天我為何出手?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樹梢那些呱叫的八哥「聽起來」像是要救援牠的同伴,而更可能是──我望向那隻受傷的八哥時,我看到了牠的「眼睛」。看到眼睛,那眼睛就像在跟我說話,儘管牠什麼也沒說,卻讓我感受到牠的脆弱、需要幫助──儘管,我根本不曉得對一隻受傷的八哥該怎麼做。伴侶Y覺得八哥很吵,數量太多,會啄我們家的木瓜,又是外來種,「給貓咪當食物剛好。」Y說。但是,我還是用毛巾包起了牠,我看著牠的眼睛,牠的眼睛好亮。
我摸著牠的身體,感覺著軟軟的牠。這時的牠,跟平常的八哥不同。牠安靜的躺著,過了一會牠張嘴像是無聲的叫,而後扭動脖子,動了幾下,不動了。
Y問現在怎麼辦?要給貓咪當食物嗎?我說,已經不能當貓咪的食物了。
 已經看到八哥的眼睛,還要給貓咪當食物嗎?(圖/廖瞇提供)
已經看到八哥的眼睛,還要給貓咪當食物嗎?(圖/廖瞇提供)
我看到了這隻八哥的眼睛,於是無法讓牠成為貓咪的食物。可是,我們也曾經看過一隻山羌的眼睛,我還摸了牠的頭,但最後牠成了我們的食物。
剛搬來鹿野的某天晚上,我們聽見山羌叫。我們住的地方聽見山羌叫,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但對剛搬來的我來說很特別。那天我們聽見山羌,叫聲急促且連續,Y說跟他之前聽到的不太一樣。隔天早上,又聽到一樣的叫聲,「好像是同一隻,」Y說。
Y循著叫聲去找,在山谷邊發現一隻被捕獸夾夾住的山羌。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山羌,像小鹿,我覺得非常可愛。但這隻我認為很可愛的動物,是獵人的獵物。那隻山羌的腳被捕獸夾夾住,而令牠致命的是山裡的野狗。Y說他發現那隻山羌時,野狗正在攻擊牠。Y揮棒把野狗趕走,但山羌已經失血過多。
山羌的屁股和肚子都是傷口,牠不斷流血,卻仍然睜著亮亮的眼睛。亮亮的眼睛,臨死前的眼睛為什麼都那麼亮?Y找來扁平的石頭,撬開了捕獸夾。我摸著山羌的眉心,不曉得該怎麼辦。我摸著牠的眉心,跟牠說不要怕。我和Y在山谷陪牠,一邊陪一邊煩惱,如果牠沒有死那我們該怎麼辦?如果牠死了我們該怎麼辦?
最後那隻山羌死了。Y打了電話給部落的朋友,說了經過,山羌現在死了,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部落的朋友說:「我處理,我來處理。」那時候我不曉得「處理」是什麼意思。到了晚上,我們接到電話,朋友說可以來晚餐了。
部落朋友煮了三杯,還有一鍋湯。我們猶豫著要不要吃,因為我已經看到山羌的眼睛了。但部落的朋友難道沒有看過自己獵物的眼睛嗎?他們當然看過,也理所當然的煮食。對他們來說,山羌是食物,在山羌死前他們也曾看過牠的眼睛,那在我眼裡是可愛動物的眼睛。
「你不吃,牠也是變成肉。」部落朋友夾了一塊肉給我。我猶豫著,最後放進嘴裡。因為我想知道我吃的時候,我在咀嚼的時候,心裡的感覺會是什麼。
這樣為什麼還要救牠?
這兩段經驗,都是出手援救瀕死的動物。現在的我回想,為什麼我要救牠們?牠就快死了,就算救了也是會死。而且八哥是外來種,有人認為不僅不該救,甚至該想辦法減少牠們的數量;而山羌是許多部落獵人的獵物。讓八哥成為貓咪的食物,讓山羌成為獵人的獵物,難道不好嗎?
沒有不好,我不反對。儘管也有人認為貓咪是馴化動物,不是野生動物,牠捕捉獵物不為了吃飽,所以應該管束貓咪在外的獵捕行為。但我自己不會特別去約束自來貓的行為,因為自來貓就是生活在社區裡,牠用牠的方式想辦法活著。牠們來到我家討食,住久了與們建立了關係,雖然建立了關係但我不覺得自己可以約束牠的行為,也做不到。那麼,我為什麼出手?
之前我也曾經困惑,覺得自己這樣做很沒意義。既然我不反對貓咪獵捕,那為什麼要出手,而且是一隻已經受傷的鳥──反正都受傷了,也活不久,就讓牠成為食物不行嗎?沒有不行,仔細想,是不忍心。就是因為受傷了,就是因為看見了。如果我發現的時候八哥已經只剩羽毛,我可能不會有感覺,可能還覺得貓咪好厲害。但我又想,我看到受傷八哥的眼睛就「不忍心」,是不是偽善?──那如果是老鼠呢?如果是一隻咬在貓咪口中的老鼠?沒死還會吱吱叫,我會救牠嗎?
從前我也曾經困惑自己的矛盾,認為自己標準不一,但後來我讀黃宗慧的《以動物為鏡》,其中引用了學者錢永祥對動保的看法,我才意識到「半調子」是成為行動者的可能──
「我有時驚悚的意識到,人性之惡如此明顯深刻,我整天卻假定人們相互可以為善,是不是有點荒唐、有點鴕鳥?可是如果我不理想主義一點,則虛無與犬儒進襲,我豈會覺得還有任何可為之事?那樣子癱瘓的情況,又有利於誰?所以,一個人可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我自己則取法其下,希望可以容許更多的人為惡之餘順便做點善事。在這個意義上,量化素食主義者、友善農業、人道屠宰,都有點意義的。『半調子』必有其然,行動者必定半調子。只要有個半調子,這世界就還有一點理想主義的可能。」
回來說那隻山羌。
不忍心,也是我們援救山羌的點。儘管知道牠最終可能會死,但因為我們看見痛苦了,所以不得不。那麼我會反對獵人獵捕嗎?也不會。那麼,看到山羌的痛苦卻也不反對獵人獵捕的我,能做什麼?原本的我不曉得能做什麼,但當我再回想黃宗慧黃宗潔在《就算牠沒有臉》中的討論,她們認為先覺察,才有在乎、回應的可能。
我想,能倡議的或許是,不要使用捕獸夾。
獵人若為生活或文化獵捕,重點是取其命,而非增加動物痛苦。捕獸夾給動物的痛苦太多了──「幸運的」可以掙脫,但是斷掌或斷腿;「不幸的」就是漫長的痛苦,那痛苦只能等到獵人來「收穫」才能解除,或是被其他動物攻擊而死才能解除。獵人若為取其命,就一對一對決。捕獸夾徒增動物痛苦,也增加捕捉到預期之外動物的可能,比如與人類一同上山的狗。
不只對有臉的動物矛盾,對沒臉的動物也矛盾
從前我為自己的矛盾感到困惑,像是身為外來種的八哥就不該救嗎?被視為食用動物的山羌就不能救嗎?或是就算救了還是會死的動物那麼該救嗎?後來我覺得,每個人對動物不同的理解與關係,無法得出標準答案,而我能做的是看見「當下的自己」與「對方」所建立的關係來做判斷。
這篇邀稿原本的字數是一千五百字,我卻寫了三千多字,而且還沒寫完。讀《就算牠沒有臉》,就是會讓我忍不住想很多──因為除了對有臉的、有眼睛的動物所產生的矛盾,我面對沒臉的也產生矛盾。你覺得毛毛蟲有臉嗎?毛毛蟲雖然看起來沒臉,但牠如果跟我沒有利害關係,我也不需要去弄牠。可是當我們家種菜,比如菜園裡白蘿蔔葉子上的紋白蝶幼蟲,那一隻一隻軟軟的生命體,量多到你不覺得牠是生命,只覺得牠在殘害你種的菜,在把你的蘿蔔弄死,導致我們不得不在牠弄死蘿蔔或我弄死牠之間抉擇。
但真的只有你死牠活(蟲死菜活)的抉擇嗎?在讀《就算牠沒有臉》時,我讀到的不是怎麼做才對,而是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比如當我弄死毛毛蟲時我感覺到牠身體的軟,我不敢直接用手弄死牠而是用樹枝戳牠,但儘管如此那觸感仍舊會從樹枝傳上來,傳到我的手指再傳到我的心,我至今仍舊無法沒有感覺。
「無法沒有感覺」──這或許是能再多做點什麼的開始。
我看不到毛毛蟲的臉,毛毛蟲的眼睛,所以我敢弄死牠。但說到眼睛,也不是對上眼睛我們就能善良──Y在田裡抓到啃咬鳳梨的老鼠,在籠子裡。我看到牠的眼睛了,但我根本不敢再看,我假裝沒有看到。因為我知道等一下牠就要死了,而當時的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圖/廖瞇提供)
(圖/廖瞇提供)
但當我這麼寫,當我說自己想不到其他的方法,當我說想不到方法然後又回想當時的情境──我發現我面對的是「你死它活」(鼠死鳳梨活),而不是「你死我活」(鼠死人活)──不是我在跟老鼠爭個死活。無論如何人類都是握有相對權力的那方,握有相對權力,也就擁有選擇的可能。
說是這樣說,說總比做容易,當看到辛苦種的鳳梨又被老鼠啃咬,而且一隻可能喚來一隻,我們是否還願意為老鼠再多想一點?多想一點?多想一點?當我們若願意再多想一點,就算還做不到,至少,我們不至於活得沒有感覺。
作者簡介
大學讀了七年,分別是工業產品設計系與新聞系。
認識「玩詩合作社」後,創作底片詩;認識《衛生紙+》後,持續寫詩。
2015年出版詩集《沒用的東西》。
2019年以《滌這個不正常的人》獲選為台北文學獎年金得主。
認為生命中所有經歷都影響著創作。
現寄居東部,一邊寫作一邊教學。
【OKAPI專訪】「真實的去認識一個人吧,然後,再多知道一些。」──專訪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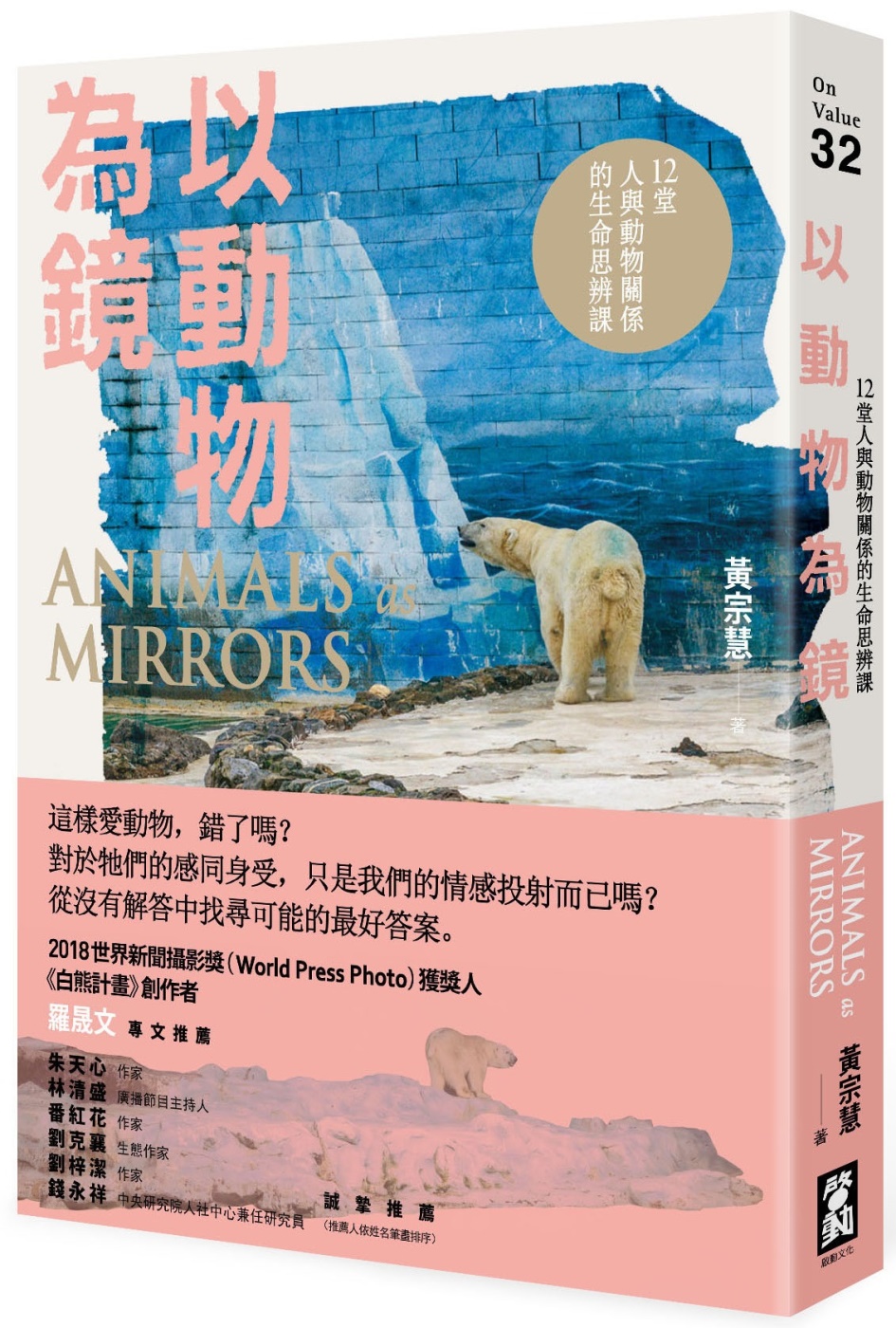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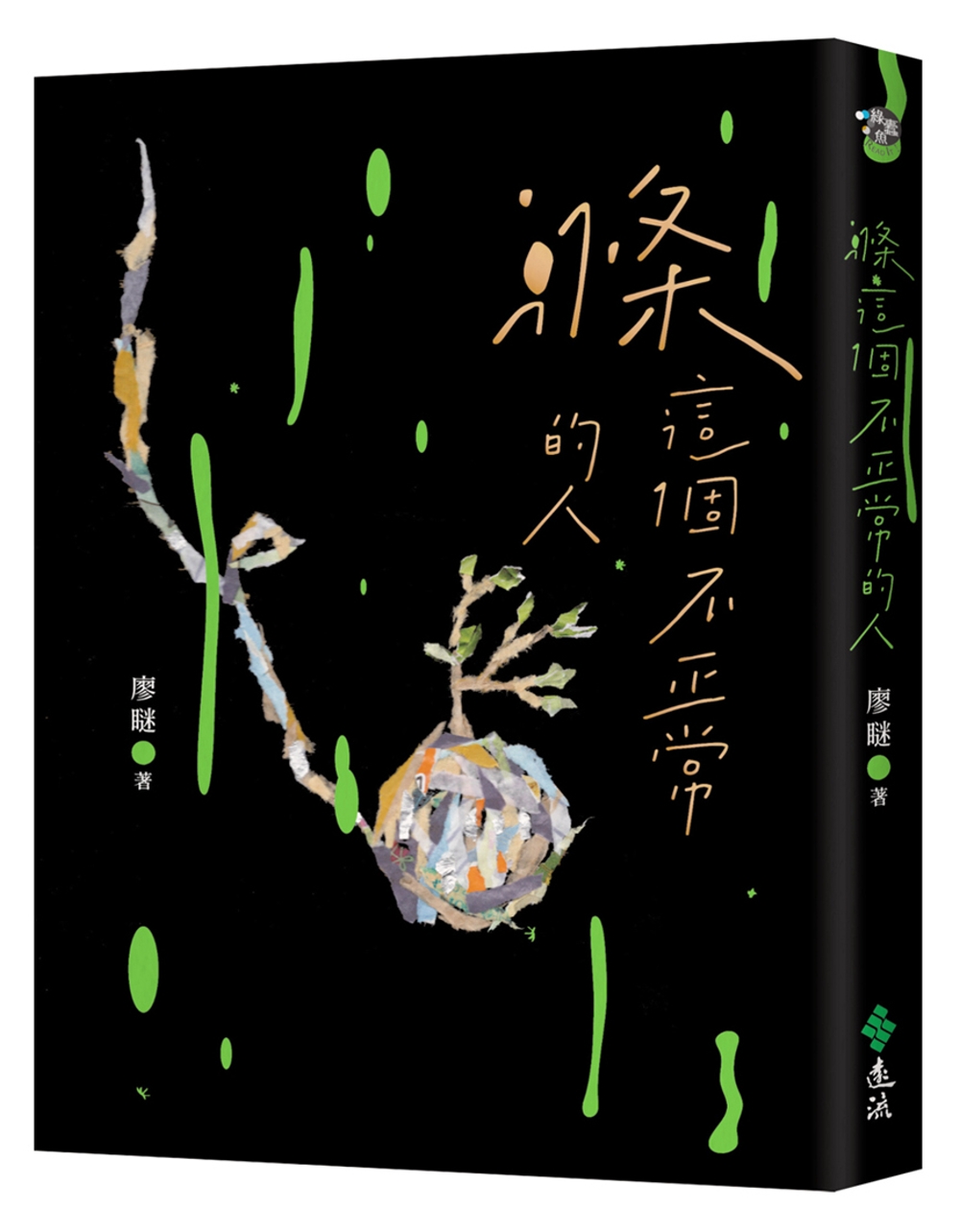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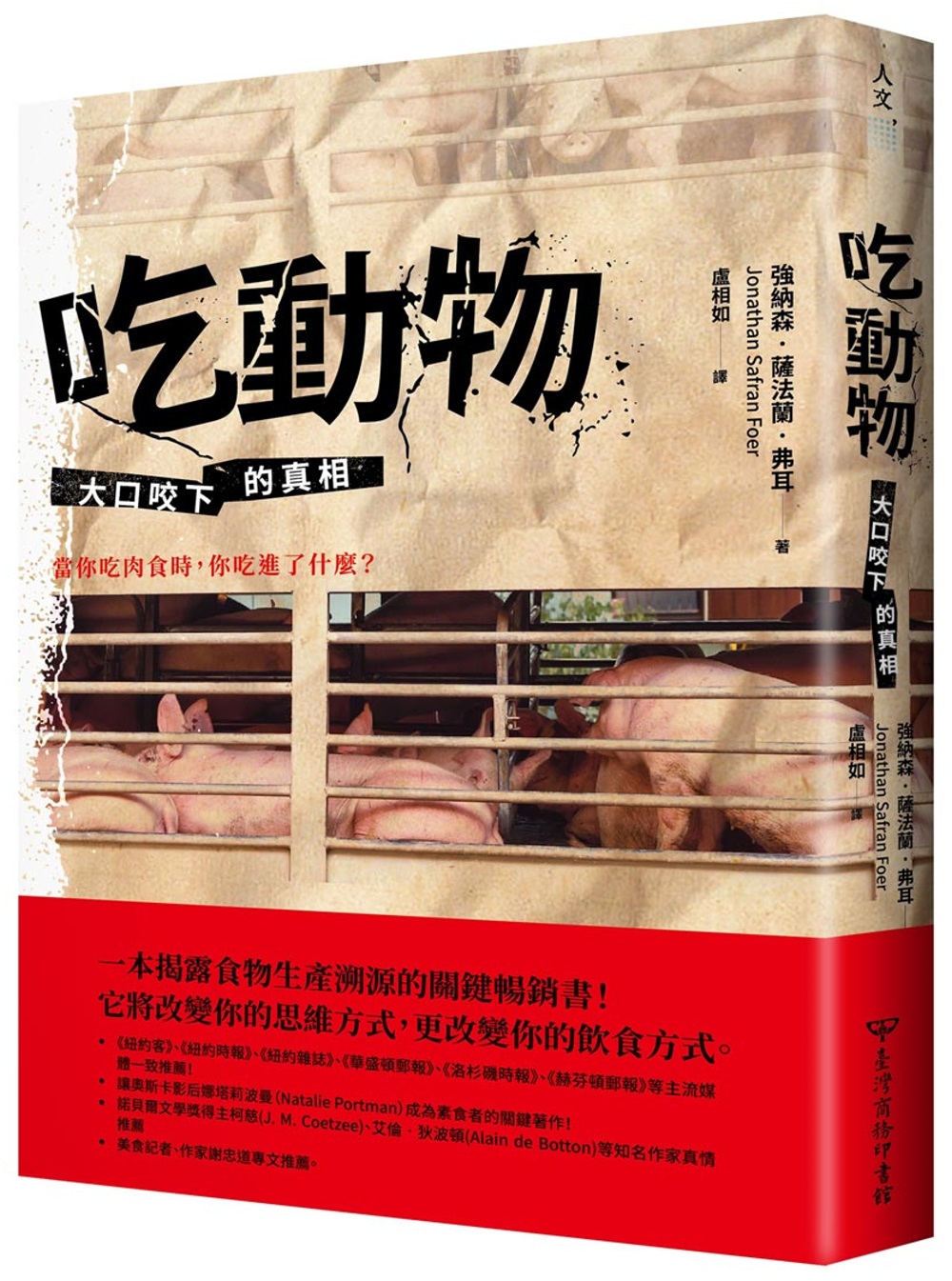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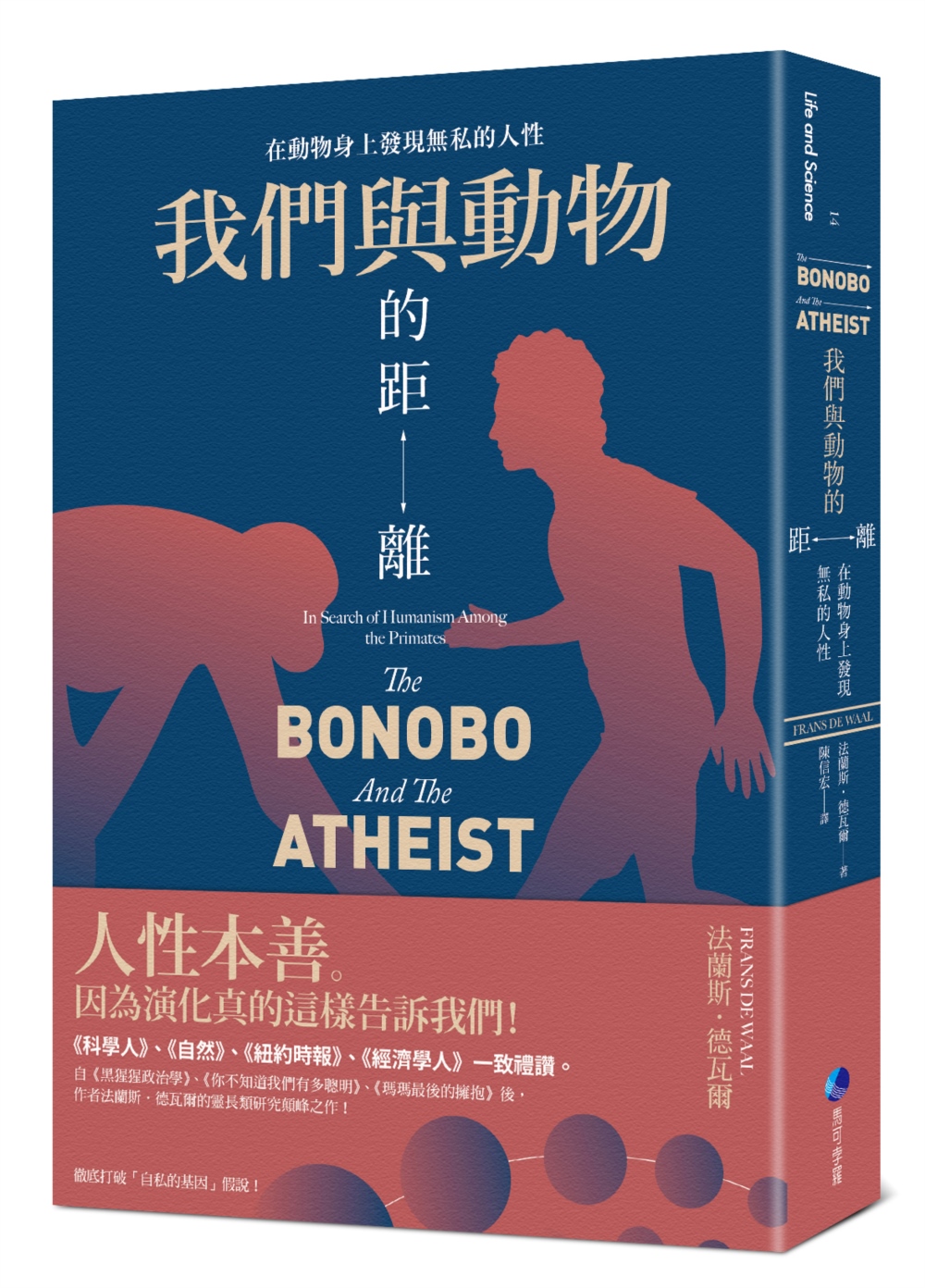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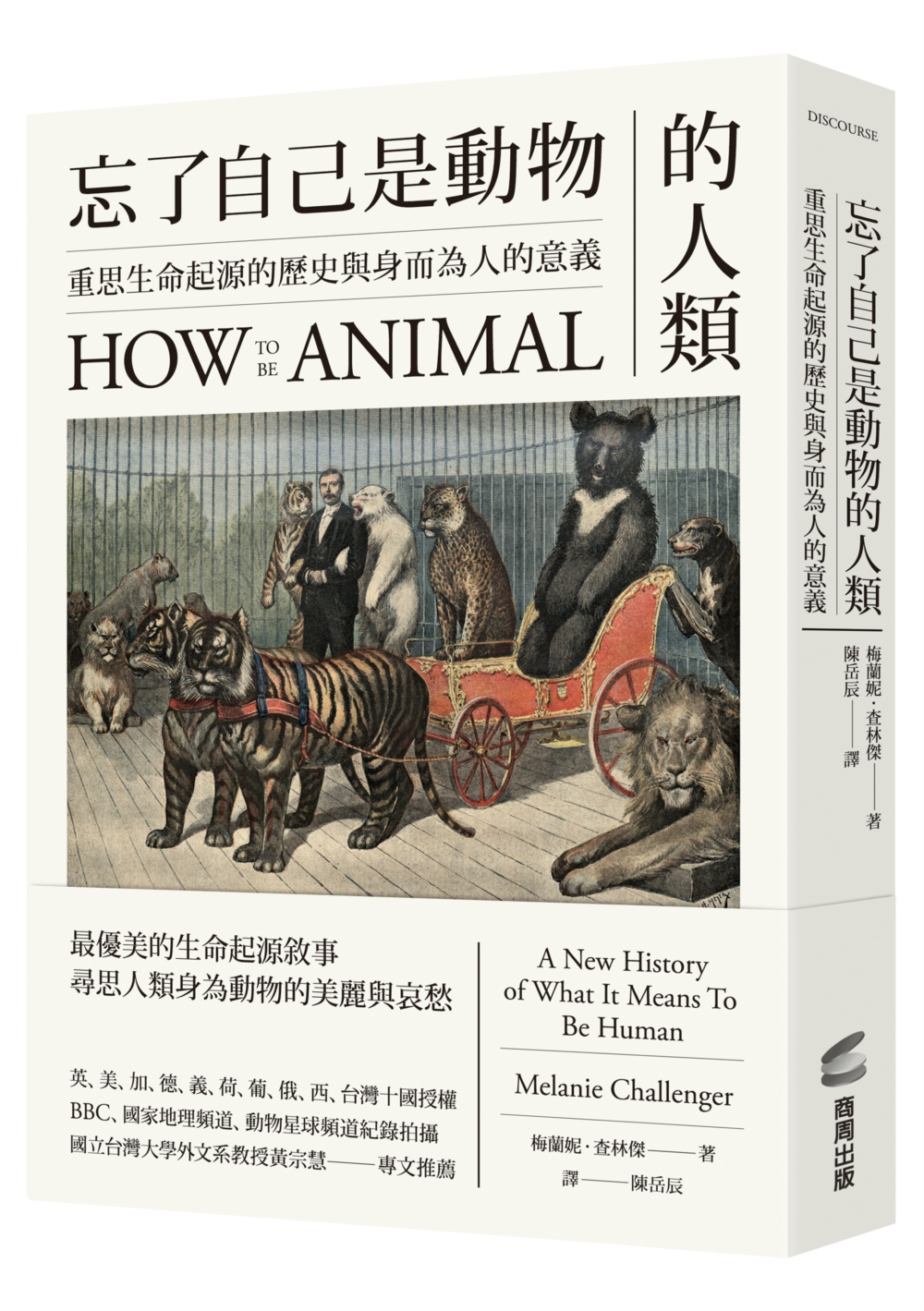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