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憤青跟廢柴可能只是一線之隔,而什麼是「騷人」,導演陳映蓉寫過:「既走不進時代,又退不出江湖,終於因為亂世無章,可以吟歌揭竿,爛漫起義,謂之『騷人』。」
以《十七歲的天空》成名,在台灣電影低迷的時期創造亮眼成績,當時的陳映蓉只有23歲,接下來的長片是2006年的《國士無雙》,六年之後的2012,傳說中的世界末日,重拾導演身分,她交出新作《騷人》。陽光盛烈的午後,訪問在開著冷氣的小房間進行,陳映蓉坐在沙發一角,手邊是喝到一半的瓶裝啤酒,談電影、生活,還有夢想,在末日預言之下,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
其實總可以打出安全牌,總有些故事觀眾一定會買單,不過《騷人》不走這一路,加進嬉皮頹廢,充斥末日預警,採用非主流敘事結構,首次登場還是作為金馬奇幻影展開幕片,「因為是2012年,值得做點冒險的事,」陳映蓉說,「很多人在做安全的選擇,很多人在做計算後的嘗試了,不差我一個。」
陳映蓉認為,末日,不一定是物質世界的滅亡,而是交接的時候,是意識選擇的時候,「末日是靈魂的選擇,你決定要到哪裡去,要用舊的方式,還是開放自己,讓新的東西進來。」說起來有點抽象,可以代換成比較通俗的命題,她想談的,其實是人生的本質。拍完《國士無雙》後,她覺得需要一點真實生活,開了一家小咖啡館,開始做生意,天天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即使不浪漫,雖然有時候痛苦,但是腳踏實地,沒有特別戲劇性的東西,真實的人生就是這樣。」多出很多跟自己相處的時間,梳理各種想法,當《騷人》的輪廓慢慢產生,她前所未有地想把這故事拍出來,「第一次拍片,不可能把你人生的信仰跟價值觀拿出來講,到了《騷人》,它是我人生的集合,也是生命走到這個階段的筆記跟心得。」如果不是距離那麼久沒有拍片,如果不是面臨現在的大環境,陳映蓉說其實她還可以繼續等,讓這個故事繼續擴張延宕。
廢柴不怕燒,奮起還可能拯救世界,爛泥似的外表只是假象,《騷人》的命題帶有濃烈的理想性,「也許天下人負你,主流價值負你,不管你被耗損到什麼程度,還是該奮起,你走到這個世代,責任就自然落在你的肩膀上,你必須要有這個意識,改變是怎麼也躲不掉的。」停頓了幾秒,陳映蓉說,「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改,但如果世界可以有改變,那一定是你的選擇。」
經營咖啡店期間,陳映蓉看著熟客來來去去,他們是差不多的人,差不多的年紀,做差不多的工作,處於同一個世代,老闆和客人也擁有差不多的焦慮,最後她體悟出「安於困惑」四個字。「你常常很疑惑,但要在這當中很自在,困惑是無解的,但自在到底了,玩到盡了,就會有一個出路。」這也是某種騷人精神,即使是無止盡的迴圈,即使是社會適應不良,接力棒都遞到下個世代的眼前了,擺爛到底,焦慮到底,觸底可能就會有答案。

電影拍攝兩男一女的生活片段,幕與幕之間呈現集錦式的群像,而非有目的前往下一個起承轉合,挑戰觀眾熟悉的時間感,更跳脫三角習題中常有的崩毀,陳映蓉認為,慾望是一件要被超越的事,「對我來說,講慾望不如講愛情,我要講的是人跟人的情感,不是性別上,也不是慾望上。」為什麼是這樣的三人組合?「兩男一女是大愛的最小單位,大同世界的最小單位。」
試映之後,她發現有些年紀大的人很喜歡,有些人對這樣的題材節奏感到不耐煩,她覺得很有趣,因為這是一部跟時間有關的電影。最近她也領悟到,《騷人》的觀影過程可以作為一種測驗,可以看出觀眾對自己的滿意程度。突破年齡的限制,騷人不只是獻給生理上屬於此世代的人,也想獻給心裡有夢的人,「即便你很累,即便你快要不相信,心裡還有夢的人依然有改變世界的潛力。」
走不進時代,退不出江湖,心裡有夢有騷動,用一句話來說騷人,陳映蓉答,「騷人是活在當下就可以改變未來的人。」
〔2012之後的計劃?〕
陳映蓉:導演對我來說,是在虛實之間的修行,像是莊周夢蝶,黃粱一夢,屬於人生本質的追尋,我一直很喜歡陶淵明《桃花源記》這個小小說,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步就能做到,但很希望能夠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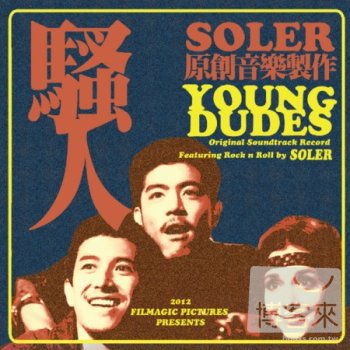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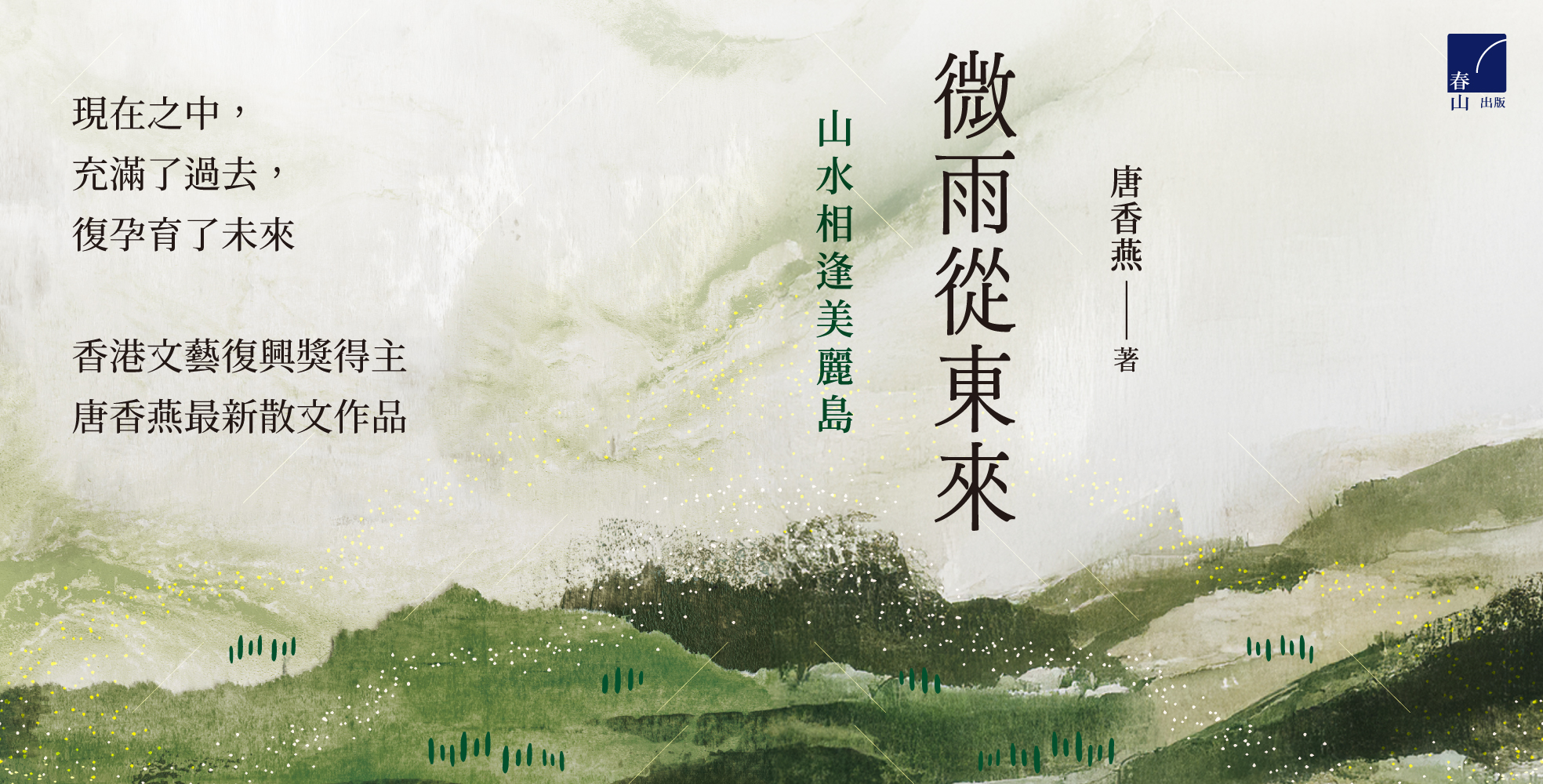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