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家朱和之。
採訪當天,朱和之隨身帶著跟朋友借來的Leica M3,這台萊卡生產於1950、1960年代,他說,鄧南光慣用的是更早期的萊卡機種,可惜借不到。畢業於政大廣電系的朱和之,大學即接觸攝影,但拍得不多,喜歡歷史的他,從歷史小說到學術書籍無一不讀,也樂於踏查歷史現場,歷史書寫於他非難事,他從隨筆開始,寫就《滄海月明:找尋台灣歷史幽光》,後轉入歷史小說創作,陸續完成《鄭森》、《樂土》、《逐鹿之海:一六六一台灣之戰》、《風神的玩笑:無鄉歌者江文也》等長篇。

他新出版的《南光》以攝影家鄧南光(1907-1971)為軸,貫穿1930年代至他1971年辭世為止,前後橫跨40年,涉及日本戰敗、國民黨撤退來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南光》之前,朱和之才重現台籍音樂家江文也(1910-1983)的傳奇人生,但江文也主要活躍於東京和北京,其經歷未能反映彼時台灣實況,激起他書寫同時代台灣人的欲望,適逢「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徵稿,他奮力一搏,花5個月研讀、128天動筆完成,順利獲得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
朱和之早在大學畢業後於雜誌社工作期間,就看過鄧南光的攝影作品,但真正深入賞析,是這兩三年的事。當初他看到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徵獎訊息,「小說主人翁,以台灣歷史上迄今之傑出藝術創作者為限」,便尋思攝影家這題目可做。他去拜訪策劃過台灣前輩攝影家回顧展的簡永彬,請他推薦,簡永彬二話不說,答:「鄧南光」。後來,朱和之從圖書館借來所有檔案照片,他坦言,初次看完並無特別感觸,翻閱了兩三次,細看之後,情緒竟忽而被擾動。
寫作《南光》前,朱和之在離家十載後被迫遷回老家,一切重新整頓,他形容,宛如對自己生命與回憶的一次大清理。原是無法在一個安心的狀態下進入新小說的創作,未料《南光》最終成為一場「內在生命之旅」。為了填補照片之間的空白、想像照片背後的故事,他自認「發明」(或曰「虛構」)了鄧南光及其他人的生命史,因此,不得不大幅動員自身生命經驗,跟著攝影家們又活了一次。小說完成後身心俱疲,情緒卻出奇飽滿。
寫作《南光》,讓他發現原來攝影與文學如此相像。攝影並非現實之複製,寫作亦然,他年輕時候執著於文學必須「寫實」,如今才體悟寫實之不可得。攝影與寫作,儘管工具不同,創作本身的內核卻是連動的。
事實上,朱和之寫《南光》並未事先知會鄧南光家屬。書稿完成後,簡永彬領他去見鄧南光高齡92歲的兒子鄧世光。他心存忐忑,沒想到鄧世光回應得大器:「小說本來就有虛構啊!隨便你寫。」
歷史小說的真實與虛構,該如何拿捏?朱和之以《南光》做了一場精湛的展演。以下是這次的訪談。

攝影家鄧南光。(取自《南光》,印刻出版,提供 / 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
Q:您最早接觸到鄧南光作品是什麼時候?
A:我剛畢業時(2000年左右)在雜誌社待過一段時間,當時鄧南光已經開始陸續為世人所知。若寫到北埔、關渡,需調圖,一定調他的照片。今天我們講鄧南光、張才(1916-1994)、彭瑞麟(1904-1984)這些台灣攝影家,覺得很理所當然、很容易在書店買到他們的攝影集,好像他們一直都在,事實上,他們一度幾乎從這個世界消失。

1989年,簡永彬、張照堂老師開始在《台灣光華雜誌》做前輩攝影家的調查、報導,第一個就做鄧南光,並舉辦攝影展,這個社會才重新認識他。戒嚴時期,攝影是一件很封閉的事,政府不希望民眾拿相機到處亂拍、發表,很難想像鄧南光這等重要的攝影家沒有開過個展,也沒出過攝影集。鄧南光拍照的習慣有點像現代人拿手機走到哪拍到哪,只不過他有很好的攝影觀念。他的敏銳,跟一種溫柔的眼光,把當時台灣的生活很生動地記錄下來。
Q:您曾提過,決定小說書寫的對象,必定是為其生命情調觸動,產生共感。您如何決定以鄧南光為題展開創作?描繪他的一生時,希望彰顯他什麼樣的精神?
A:這些攝影家當中,我自己的生命情調跟鄧南光比較像,都是「退後一步看世界」的人,不太直接參與。他不是一個抗議者,日本時代,叫他當皇民,他有一個日本名字叫吉永晃三;到了中華民國時代,他寫文章說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他轉換得很好。在行為上,他很隨順,反正能拍照就好,看起來滿沒骨氣,可是他就做他能做、想做的事。
張才就滿抗議性質,他在上海時期拍很多窮人乞丐,彰顯社會不公,是很厲害的街拍。他採取「對決式」的攝影,拍到很多人對他怒目而視,神情很有力量。鄧南光不幹這種事,他是偷偷摸摸的。他如果覺得你很好看,想拍你,不會冒失的現身,一定是繞到後面,慢慢包圍、接近,趁你不注意時拍下來,拍到你最自然的一個表情,你甚至不知道被拍到。
我的小說並不是要為鄧南光立傳,而是透過他去看那個時代的流轉,鄧南光的經歷讓我比較有著力的空間去發揮。他拍的面向很廣,從東京留學時期拍摩登仕女、法政大學迎新會,返台後拍了很多故鄉北埔和家庭,包括他弟弟娶媳、家族出殯。到了60年代,他轉向社會關懷,開始走入人群。我想彰顯的是,一個敏銳的心靈如何在這樣多變、混亂、壓抑的世道裡追尋,仍然讓自己的心能夠有飛行的空間。

法政大學迎新活動。(取自《南光》,印刻出版,提供 / 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鄧南光弟弟迎娶。(取自《南光》,印刻出版,提供 / 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九份盲女走唱。(取自《南光》,印刻出版,提供 / 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Q:寫作《南光》時,您參考了哪些資料?
A:寫這本書,我總共列了66本參考書目。第一類當然就是攝影理論,跑不掉班雅明、桑塔格、羅蘭.巴特、約翰.伯格等人。因為我寫的是一位受日本教育的攝影家,也讀了幾本日本攝影書,比如飯澤耕太郎《寫真的思考》或《寫真物語》,乃至《土門拳自選作品集》,裡頭全是照片,沒什麼文字,對我也有很大啟發。
第二類是攝影家的生平,或他們的隨筆。《浮與沉:攝影家尤金.史密斯的傳奇人生》寫得滿像短篇小說,非常好看!原來攝影家的故事可以這樣寫。它不是斷代式或者按時序去寫,而是每一章從一個面向(或從某一個人)切入,譬如從爵士樂手孟克(Thelonious Monk)的角度去看尤金.史密斯,你會從旁看到這個人多怪、多糾結。
第三類也很重要,是從周邊的文史,全面廣泛地去看,包括同時代社會的發展、各種文藝理論、國家的控制或是「女給」文化、戰時的動員。
Q:書中除了記敘鄧南光生平,亦旁及彭瑞麟、張才、郎靜山等人,當初撰述這本書的構想除了聚焦鄧南光,是否也有更大企圖?
A:一如剛才所言,我不是要替鄧南光立傳,我的企圖心是要寫一個時代的流轉。其中有一部分是在談,攝影是一個文明的工具或現代性的象徵,在30年代進入前現代時期的台灣,我們台灣人的精神結構如何接納這個東西?如何對「現代性」好奇跟抗拒?
我寫彭瑞麟,在講寫真跟科學的關係。他父親本來是中醫,但日本人覺得中醫不科學,廢除了他的看診資格,投資土地又失敗,抑鬱而終。彭瑞麟年輕時想當中醫師,證明中醫很科學,後來因為家計的關係,考上台北師範學校;他想畫畫,偏偏色盲,老師建議他去拍照,才開始從事攝影。在彭瑞麟那個章節,我寫了當時攝影技術的進展,一個色盲攝影師使用了「色盲片」,他要用藝術去克服眼睛的缺陷,一直實驗各種不一樣的媒材、不同的顯像方式,不斷追求突破。
至於寫張才,就是寫真跟社會的關係。照片的力量很大,張才透過對決式的攝影,把社會實況帶給你看。
郎靜山(1892-1995)則是首先用「集錦攝影」(集合多張底片之所需景物)創造出他心中美好的中國。1950年代他來到台灣之後,沒辦法拍,無法取得新圖像,怎麼辦?他就用既有素材去做出他懷念的中國。而他長年主宰了台灣攝影界。
你可以看到攝影能夠對應到科學發展、社會、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
Q:您大學時代開始接觸攝影,攝影的喜好和技術在寫作時發揮哪些助益?
A:暗房的經驗對我有很大幫助。為了《南光》,我特別去達蓋爾銀鹽暗房工作室,重新學一次暗房實作。暗房很迷人,是你唯一能夠清醒著進入、很類似潛意識的空間。「暗房」顧名思義不能有光,但要能看得見,得有盞紅光的暗房燈,像不像作夢?你是半清醒的。
在暗房沖洗時,你要調整參數,看要裁切或遮罩,透過你的心像呈現出來,從藥水裡顯像的過程就像巫術──我們的視覺經驗,會先看到亮的地方,把暗部對比出來以後,才能辨識影像;顯像過程卻是逆反的,相紙是白色的,曝光好放進藥水以後,慢慢會有些黑色浮現,等到黑色部分出來夠多,才忽然整個扭轉過來,能夠辨識出是什麼影像。你會有種認知不協調和驚喜的感覺,它又很像一個時間逆轉的過程。
我們常說相片好像把時光切片保存下來,就像標本。我寫這小說,就有點像把每一個凝固的時光,放回時間的大河裡面,讓它融化,讓它流動,去看到這一秒的前一秒跟後一秒,乃至於前一分鐘後一分鐘,前一年後一年。

Q:您認為「發明」、「虛構」了鄧南光的生命史,小說中很多情感是臆測的?
A:對,是臆測的。他都是留下照片,沒有什麼文字資料,所以我必須從影像去解讀他的人生跟他的情感。我寫這小說是用兩種眼光,一是「機械之眼」,鄧南光、張才等人留下這些珍貴的影像,讓我們看到30至60年代的台灣,我們看圖說故事,讓那個年代重新回到眼前。
雖說有圖有真相,但很多時候,真相其實在圖的外面,比如,張才拍過二二八,擔心牽累被攝者,自行把照片銷毀了。他們有不能拍、沒有拍的東西,我用「肉身之眼」,也就是他們的生命經驗,補足機械之眼看不到的,這兩種眼光合併起來,就是一個時代的圖像。我關心的是,人在那個時代如何生存?
Q:《南光》刻意不使用引號標示出對話,用意是?
A:過去大家可能一直覺得我是歷史小說寫作者,我以為的寫法就是「很寫實」,可是這次我故意取消引號,這很多人都用過,像薩拉馬戈《修道院紀事》不用引號,甚至不用句號。我從楔子開始寫,那是唯一後設、以第二人稱寫作的篇章,當時只是好玩,寫了之後覺得好美唷,感覺很舒服,就定調了。
因為當你跟自己說話的時候不會用引號嘛!後來雖已不用第二人稱書寫,但延續了那個情緒,就不用引號。我發現它非常好,因為讓你搞不清楚是對話、當下思緒,還是忽然跑出來的回憶,乃至於是全知作者的客觀陳述,全混成一團,變成一個蒙太奇效果。這很接近人在觀看一張照片時,思緒會不斷跳躍的狀態。
在小說裡,我甚至會跳到未來,譬如說,「20年後你回想到此刻、你那時候才明白⋯⋯」我們在小說裡有權力讓讀者預先知道你20年後會這樣想,就可以把整個精神結構或時間拉長,造成一種審美距離或特殊的審美方式。

Q:您說,寫完《南光》很興奮,告訴自己,終於寫了一本「非歷史小說」,但陳芳明老師讚譽這是最棒的歷史小說,令您有點哭笑不得。您原本為什麼覺得《南光》不是歷史小說?
A:關於歷史小說的定義,我現在也不是很有把握,我個人覺得,歷史小說是以事件為中心,要比較嚴謹,虛構部分也許要藏得好一點,或是沒有那麼多虛構。我也一直在探尋歷史小說的邊界。
你們會覺得《單車失竊記》是歷史小說嗎?我想不會,但它比很多歷史小說都還要有歷史感。或者說《修道院紀事》,薩拉馬戈以18世紀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下令修建瑪弗拉修道院為背景,雖是魔幻寫實,但極具真實感,我認為是很棒的歷史小說。
Q:請您推薦一些私心喜歡的歷史小說。
A:歷史小說有很多種寫法,一是很重視考據,譬如高陽,我很喜歡《胡雪巖》。他很多作品考據過頭,或像亂跑野馬、炫技歷史知識,《胡雪巖》算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嚴謹流暢的。
有一種小說是藉由歷史故事來講述某一種精神。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敘述日本天平年間,四位年輕日本僧人不畏艱險隨遣唐使赴大唐,請求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傳法。尉天驄老師指出,日本戰後遇到國家發展上的瓶頸,井上靖其實是藉這個故事重新去反省日本文化。
司馬遼太郎的《新選組血風錄》則有點難歸類,他以幕末矢志成為維護幕府的守舊勢力的「新選組」為主角,把他們的血肉寫出來。這些人為何要投入幕府,違抗時代潮流?他們可能有苦衷、純粹搞不清楚狀況或為了討生活,每個人都有不同原因,內部也有矛盾,寫得非常生動,完美結合「時代感」與「個人衝突」。

鄧南光相關作品

朱和之作品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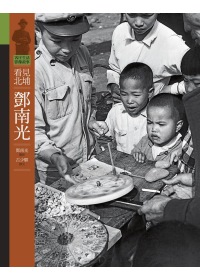




 土門拳自選作品集
土門拳自選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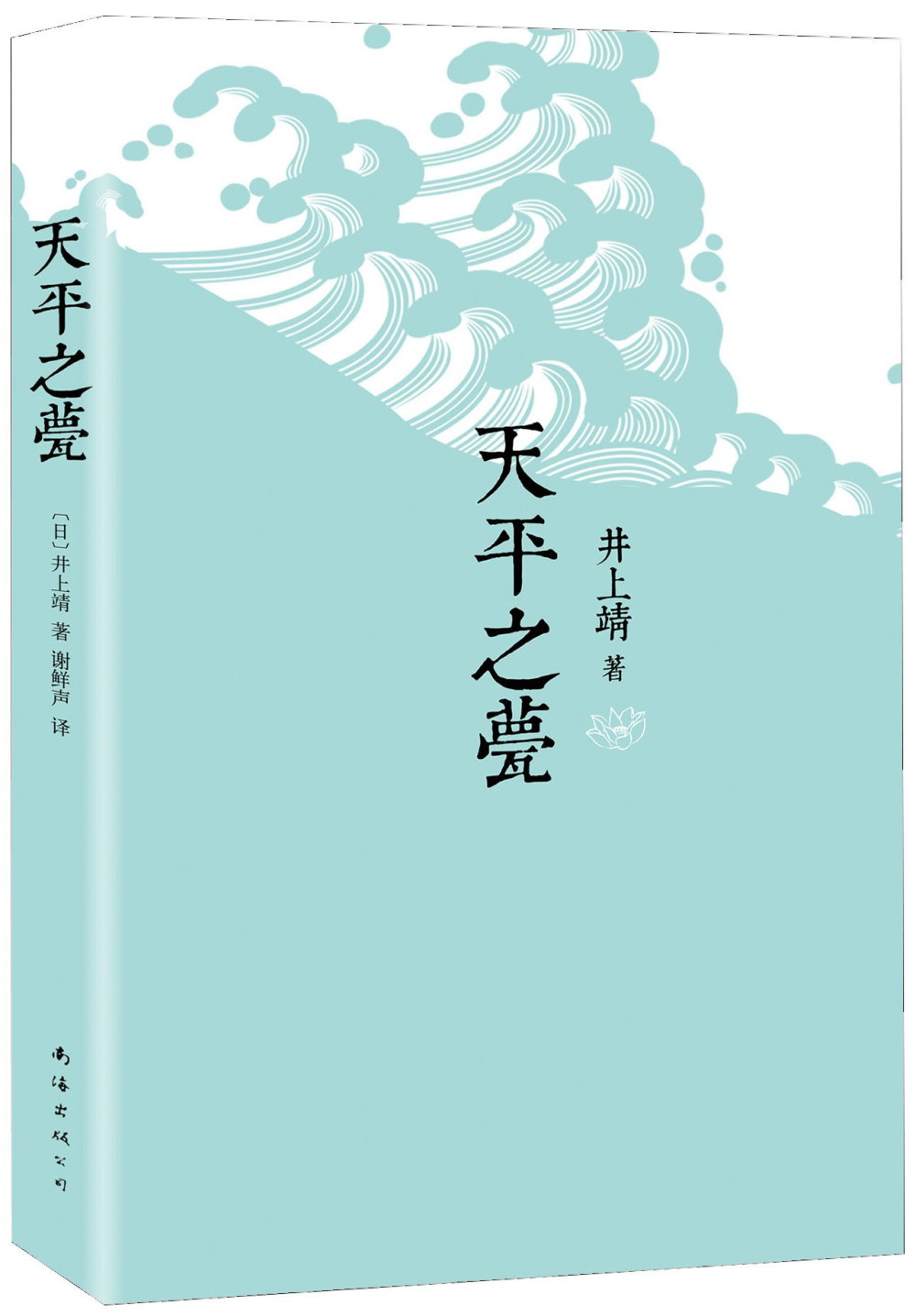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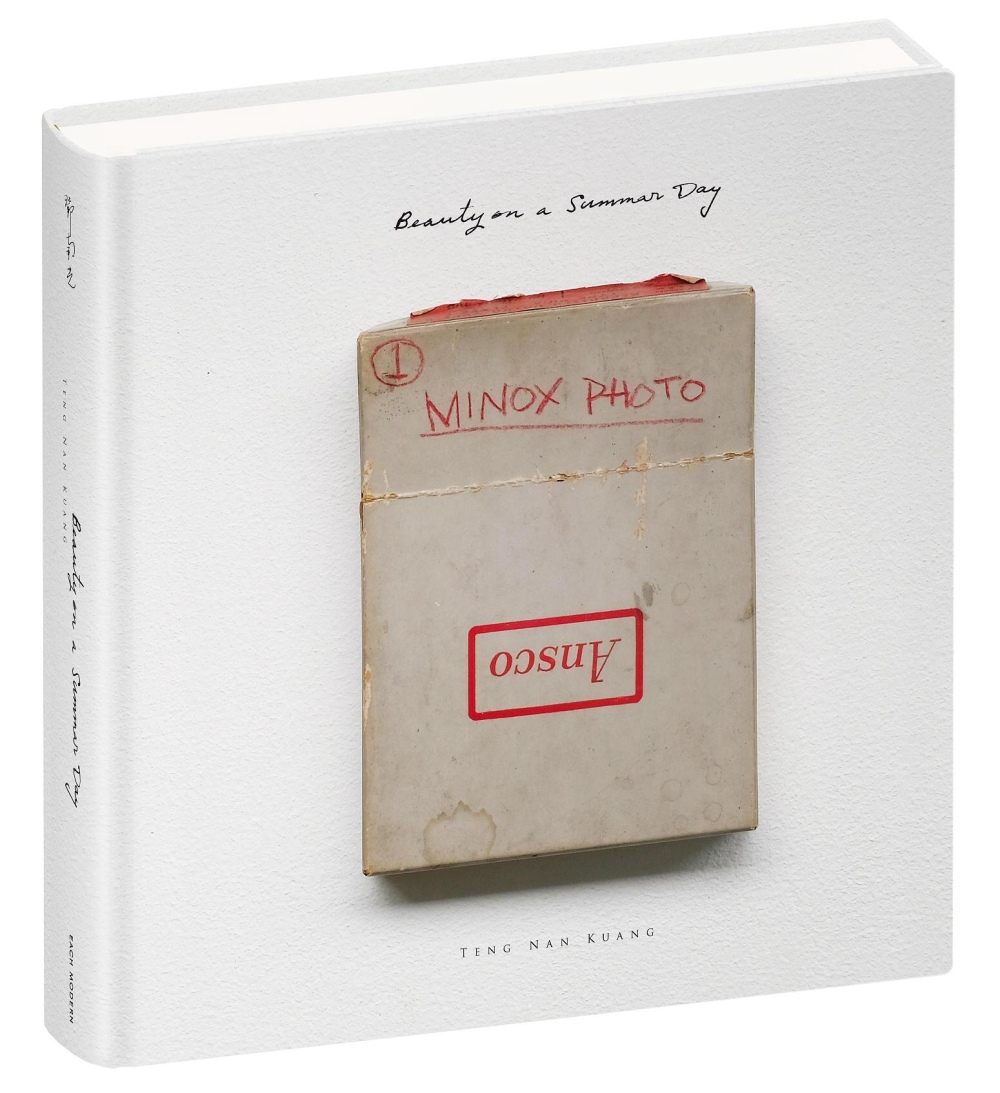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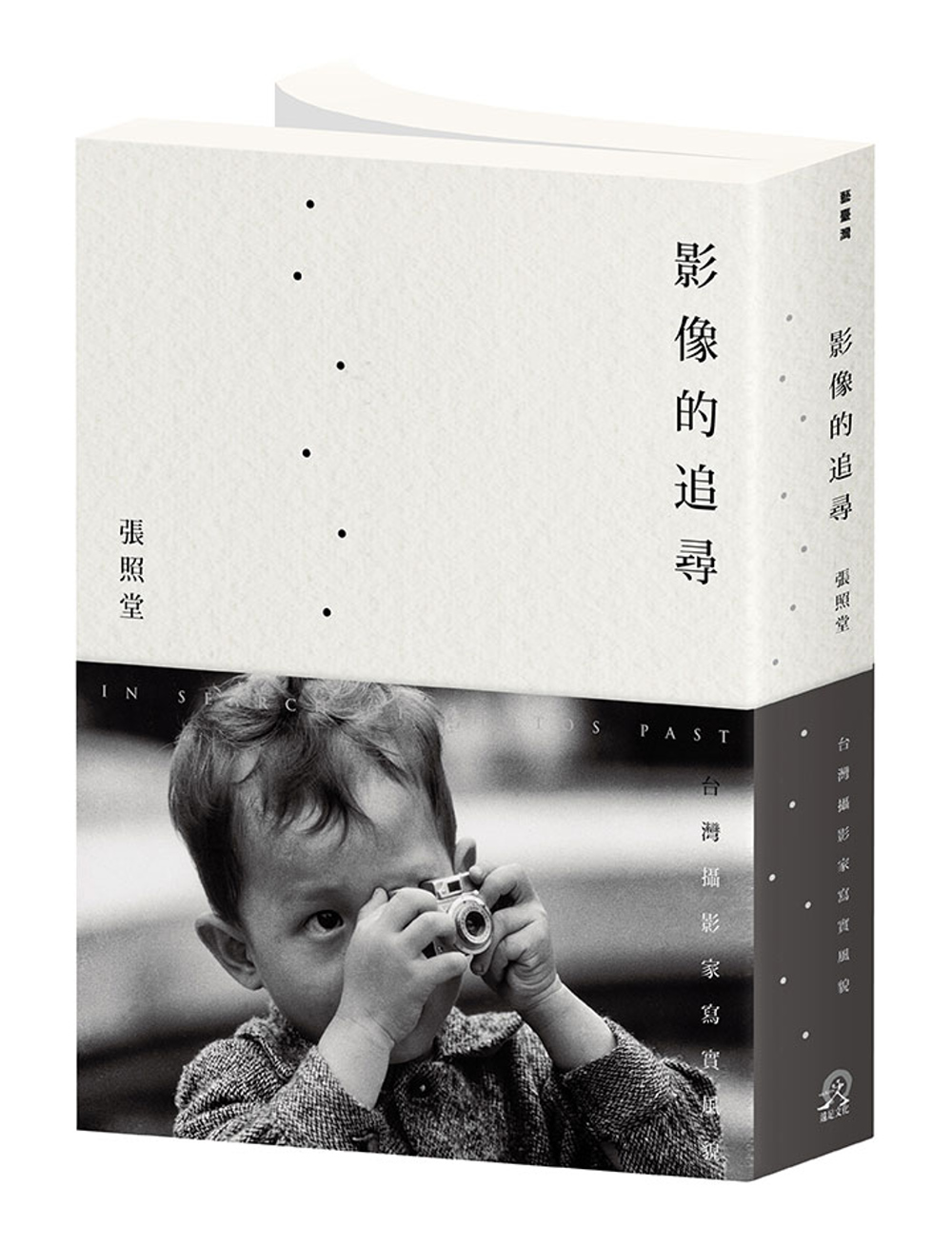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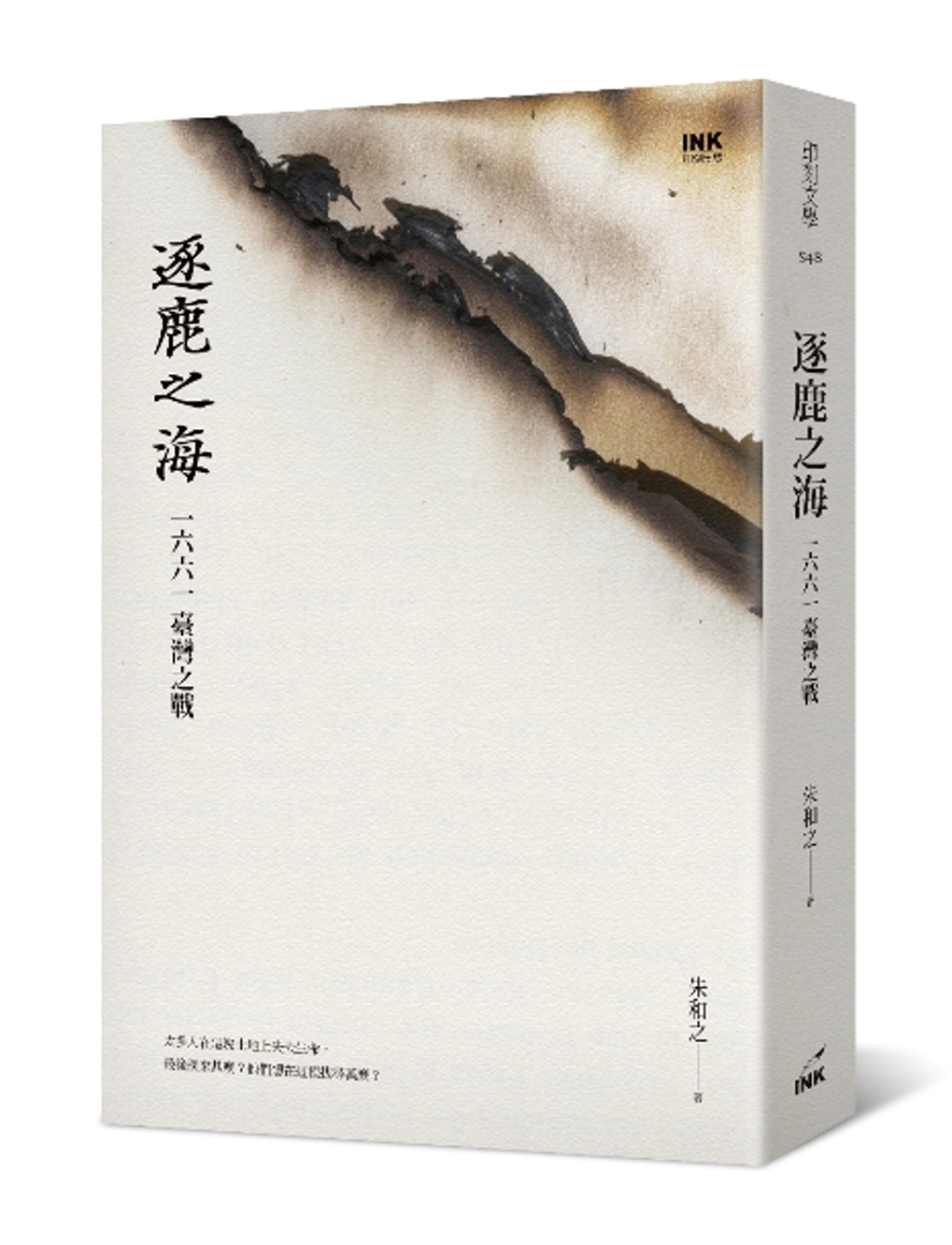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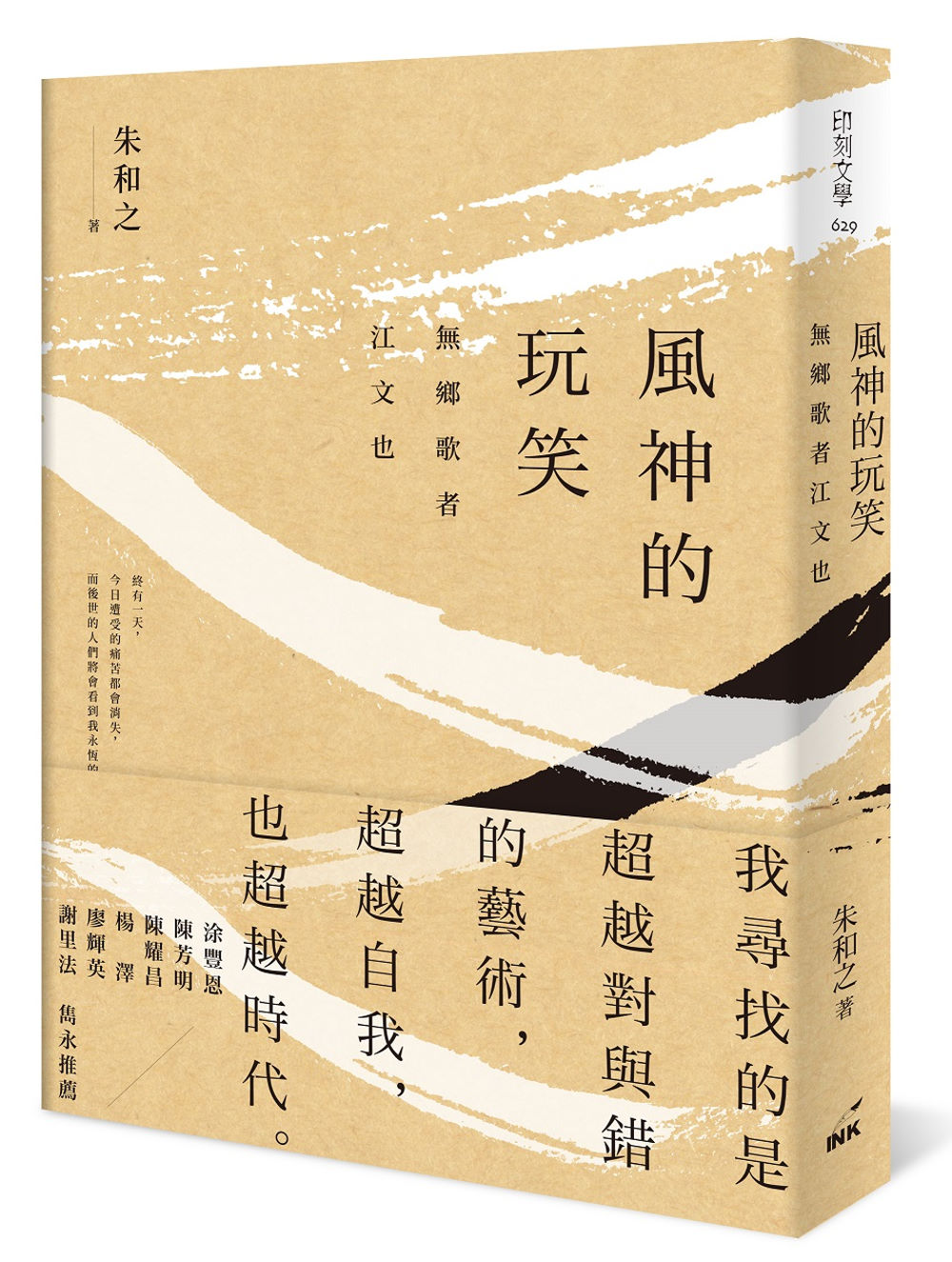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