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韓麗珠的長期讀者,一向著迷她以文字密密織出高度風格化的小說世界。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開始前,其小說中已可讀見香港怎樣命懸於昏睡和醒覺的邊緣──2017年《空臉》對比今日香港政局,如何不怵目驚心?
2020年初出版的《黑日》,是偏愛小說的韓麗珠罕有的散文集,全書採日記體,由2019年4月始,在9月杪插入五年前雨傘運動片段記錄,至11月底暫停。清楚標誌的日期,就像那一年未曾稍息的抗爭運動,隨著時序持續推進。
2019年末迄今,不只香港,整個世界都走入一個全然有異的維度。在香港法制萎縮、自由急劇限縮的現況下,韓麗珠仍持續寫作,將疫情之後,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無罪之人紛紛入獄之後的「超現實」,以她充滿韌度的思索記錄下來,輯成新作《半蝕》。
對 談 人
作者簡介
//
孫梓評=孫|韓麗珠=韓
孫:那一天,聊完將出版的《黑日》,夜已深。送你上巴士前,我笑著說:「很快台北國際書展又會見面。」沒有想到,只是隔天,港警就在我們幾日間來回走過的地段發射大量催淚彈及橡膠子彈。我回到台北,一如2019下半年以來,隔著電腦螢幕觀看香港媒體直播平安夜抗爭現場畫面,想起巴士上你揮手漸遠的身影,心裡深刻知道,若巴士即香港,無論多麼關注此事,永遠無法替代自己成為巴士上的你。還好有書,還好有字,被你寫下來的,立體且全面地延展了新聞畫面無法觸及的內心與思考。
仍是沒有想到,時間滑進2020年,疫情擄獲整個地球,台北國際書展取消了,國與國邊境日益壁壘森嚴。在那雙重的隔絕中,你仍誠實而警醒地寫著,而有了《半蝕》。書中「穴居時期」一輯,重喚醒我們如何跌進共同的惡夢,病與隔離的隱喻之於香港,更加切膚與痛,但你(在洞穴中)始終保持柔軟:觀看自己、掘挖幸福(有時做為孤獨的同義詞),使內在匱乏成為豐盈;眼光則向外照拂醫護人員、漂流者、政治立場或許相反的陌生老者、因制止堂食而無處吃飯的勞動者……
「或許,來勢洶洶的病毒,並非為了取人性命,而是以一種激烈的手段,讓人經歷前所未有的進化。」這是你的特殊眼光,才能有的說法。在「進化了的家」尚未誕生之前,香港/人必須先試圖修復自己,對你來說,「善的意圖」即是修復的關鍵嗎?又,我也好奇,新書書名「就是《半蝕》、只能是《半蝕》」,乃因「半蝕」是此刻最準確的心境?
韓:你提及前年(2019年)我們在香港相聚的事,我覺得,那種生活和那段時光,好像已被丟進一個名為「失去」的巨大玻璃球裡。每個人都看著那些失去的人、事物以至時間,總是以為一切還在,終有一天會復得,但我懷疑很可能不是如此。有時,我會想起,那年我們見面,除了以為在台北書展會再見,我還以為,幾個月後,你會在德國參加寫作計劃,然後告訴我你寫了什麼,認識了什麼人,或吃了什麼美食,但最後,你貼出的一些照片,都是行人寥落的街道,不到幾天,疫情險峻,你飛回台北隔離,出關後第一件事是,丟垃圾。
是在想起這些日常碎裂了的種種時,便感到,我們現在身處的分崩離析的世界,也是被嵌在名為「暫時」的巨大玻璃球裡,而在這些玻璃球之間,現實是像雨那樣從天落下的尖銳碎片。
關於修復,「善的意圖」確實非常重要。可是,身為人類,純粹的善,不帶任何批判、憤怒、絕望、貪婪和私慾的善,是艱辛上坡路。有時我想,人如何可以把自己從現有的紛亂玻璃球裡釋放,或許,要整個世界大部分的人,心裡的善念都提升至更高等的層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嗎,我不肯定。
「半蝕」其實是,在我看來,我的世界以及外在世界的一種共同狀態。物質的轉變,從固有的狀態,轉變成液狀,然後,不同物質彼此交融,互相侵蝕,最後,再次固化。而現在,世界置身於這種轉化,只是,一半融蝕,一半完整而已,尚未完全成為液狀。在我個人的層面,母親在年初去世,我原以為她會康復。於是,那一段日子,我無法用力地思考(用頭腦思考,是堅硬的形狀),只能感受和以直覺思索(這是水狀),那也是一種「半蝕」。
孫:你的小說《人皮刺繡》出版日期與《黑日》相近,兩者互為表裡講述了暴力及其難以乾涸的漬印。我不知道要經過多少跋涉,才能以澄明的眼寫出那些泥濘。《半蝕》「心裡有蛇」一輯,像此一主題的殘響,且那「關係」的幅員不僅於戀人之間——作家與讀者,性侵犯與受害者,貓與「我」,傷口與飼主,雲與窗,偶然與必然,囚籠與人民……戰場在街上,也在心裡。因此《半蝕》這樣一本「創傷之書」所標誌的,並非只如顧城詩句:「使我們相戀的/是共同的苦痛」,而是「自己的內在之書,跟眾多他人的內在之書,突然在某天生出了可以互相接通的部分」。這是你必須在書寫中反芻痛苦的原因嗎?又或者,曾經你觀看過痛苦的花朵,希望藉由時間推移,更完整展示「從花冠到莖部的奧祕」?
午後我前往實驗劇場看周書毅舞劇《阿忠與我》,觀眾陸續入場時他已在台上舞動身體,黑盒子中唯有一方LED看板亮著紅字:「在與____相遇之前,我的身體是____的」。其後,身障者阿忠坐著電輪登場,他施與命令,使舞者重新找尋身體,兩人也經歷過相互承載的可能,唯當「黑暗」光臨,曾經自由的身體必須撐拄拐杖如同被挾持的刑犯,此刻,LED看板幽幽亮起紅字:「我會得到新的身體嗎?」
我從沒忘記,相遇是暴力的。暴力的幸運。
韓:「電車在夜裡對稱/往前,成為螢」
會進入那種暴力,或,關係裡的兩個(或以上的)人創造出一種暴力,最初,必然有某一刻以為那是幸運的相遇。殘害是一種強大的能量,互相殘害過,留下的傷口,就是證據,證實確然曾經相遇。
任何關係模式,都具有讓人更深入體驗自己是誰的功能,那最後不免直搗,自己和自己的關係。你提及的《阿忠與我》,令我想起近日讀過的《背離親緣》。第五章,「跨性別」。山姆在妻子離他而去後,想要體驗當女人的感覺,於是變性,但之後又後悔,覺得自己犯了錯,再動了一次「恢復」生殖系統的手術,非常痛苦。作者指出,每一百個動過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就有一個後悔。一個人給予另一個人的傷害,以及後悔,是一件怎樣的事。當我讀到這故事,只想到,這是巨大悲傷的顯化。
其實我有時會覺得,「不應該」書寫那麼多痛苦,然而這世界,大部分的人和場域,都抗拒認真感受疼痛,文學書寫則是少數的例外。有時我希望,書寫是一列電車(在香港,這種交通工具最緩慢),所運載的痛苦,重量漸漸減輕,無論載具或載體終於都成了會發光的螢。
活著的心願僅僅是「挺直腰桿做人」
——韓麗珠
孫:戰場不只在心裡,也在腦子裡。如果說,循著日期翻頁的《黑日》保留了2019年抗爭運動的時序,《半蝕》「吃人的家」一輯,則直面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通過後,人民(尤其是,一位像你這樣持續於公眾媒體上寫字的創作者)「思想」的處境。畢竟,執法者已然「合法地」從現實中對手無寸鐵者的攻擊與盤查,延伸至思想的檢驗。國家機器且不斷透過宣傳(propaganda)、弱化反對者聲音、侵犯或囚禁肉體,使自由煙散,使舌頭麻木,使生活成為一件難以褪脫的假裝。
恐懼如此真實,文明墮成荒蠻,一條又一條荒謬的新聞撲至眼前,「穴居生活」亦可能被凌晨搜捕的警察敲開大門而「失去洞穴」,想必有許多朋友都為你擔心,但你(在審慎的思考後)仍決定留守香港,是因為寫作的人無法離開自己的土地?或者,你的「根部」有其他更深層的理由?(一如你總能清晰解夢,你有看穿夢與現實表象的能力。)
「吃人的家」一輯,同時寫了你搬離屯門,找房子、遷居所歷。我們暫時還無法輕省地過上一段《游牧人生》,而現實的尋求安頓,與靈魂的尋求安頓,或許都指向同一個課題:我們已找到自適的方式嗎?
就像你所說:小死(睡眠)乃人生必須,最高的真實無非一吸一吐,活著的心願僅僅是「挺直腰桿做人」。
沒有吃過人的家,或者還有?
韓:年初,母親病逝。那之前四個月,我從屯門搬到粉嶺的房子。找房子的時候,母親一直在擔憂,暗裡想了不同的讓我安居的方案(這些都是她不在之後,姊姊才告訴我),某次,她甚至對我說,要賣掉自己的房子,讓我有一筆首期可以去買新的房子。那時,她說:「我不久於人世,你也不必跟我一起住太久,就可以獨自在那房子生活。」我只是笑著對她說:「不要傻。」但其實我對這種想法,感覺強烈近乎憤怒。我一直抗拒那種,做為女性,或母親,必須為伴侶和孩子犧牲到底,才算是愛的說法。母親明明那樣喜歡自己的房子,而且,像我一樣珍惜獨居的自由時光,為何又要慣性地過度付出?她不明白,對我來說,她的快樂比房子重要太多。
此刻,我正在籌備修葺媽媽留下的房子,為了獲得那種連結,但更可能是疲於不斷遷居。不過,誰能肯定,擁有一所房子,就有安居的權利?即使能逃過收地和迫遷,也很可能,不知道在哪天,會面臨必須逃難,否則被收押的命運。房子只是在洶湧的大海裡,一塊浮木。然而,得到浮木也是幸運的。我的世界只有「這裡」,沒有「那裡」。
媽媽年幼時在馬來西亞面對排華,被遣送回中國,她成年後,從中國逃到香港,得到安身之所,好像抓住了一條穩固的根。但,根是假的。所以,我們大概像是一種,類近「空氣草」的植物。

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人民以雨傘抵擋警方強勢火力。(圖片來源 / wiki)
孫:2019年在香港大規模展開的抗爭運動,維基百科上的全名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原肇因於一樁殺人事件,然而「殺人者」迄今未獲罪起訴,不到兩年時間,香港運轉邏輯被全然抽換,代之以權力者想要的規則:「愛」必須合法,但法治被極權壓制奄奄一息;「罪」則無關是非,端視權力的有無。因此,《半蝕》「帶罪者」一輯,你關注海上漂流的人,被迫離鄉的人,墜海而死卻「無可疑」的人,柵欄內等候審判的人……在法制失能的社會底下,誰都可能是「待罪者」。
我常想起,在香港訪問你談《黑日》時,我問,這半年來層出不窮的事件,你如何克服心口湧上的荒謬感?你答,「我身體裡有一個機制,我會告訴自己,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那時我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直到讀《半蝕》,你對這句話有著(至少兩種)令我震動的詮釋。那天我還問了許多問題,其一,是關心你的小說身分,我問,「一直以來,你都如此敏感於身分和關係,在抗爭運動中被深刻傷害的,你會試圖用一本小說來『修補』嗎?」你說,「每天都有新的恐懼。我必須覺得非常安全,才可以寫小說。」
然而,打開《半蝕》,開場一輯「城影」,以薄切的寓言體,幻燈片般為我們在柏拉圖的洞穴壁上展示了香港近兩年的斷代。其將現實米雕後雋刻收納於小小的方寸間,卻又允許被放大放大而終於看見一整座傍海城市,及生活其中的人們,人們的呼吸,思想,感情,一如過去你寫下的精采作品:《空臉》、《離心帶》、《失去洞穴》……它們都有一個不捨得說穿的名字:香港。
在仍然浪潮般拍湧而來的恐懼中,想問:你尋回寫小說的安全感了嗎?
韓:我有一本用來記錄小說意念的本子,已經許久沒有使用,但,這幾天要翻出來,在上面編織一些東西——因為我答應了幾個小說的約稿。另一方面,要把那本子再拿出來,因為我有信心,已把肚子裡「小說的固定概念」這種關於創造的障礙物消除了大半,所以想再試一下。
我仍然沒有那種安全感,而且慢慢地接受,那是失而無法再得的東西。謝謝你問我這個問題呢,因為在許多忙碌的時候,當我想到:「現在可以寫小說了嗎?」的時候,都無暇去發一個訊息告訴你。除了安全感,還需要遺忘——通過遺忘,生活裡許多紛紜和瑣碎,蒸餾出真正重要而不會被淘汰的信息,才抵達小說時刻。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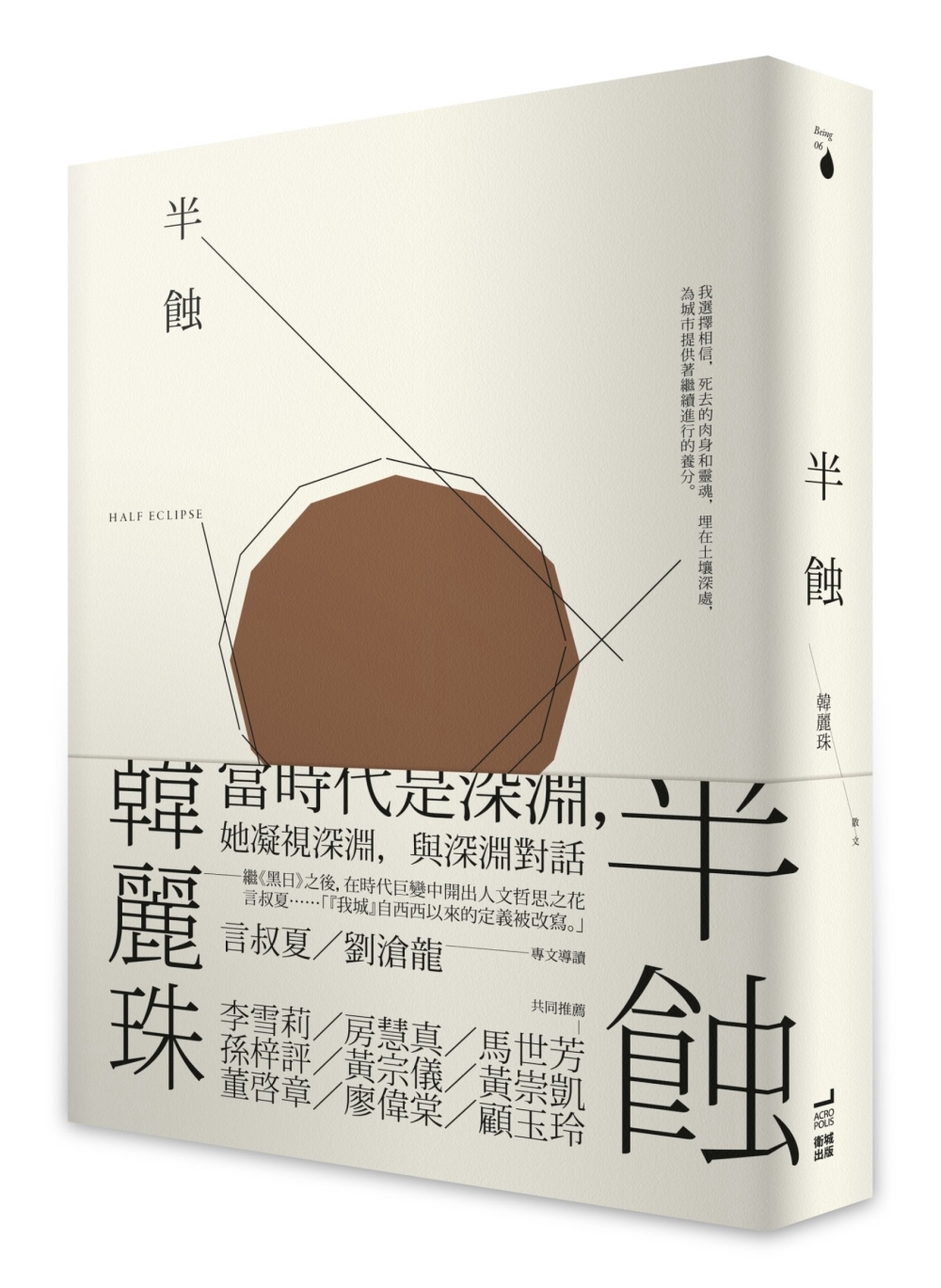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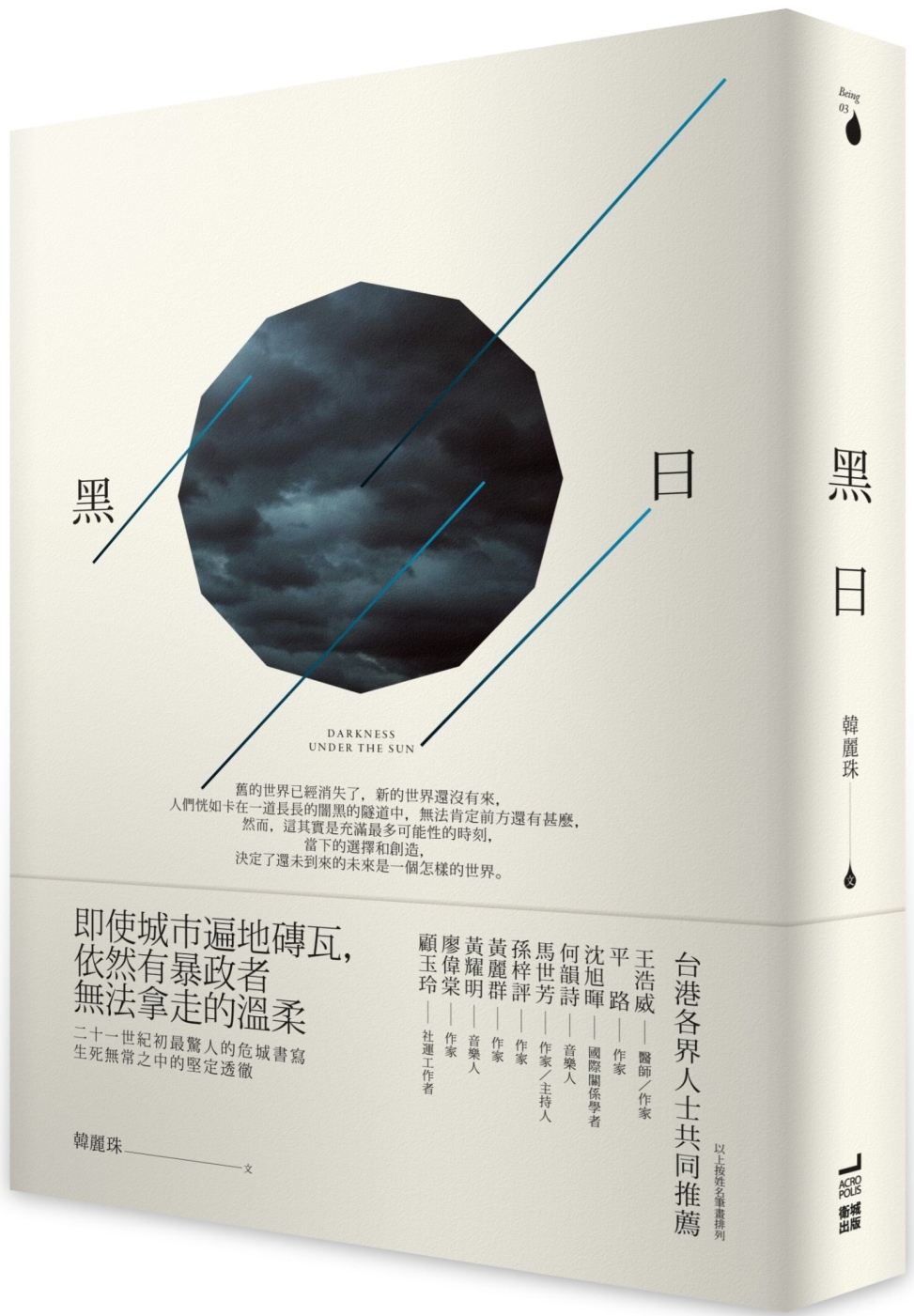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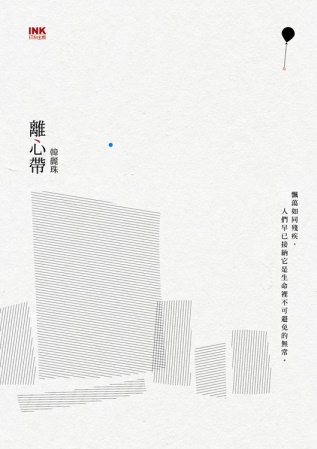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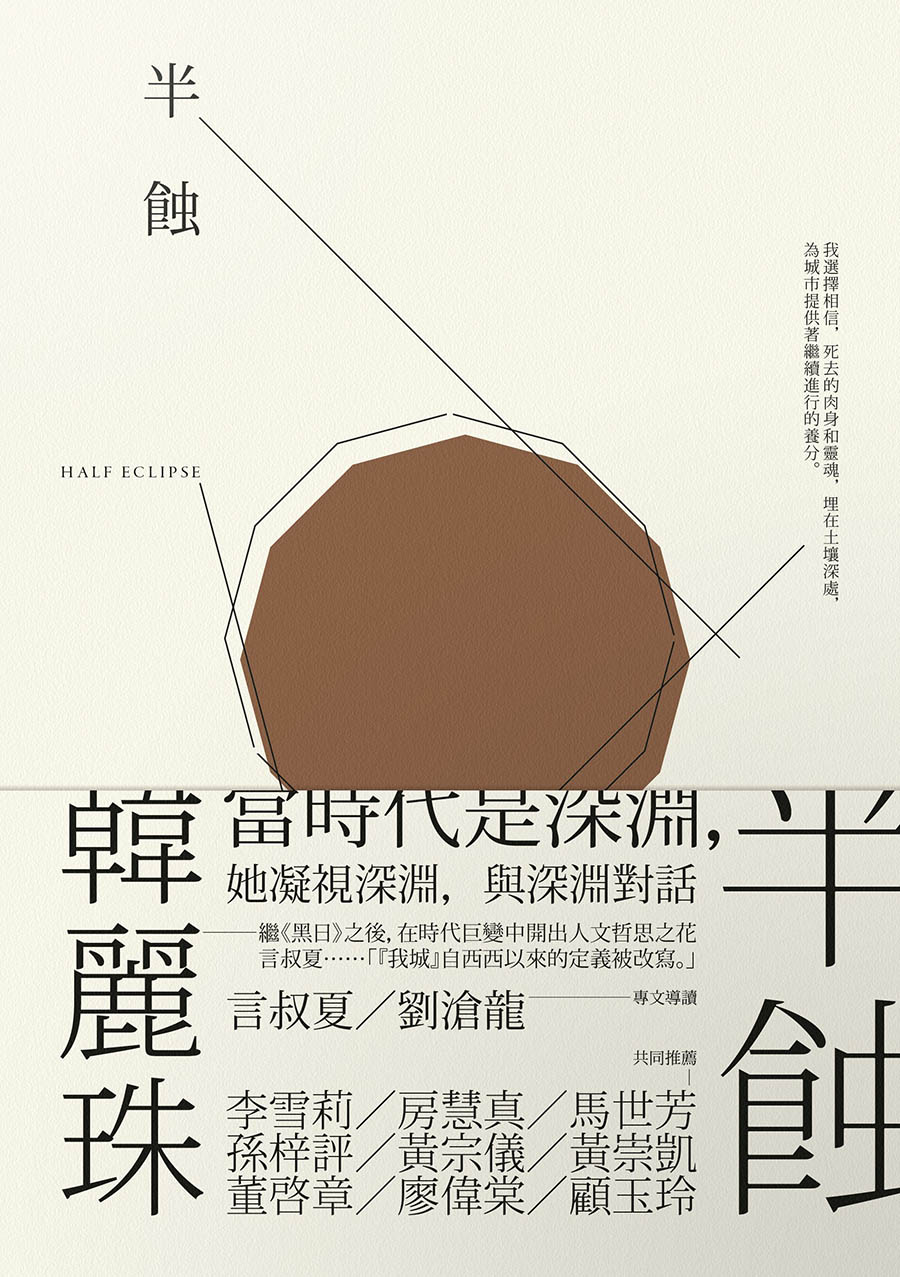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