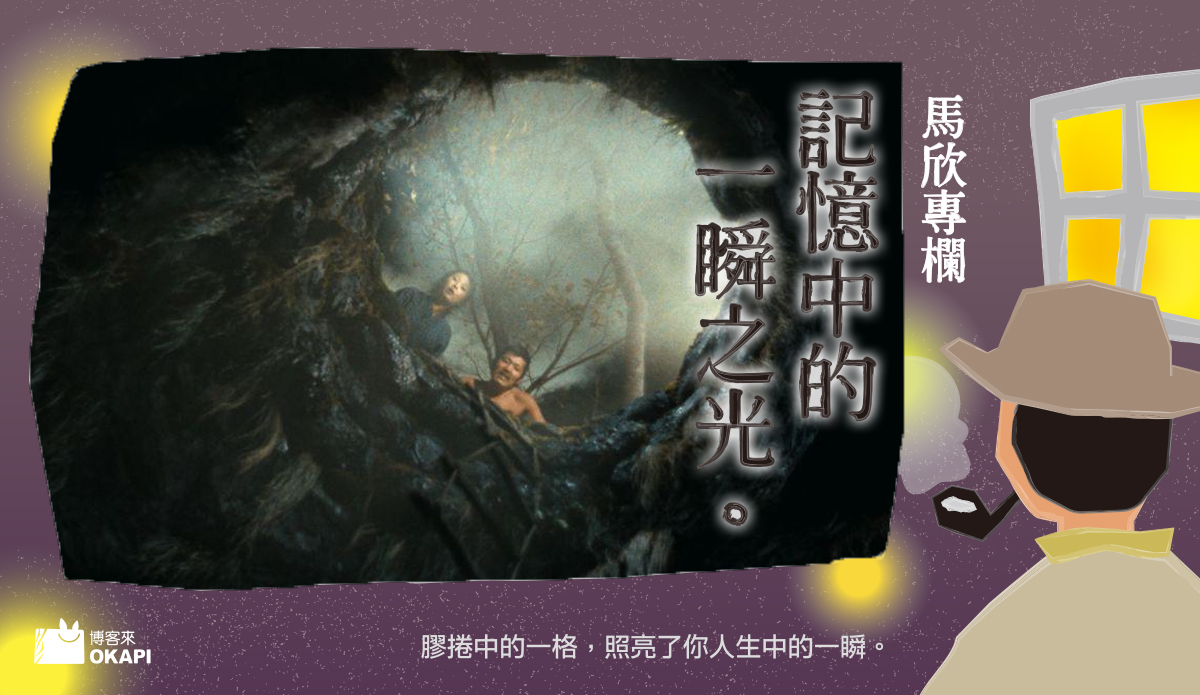
好電影散場後,它會在你的記憶裡繼續演下去。
有時只是一幕景色、有時是個角色的身影。
看似人走茶涼的一幕,卻讓你也活了進去的燈火未滅、溫度仍在,角色隨時可以回來,你總感到似曾相識。
如《新天堂樂園》膠捲中的一格,記錄了太多意在言外。
為什麼?因為它照亮了你人生中的一瞬之光,相信它是永恆,而你的心仍有星火不滅。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感官世界》的阿部定與《愛的亡靈》的阿石的人生都像種子落在泥濘中又生不了根,根壞死了也離不了地,她們都背負著性的原罪。如一株鮮嫩被栽種在陽剛社會的絕望本質裡。
《感官世界》的阿部定與《愛的亡靈》的阿石的人生都像種子落在泥濘中又生不了根,根壞死了也離不了地,她們都背負著性的原罪。如一株鮮嫩被栽種在陽剛社會的絕望本質裡。
電影一開始就以一個破舊的車輪,如同催眠一般地帶你到一個遙遠的過去。
輪子在殘陽與雪夜中滾動中,代表著那村莊的離群,也代表著苦日子的無盡頭。看似在很久以前與在一個很遠的地方,人們看似是受慾望的驅使而犯罪,其實是因根本無法填滿心底的破洞,而不知所云地活著,甚至不動聲色地瘋狂著。
大島渚用一個很美也很決裂的方式,來拍一個他人認為墮落又該死的人的故事。
女主角阿石在那荒村中,身體如走獸的記憶一般勞動著。那裡的人似乎從童年就習慣勞動。身為地主財產的幾戶人家,幾代都在那裡勞動著,儘管活在一個天高地闊的地方,但如牛有終生該犁的田道,人有出不去的處境。
阿石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求生著,你猜不出她多小時就嫁給了車夫儀三郎。她臉上還有點稚嫩的嬰兒肥,神情有著從少女的憨氣。她看似是豐潤的,但在揹著孩童、且習慣彎腰工作的背影中,她的身影又象徵著貧脊,如同她所居住的山村,人們像她還這麼年輕就化在那裡了似的,如同牛化入田裡、鹿化入樹林裡。她則屬於那村莊的記憶,她自己的記憶卻彷彿一搓就碎了。
所以這部電影以怪談片來呈現,有著聊齋的氣味。大島渚以60年代小林正樹拍《怪談》的美學,拍著一朵像花的靈魂被拘著,直到凋謝的過程。早些年的怪談常有這樣的美感,人化進潭中的血花,變成古鏡中的幽魂、燈籠中的怨念。
與其說恐怖,不如說古代女性的際遇被扁平化後,一個樣本蝴蝶仍想要飛起的妄念。淒涼的意味縈繞不去。
從《感官世界》,大島渚將阿部定拍出女人無根無著地當時奴命,唯一能依存與棲腹的是男人的性器。而《愛的亡靈》中的阿石,在丈夫拉車遠行的日子裡,她與男嬰如此明顯地凸顯著那地方的弱肉強食,她被豐次強行佔有後,人生如同開滿山谷的野草一樣,無可收拾地偏離任何軌道。
那酷寒的荒村,嚴冬一來就封了大地,沒日沒夜的雪境。幾戶人家各自偎著火光,遠看是如此寧靜,又是如此宿命的地方。
 阿石在丈夫拉車遠行的日子裡,她與男嬰如此明顯地凸顯著那地方的弱肉強食。
阿石在丈夫拉車遠行的日子裡,她與男嬰如此明顯地凸顯著那地方的弱肉強食。
阿石成了豐次的地下情人,並在他唆使下殺了歸來的丈夫。阿石沒有她名字頑強,這看似從有記憶以來就開始勞動的大女孩,活在一個老天賞飯、有地就種、有飯就吃的處境裡,活著是唯一的意志。
每每看豐次從市集買點甜食,就稀罕地吞咬著,那些有甜內餡的吃得可有滋味了,她嘴角的一點油光與甜粉,總算貪到點粗食外的滋味。這只有身體在長,心底卻一點點感受到空乏的滋味,到底怎麼了也說不出來,生活總是像壓境似地日復一日來了,心裡即便長出了希望新芽,每每還沒竄出頭,就被身體的疲累輾平。
 心裡即便長出了希望新芽,每每還沒竄出頭,就被身體的疲累輾平。
心裡即便長出了希望新芽,每每還沒竄出頭,就被身體的疲累輾平。
那山村就是這樣的安靜。不是都市人去鄉下體驗的那種知足平靜,而是身為一個勞動動物,靈魂總要開始呼嘯著什麼,哪裡從何時開始破掉了都不知道,心口一直吹著風。豐次與阿石如動物般衝動地完成了慾望,卻讓惶然日形擴大。阿石自殺夫後,精神如雪壓樹枝,在那隔絕山村裡面對自己內心的荒境。
她從來沒有權利與餘裕思考,這種日出低頭工作,抬頭就天黑的日子,想什麼都很奢侈,感受卻時刻侵略她。她的丈夫的存在如他駕駛的車輪是無盡的轉動,朝生夕死的證明。浪蕩的豐次像是離開村莊的一抹想像,但像知了一樣,只為了一瞬不住鳴叫著。
這村莊如命運困住了他們,而他們內心的破洞卻深不見底。
阿石與阿部定(《感官世界》)被迫寄生在男人的命運上是如此飄忽,像種子落在泥濘中又生不了根,根壞死了也離不了地,她們都背負著性的原罪。肉身因鮮嫩而可恥一般,最後被掛在樹上鞭打著。那鮮豔的人生異香,是紅顏枯骨的兩面性。
這部電影延續日本怪談的異境感,阿石殺人後如被夢魘的人生,讓你不知虛實,不知她是醒還是睡,或是醒睡已經沒有差別了。你會發現她醒來時,日常有破綻,睡著時卻有著現實的痕跡,最後心裡的樹枝終於被雪壓垮,她的精神如斷絃一般,真正活進內心的荒村裡。
 阿石被吊在樹上鞭打
阿石被吊在樹上鞭打
 殺夫後的虛實交錯,以為死去的丈夫回家
殺夫後的虛實交錯,以為死去的丈夫回家
最美的一幕是,阿石奔出她的家裡,出來是一片雪境,無限的白如囚籠,她背負著人們心裡的貞潔與慾望,她無處可逃。
乍看她們都是被街市辱罵的妖女,都是放任自己慾望的女生,她們鮮嫩如土壤,卻活在男人的絕望裡,《感官世界》是生在軍國主義冷血的高燒中,兩人汲取對方真實的體溫,感受著哪一種更瘋狂?《愛的亡靈》是邊陲與窮困的絕望,心頭一點妖火像模仿愛情的亡靈,然天地平靜到彷彿他們沒有活過。
大島渚擅長由心來看世界,他的電影世界裡沒有一定的善惡,只有堅強與脆弱。從心的破口看世界是如此魔幻,瞬間又萬籟俱寂。
此片以怪談拍法有其寓意。畢竟早期的怪談何止是怪談呢?而是颼涼世道裡一點溫存,人心頭那永遠捕捉不到的螢火蟲。如女鬼小倩之於書生的遙遙趕路、阿石之於無人能離開的荒敗村莊。故事如放一隻螢在袋中的飛舞,是人生的意象也是周而復始的追求。
《愛的亡靈》(Empire of Passion)以「車夫儀三郎被害事件」真實事件改編,日本新浪潮大導大島渚以犯罪與性愛批判社會政治代表作,改編自車夫儀三郎真實事件,主角們的愛慾與恐懼,此消彼長,同時愛慾與反抗持續綿延糾纏。此片是大島渚繼《感官世界》之後的又一情慾作品,兩片被以姊妹作相稱,影評盛讚「延續著《感官世界》,《愛的亡靈》繼續對人類性問題的深刻探討。」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 余永寬:尋找永不衰減的聲音──紀錄片《坂本龍一:終章》
- 【但唐謨專欄│電影失格之恐怖的愛】「鬼迷心竅」與「情人眼裡出西施」一線間
- 【馬欣專欄|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失去了自己就能找到愛嗎?──《密陽》的李申愛
- 【馬欣專欄|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當人失去了對故土的想像──《三夫》的一場香港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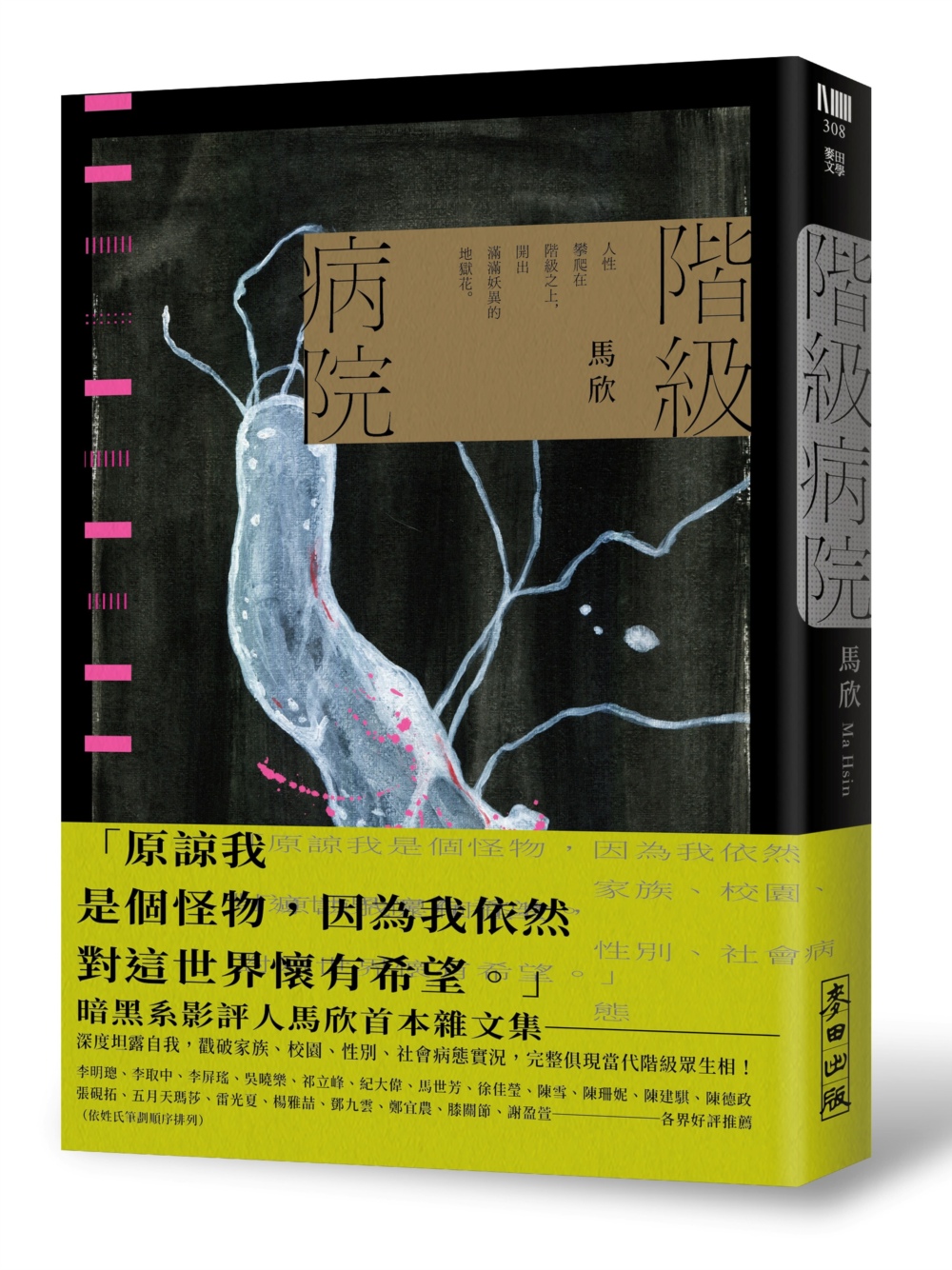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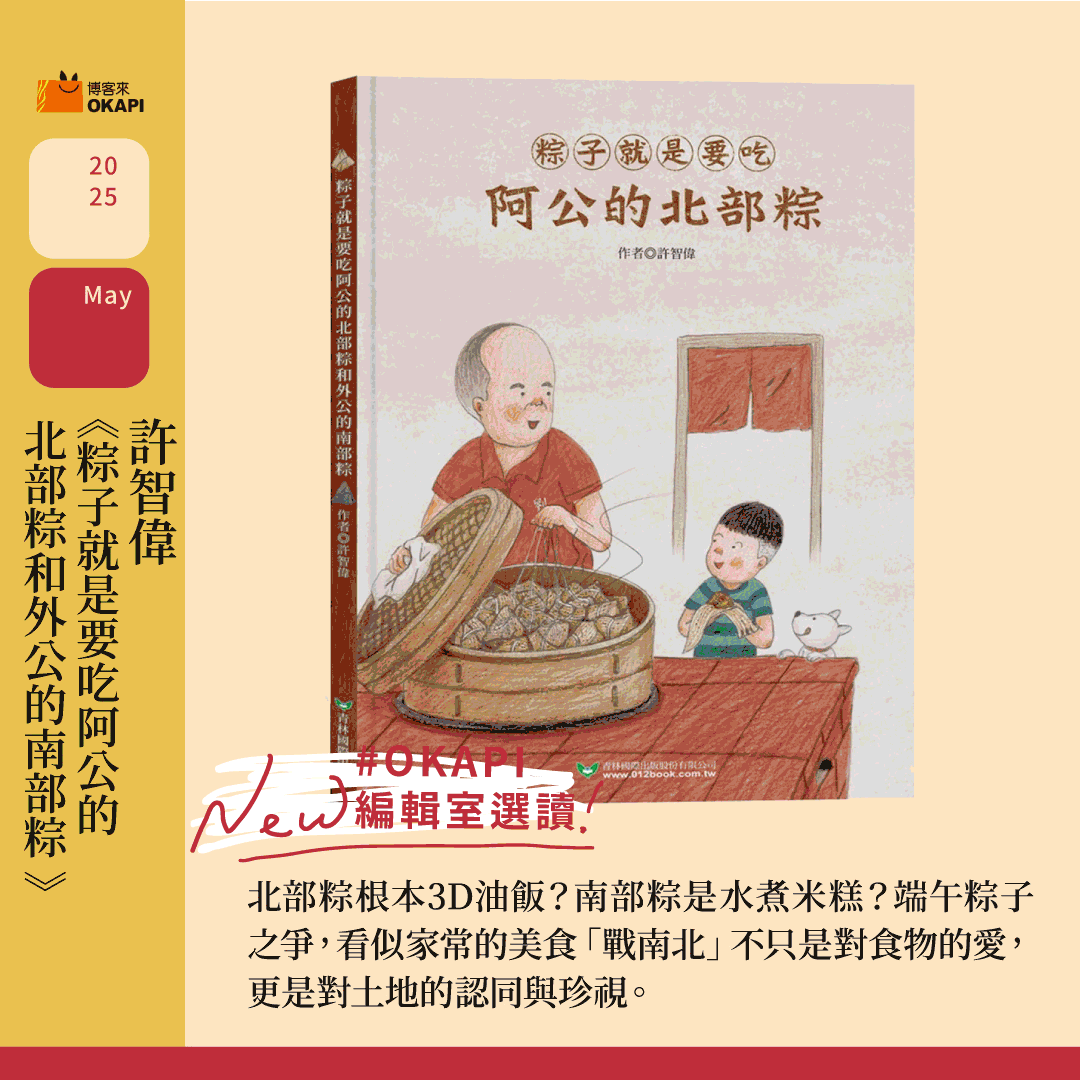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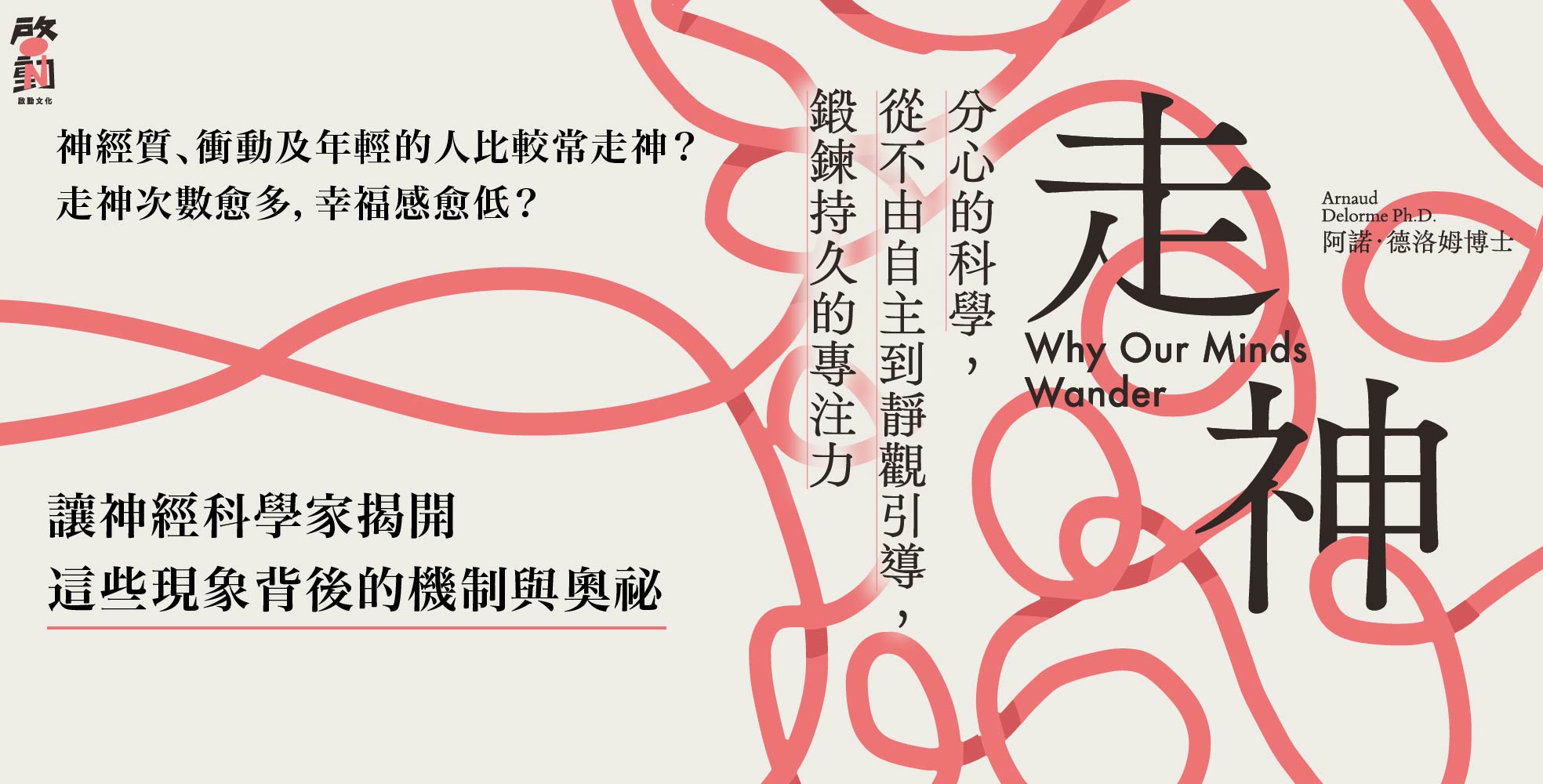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