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臺灣,提起「美國自然書寫大師」,一般讀者想到的大多是寫出《湖濱散記》(Walden)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或者《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作者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甚或以《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引領整個當代自然環保人文思潮的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對於約翰.繆爾(John Muir,又譯謬爾)這個名字向來是比較陌生的。最近,因為臉譜出版社的「山岳文學書系」問世,繆爾的自然書寫經典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原書1911年出版)才再度有譯本推出(《我的山間初夏》,譯者呂奕欣),我想趁此時機跟讀者們分享過去二十幾年來約翰.繆爾在臺灣的眾多不同面貌。

繆爾(1838-1914)是蘇格蘭人,少時隨家人遷居美國。1911年出版日記《我的山間初夏》。
▌國家公園之父?
提到約翰.繆爾,「國家公園之父」這個頭銜是絕對不能少的。1989年天下文化「自然人文書系」推出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第一個譯本《夏日走過山間》(陳雅雲譯),在封面上如此定位繆爾與他的書:「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盛夏日記」。這個稱號在隔年也在中國被採用,天下文化譯本《夏日走過山間》的版權被北京三聯出版社買去使用,以同樣的名稱出版。而在《夏日走過山間》出版的前一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綠色經典文庫」才推出了繆爾另一代表作Our National Parks(原書1901年出版)的譯本《我們的國家公園》。而且,天下文化「自然人文書系」的第一冊就是李奧帕德寫的《沙郡年記》;吉林人民出版社「綠色經典文庫」則更是完整收錄了《湖濱散記》《沙郡年記》與《寂靜的春天》。光是藉由與這些自然書寫經典名列同一叢書裡,我們不難發現,中國與臺灣的出版社從一開始就想要為繆爾塑造「美國自然書寫大師」的形象。
不過,繆爾嚴格來講並非「國家公園之父」,因為國家公園的概念,是在1832年首度由美國19世紀畫家與作家卡特林(George Catlin)提出的。卡特林的畫作與著作多以美國印第安人的人物畫以及西部大草原為題材,進而提出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應該被保存於「國家公園」內。
就像臉譜山岳文學書系策畫人詹偉雄先生在《我的山間初夏》導讀裡清楚指出的,美國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於1872年創立時,繆爾尚且默默無名,哪有推動國家公園成立的能力?但繆爾在1903年5月15日帶著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去優勝美地(Yosemite)露營,讓大自然深深啟發了羅斯福,所以他才會在接下來任期內發動史上最大的國土保育行動,創立 5座國家公園、18座國家保護區、55個鳥類與野生動物保留地。就這點來講,也許繆爾不是「國家公園之父」,但他推動國家公園設立與國土保育的功績絕對是無人能出其右。

左:青年時期的繆爾(1860年留影,年約22歲);右:繆爾曾於1903年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一起在優勝美地露營,促成總統推動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自然保育計畫。
▌在荒野中領略上帝的繆爾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雖然在1911年出版,但其實是他1869年整個夏季在加州東部內華達山山區擔任牧羊人時的日記,他在該年6月23日寫道,「噢,這浩瀚寧靜、無垠無涯的山居歲月,令人既想工作又想休息。在這些光輝的歲月中,每件事物似乎都一樣神聖,而且打開了千百扇讓我們能夠看見上帝的窗戶。」在《我們的國家公園》一書中,繆爾則是說:國家公園彷彿「一座宏偉的地質圖書館」(grand geological library),館中俯拾皆是上帝所寫的歷史。所以,其實這也是繆爾眾多面貌中之一:一個強調性靈的宗教作家。
有些出版社在推出他作品時就特別強調這一點,例如,李.史戴森(Lee Stetson)在1994年編了一本繆爾的作品選集,取名為The Wild Muir: Twenty-Two of John Muir's Greatest Adventures,書名原本不帶任何宗教氣息,但在2000年由國內張老師出版社推出譯本時,書名翻譯成《國家公園之父:蠻荒的繆爾》,封面上還加了一個副標題「二十二篇讚嘆造物主發明的歷險文學」,森林環境學者金恆鑣為該譯本寫的推薦序還特別以「傳自然的福音」為標題。
類似的做法,也出現在哈爾濱出版社於2005年推出的繆爾自傳譯本。他的自傳原書名是The Story of My Boyhood and Youth,但譯本書名卻變成了《在上帝的荒野中》。我想,這也就是為何《約翰.繆爾的精神書寫》(John Muir: Spiritual Writings)的編者提姆.佛林德斯(Tim Flinders)會在導讀中特別強調繆爾「逐漸把自然世界當成揭露神性的天書」(“came to view the natural world as a revelatory scripture to the Divine”)。如此看來,繆爾或可被當成繼惠特曼(Walt Whitman)、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繆爾曾於1871年與愛默生短暫相處,後來兩人常常魚雁往返)以降的第三位偉大美國超驗主義文學大師。

張老師文化的《國家公園之父:蠻荒的繆爾》加上副標題「二十二篇讚嘆造物主發明的歷險文學」,強調繆爾作品的宗教面向。

哈爾濱出版社的《在上帝的荒野中》其實是繆爾自傳The Story of My Boyhood and Youth,但書名從宗教角度重新詮釋。
▌旅行探險作家繆爾
1867年,繆爾在印地安納州首府印地安納波利斯一家馬車零件商店工作,一眼遭碎石子擦傷,幾乎失明,但一個月後他的視力恢復,這也促使他將自己的目光移向田野和森林,於是從印地安納波利斯步行一千英里,穿越了肯塔基州、田納西州的森林,途經喬治亞州,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墨西哥灣地區,接著到古巴、巴拿馬,在巴拿馬橫越巴拿馬海峽,抵達美國西海岸,於1868年3月回到美國的舊金山。這次跨國壯遊更早於他前往內華達山山區牧羊的體驗,這時他年僅29歲,隨行只帶著《新約聖經》、英國詩人米爾頓的《失樂園》與蘇格蘭詩人柏恩斯(Robert Burns)的詩集,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他這趟壯遊的日記能夠在他逝世後以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為名出版。
透過這些日記體的文字,繆爾已展現出優異的觀察力,無論對於花草鳥獸、木石地質,都有非常透徹的觀察,不過這應該也得力於他在威斯康辛大學就讀期間努力研讀而得到的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知識。2012年,馬可孛羅出版社出版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的譯本《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歸類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中,這次與繆爾比肩的,不再是梭羅等自然生態作家,而是同一文庫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小獵犬號航海記》作者)、發現樓蘭古城的偉大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我的探險生涯》作者)、史上第一位搭乘帆船獨航全世界的加裔美籍船長約書亞.史洛坎(Joshua Slocum,著有《孤帆獨航繞地球》),讓他又搖身一變成為「探險旅行文學」大師。就像文庫策劃人詹宏志先生所說的,身為一位壯遊探險家,繆爾的方法簡單無比,就是「選擇我能找出的最荒野、森林最茂密又最省腳力的路線往南行,以能經歷最大範圍的原始森林為目標」。而且,在我看來繆爾就是要在旅途中回到荒野,對他來講回到崇山峻嶺與荒野,「無異於回家」。

《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隸屬於馬可孛羅出版社的「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又是另一個了解繆爾的角度。(攝影/ 陳榮彬)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超過十個中譯本的「山岳文學」經典
近年來,除了原創的登山類作品之外,有愈來愈多英美的山岳文學作品被引進臺灣,例如旅行作家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探索三千公里長阿帕拉契山徑後寫就的《別跟山過不去》(A Walk in the Woods)、英國自然、旅遊書寫旗手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的《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Mountains of the Mind: a History of a Fascination)與蘇格蘭山岳文學家娜恩.雪帕德(Nan Shepherd)的《山之生》(The Living Mountain)。甚至,在2016年還有一本與繆爾有關的山岳文學作品問世:蘇珊.羅伯茲(Suzanne Roberts)的《山女日記:約翰繆爾步道上的28天》(Almost Somewhere: 28 Days on the John Muir Trail)——據選書的紅樹林出版社總編輯辜雅穗表示,這本書推出的契機是戶外、登山類圖書銷售漸佳,走出戶外、走進群山之間的女性也愈來愈多,該書可同時滿足兩個訴求,而且又是美國國家戶外圖書獎(National Outdoor Book Award)的得獎作品。書中蘇珊.羅伯茲與兩位同伴一起探索的,就是優勝美地國家公園裡以繆爾的名字命名的一條340公里經典步道,途經國王峽谷、美國杉國家公園與西部荒野,精彩探索登山同伴之間、人類與群山之間的關係。

臉譜出版社的「山岳文學書系」就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了,書系推出的第二號作品就是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的全新譯本《我的山間初夏》。這本書其實是繆爾從1869年6月3日開始,一直寫到9月22日的日記,記錄了他與同伴從優勝美地中央谷(Central Valley)托魯姆聶河(Tuolumne River)以南出發到內華達高山牧場,再從那裡返回到中央谷的經歷。讀者若想有系統地了解繆爾的生平,不妨在看完《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再接著看這本《我的山間初夏》,因為他就是在千里壯遊之後才第一次進入他畢生鍾愛迷戀的優勝美地,在那大片山野中,繆爾經常伴著羊群連續幾日漫步於群峰、湖泊、峽谷、草場之中,只帶著極少的麵包,而且這是他與美國最經典的荒野的初次相遇,他用日記把自己的種種感知、感動,還有那種彷彿醍醐灌頂的震撼詳盡記錄下來,在這方面跟其他許多自然書寫作品都有所不同。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一書在臺灣與中國加起來總共有十幾個譯本,光是在臺灣就有以下三個: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在臺灣的三個譯本,出版的時代脈絡各自不同。(攝影/ 陳榮彬)
《我的山間初夏》除了收錄詹偉雄先生寫的精彩導讀〈赤子之心,不免澎湃:繆爾與那一世代人的十九世紀〉,從現今文化史與休閒史的角度把繆爾全新定位為「戶外活動先鋒」之外,我個人覺得書名的翻譯也頗具巧思,在十幾個譯本中是唯一把書名中“My”一字翻譯出來的,很能呈現出這本書的自傳性、與自然的親暱性。而且,書末還收錄了植物譯名對照表,可供有興趣的讀者查閱參考。(天下的譯本《夏日走過山間》也收錄了臺大植物系郭城孟教授審定的「植物譯名索引」。)
另外,讀者們如果想要進一步領略繆爾的文字魅力,也可以閱讀風雲時代出版社的《群山在呼喚》(范亦漳譯),這本書其實是繆爾的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加州的群山》,1894出版)與The Yosemite(《優勝美地》,1912出版)兩本書的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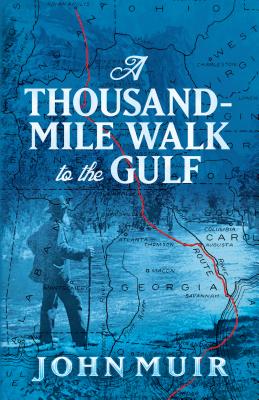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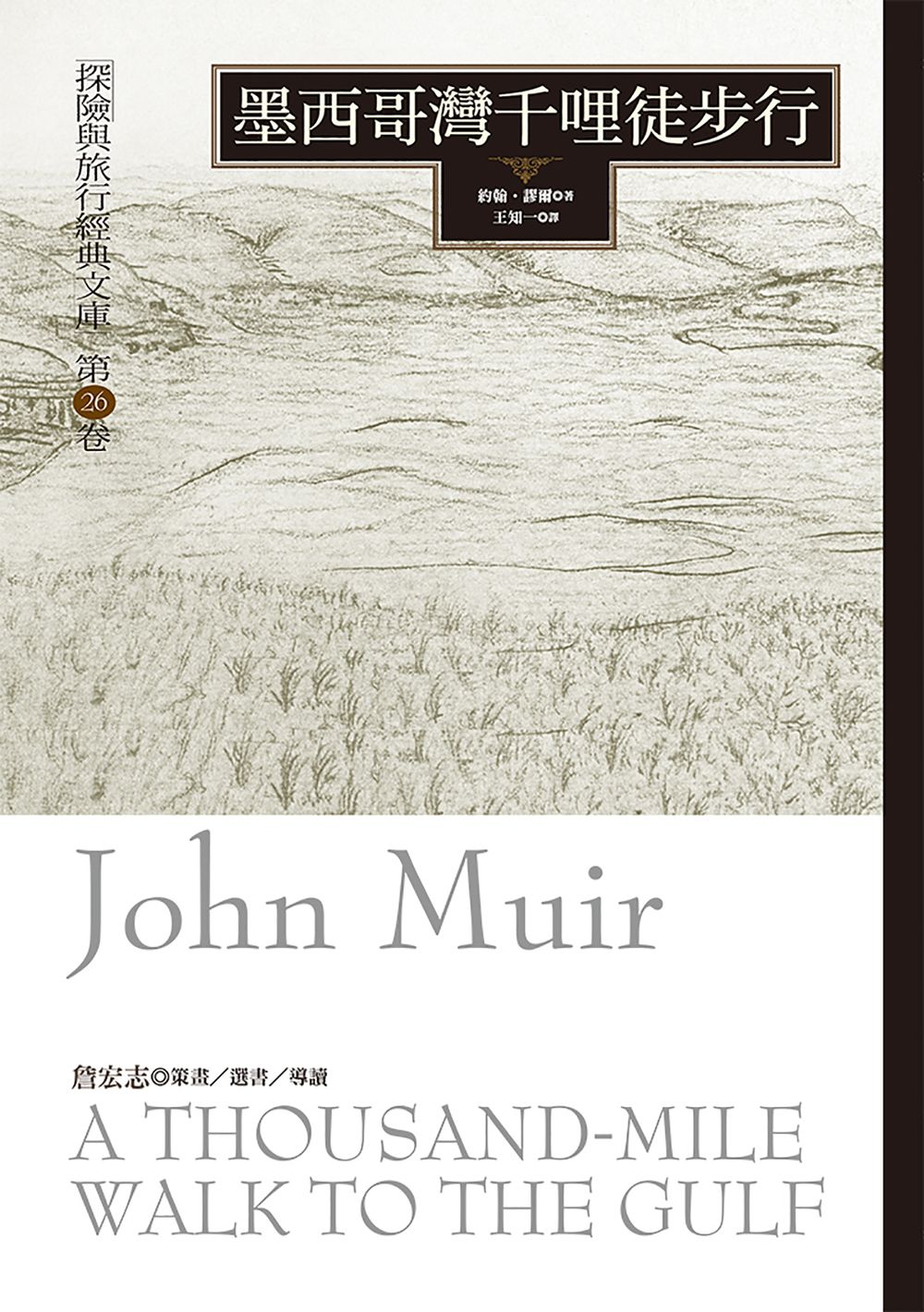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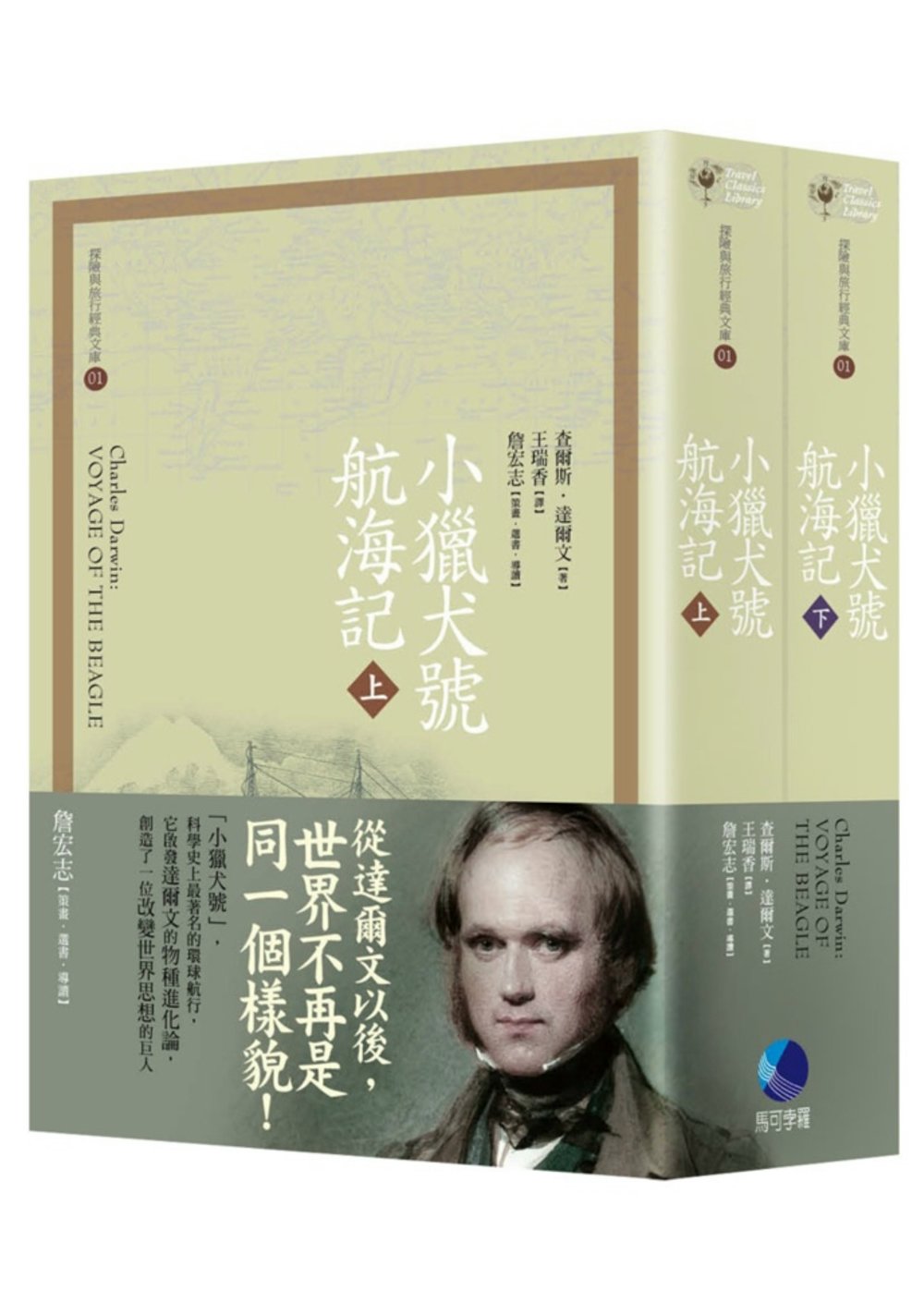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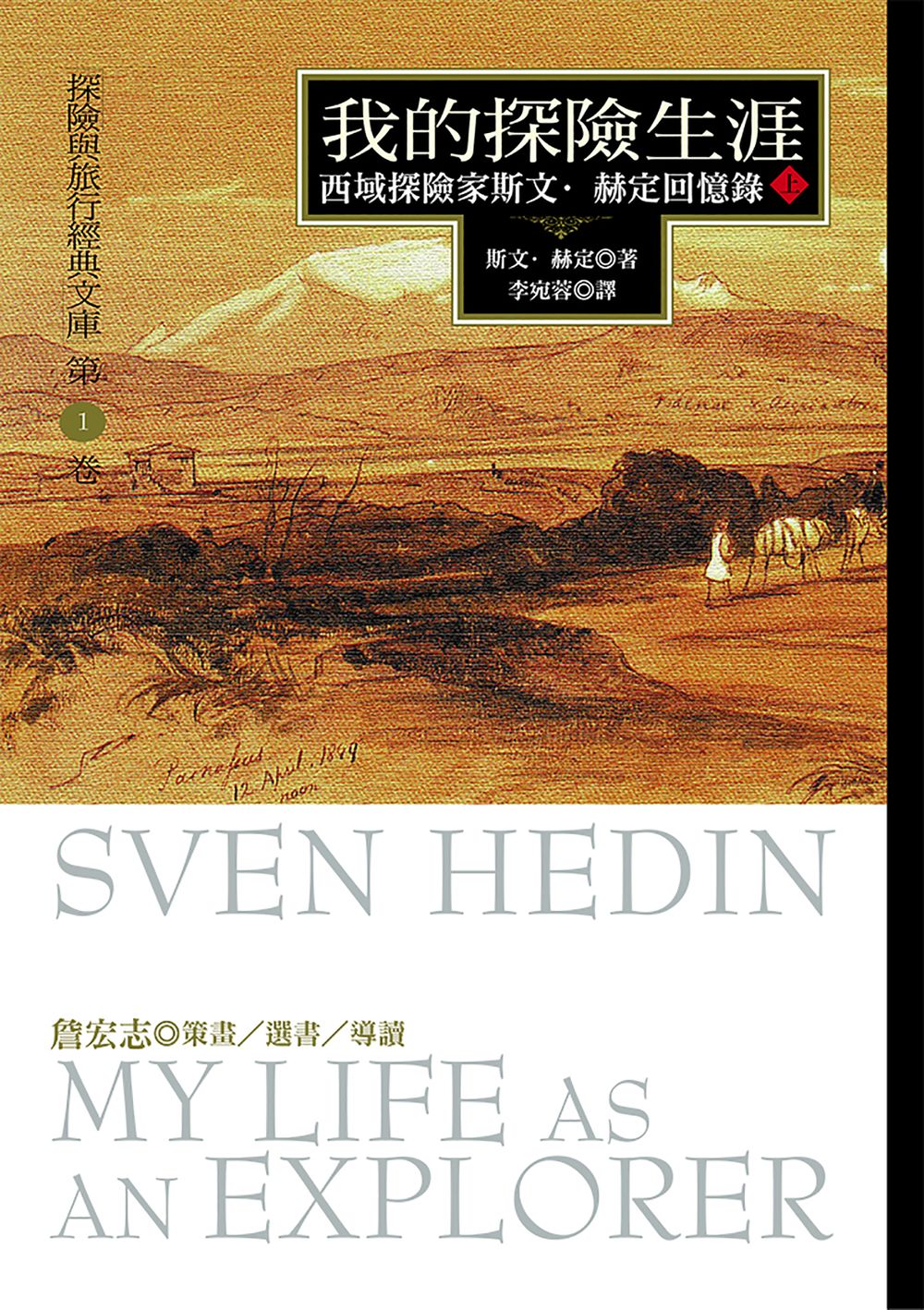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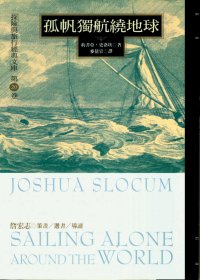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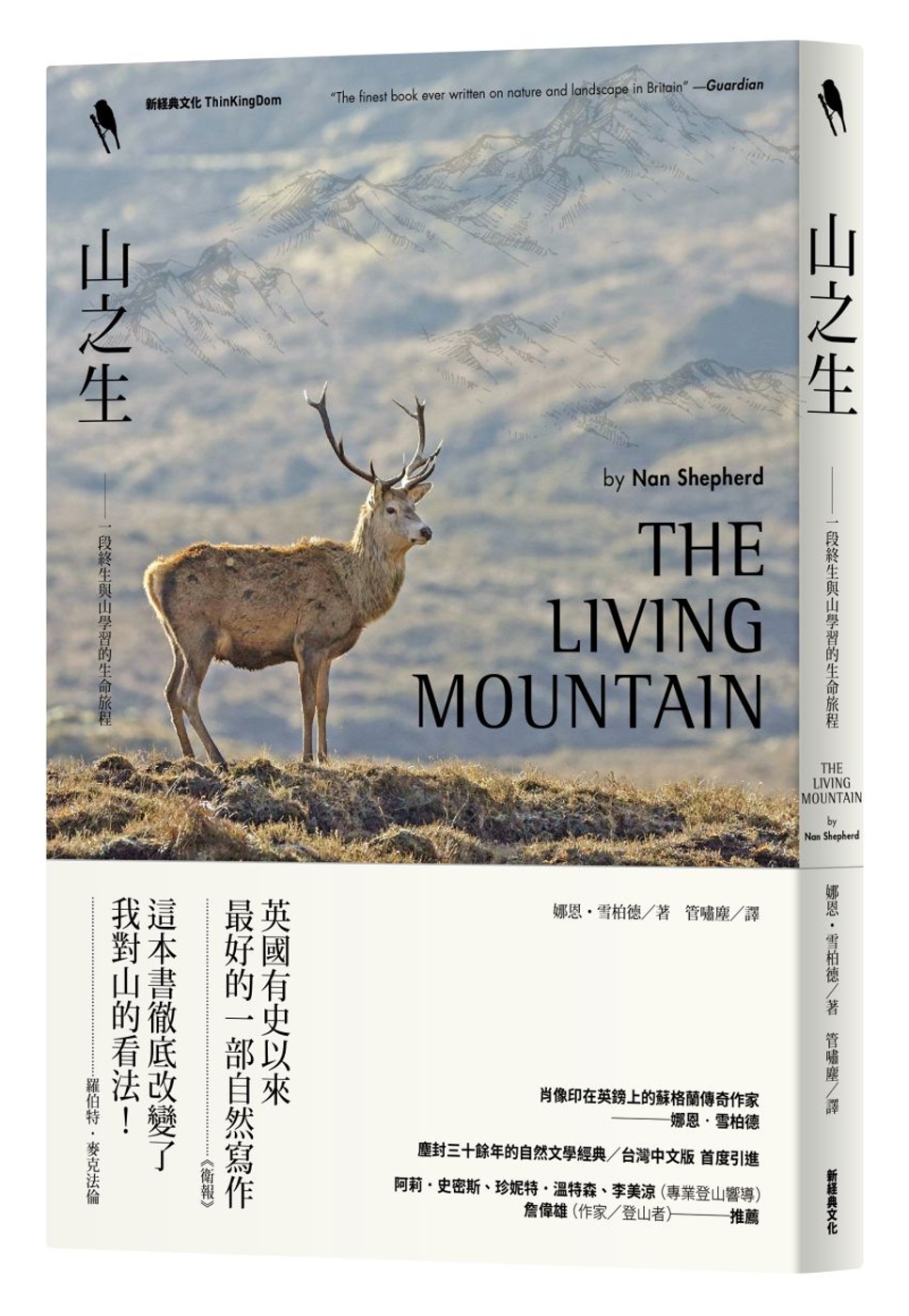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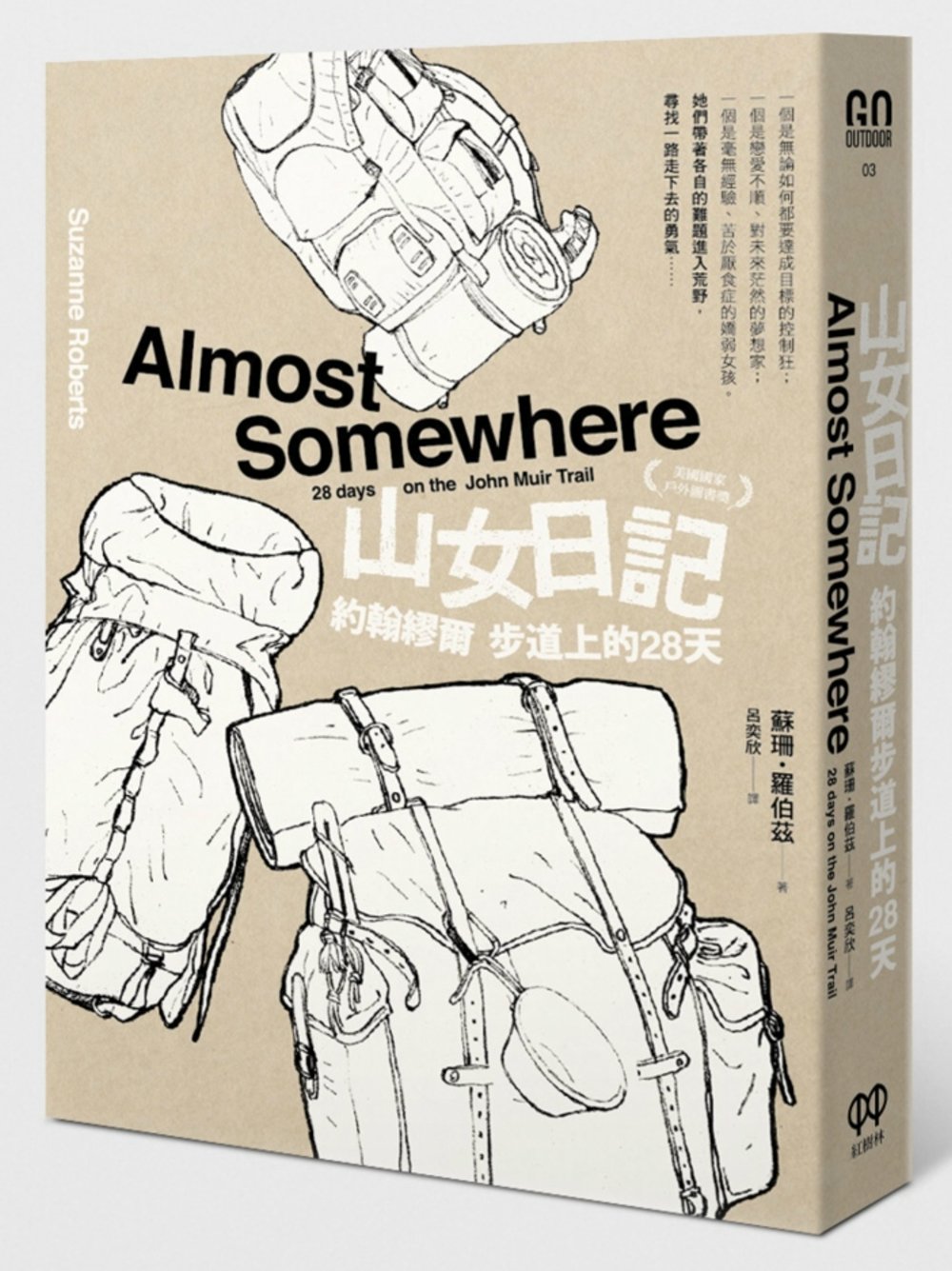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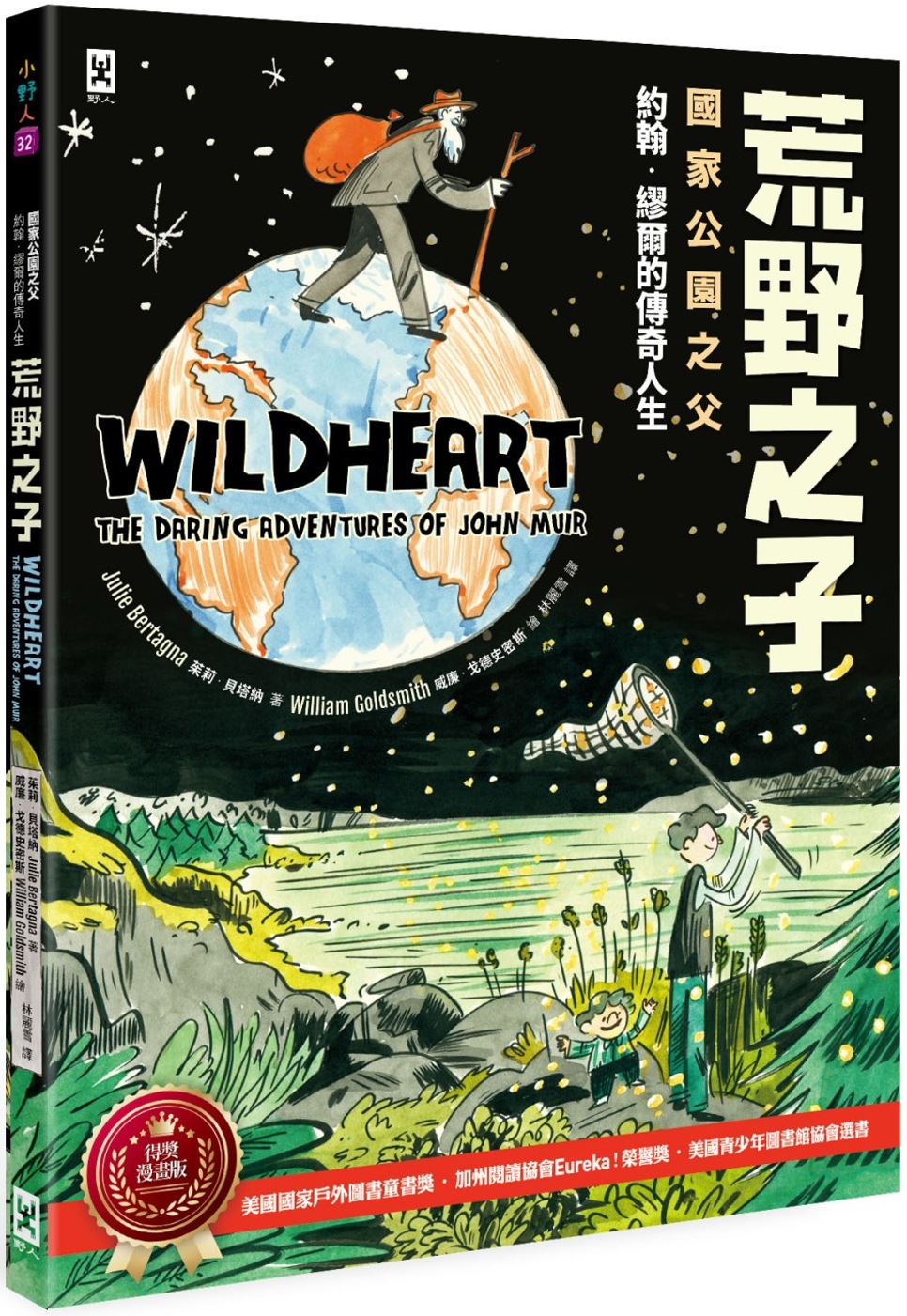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