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Q多麼像《第二爐香》裡的羅傑.安白登,小天地裡取得位置,離地,但相對安穩,普通生活行禮如儀,而正是這種生活裡一點點不對,就將人生撞歪了軸線。教授Q生活於回歸後的「陌根地」(影射香港),生活網絡由南方語言(粵語)、剎難語(漢語)和維利亞語(英語)交織而成,這三種語言具有不同位階與政治意義,恰恰顯示出該地歷史與地緣的複雜程度;因此,教授Q注定日子要比張愛玲筆下殖民地大學裡的學者來得難過,他的問題不是老像一隻白鐵小鬧鐘那樣轉,威脅來自一種更親近、更高遠的目光,監視並襲奪個人自由,無所不在。
在《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這部小說中,教授與至少兩位主要女性的關係,可以歸類為「現實─瑪利亞」、「欲望─愛麗詩」這兩大塊。瑪利亞潔淨寡欲,完全受陌根地殖民地教育長大,以「清麗、標準的維利亞語」作為標誌,聖母般降臨到他的生命,森嚴如他的出身所能獲致的最神聖境界;愛麗詩則延續了教授人偶收藏的嗜好,只是這一次,他不以擺弄人偶為滿足,還進一步希望能與栩栩欲飛的愛麗詩真正像人類男女那樣纏綿。可是,他同時鎖住了愛麗詩,他知道強烈欲望不能直接攤開在現實中。那是暗黑衍生物,內裡柔軟膨大的芽。可是,「欲望─愛麗詩」越來越強勢,不是愛麗詩要求,而是教授Q越來越無法按捺自我,想解除與「現實─瑪利亞」的契約,才能完全沉浸於總是任他探索深入的另一個女人/偶。規範世界裡的模範生瑪利亞,長期剝去了想像力,跟蹤丈夫看見他來到祕密房間摟抱著的竟是一個人偶,她只想到他病了,而未能對此病癥做更深層的解讀。
當教授Q沉迷於愛麗詩,罷課行動與暴力鎮壓正蔓延在他所任教的孤舟大學裡外,但他幾乎無所見聞。把他從欲望的太虛幻境拉回來的,是大學管理層一封約見通知信。那封信等於權力階層不容拒絕但仍偽裝禮貌的呼召,接下來,教授Q發現他被懷疑與某些政治陰謀有關,專門用來與愛麗詩度日的教堂也被查獲了,審問他的男人們想利用那座教堂做為破口,突擊影子地帶。搞革命的大學生們,正受到影子地帶庇護。軟弱的Q還想先取回私人物件,然而老大哥及其分身的笑聲,否決了請求:「有時,我也喜歡做做夢,好平衡一下苦悶的現實。但夢中發生的一切,無論如何是不能侵入現實的,如今,假借我們之手,正是毀滅你做過的夢、毀滅罪證的最好時機。」Q本以為夢幻絕對私人,小說至此,意義昭然若揭:在不斷進化的獨裁底下,公與私沒有不移的隔線,只要老大哥認為有必要,認為緊急,隨時可以取消那條邊界,羅織即宇宙。(想想才剛公布不久的《國安法》施行細則!)
這樣看來,Q可說是中產香港人的縮影,在越界、無差別的騷擾中(如此即時、富有既視感,在商場中喝午茶的教授也被按倒在地),才醒悟到他自身命運與陌根地所有的人都是一體,無法自外於「遠處有一團團慘黃的煙霧,其中走出了一排烏黑暗綠的生物,牠們有著鋼鐵蒼蠅的複眼、嘴巴是一個突出的口器,卻僵硬地擺動著人形的身體,正一步一步地向你們迫近」的絕境。至於仍有夢的陌根地居民,比如那些革命的學生,被風與光催醒的人偶們,Q沿著那個神祕袋子、異界入口,來到陌根地的影子地帶、一座城市的前意識裡,一個跳舞女孩向他解釋,在這裡居住的,不是人偶,而是機器做夢人,想活,但不想當人,通過做夢的力量,「來超越現實的界限,來武裝自己,把自己變成像機器一樣強大的人」,他們可以活動,但也可以長久不動,前者與後者,都由個人決定。可畏懼的是,那不允許自由說話行動也不允許自由沉默的未來,不就已經來了嗎?
從西西筆下的肥土鎮,董啟章的V城,到謝曉虹的陌根地,通過另起名字,拉開虛構與紀實的距離,增添曖昧中的針砭,託言夢幻,編織異境,其實遮蓋是為了指明,在煙霧中本體更為澄明──已成為香港小說家的拿手技藝,以及寫作上的不得不然。鷹頭貓作為Q的影子少年/詩人,久已於成人生活被沖刷,在這陌根地如戰地的此刻,竟因為催淚彈與愛欲的召喚,魂兮歸來。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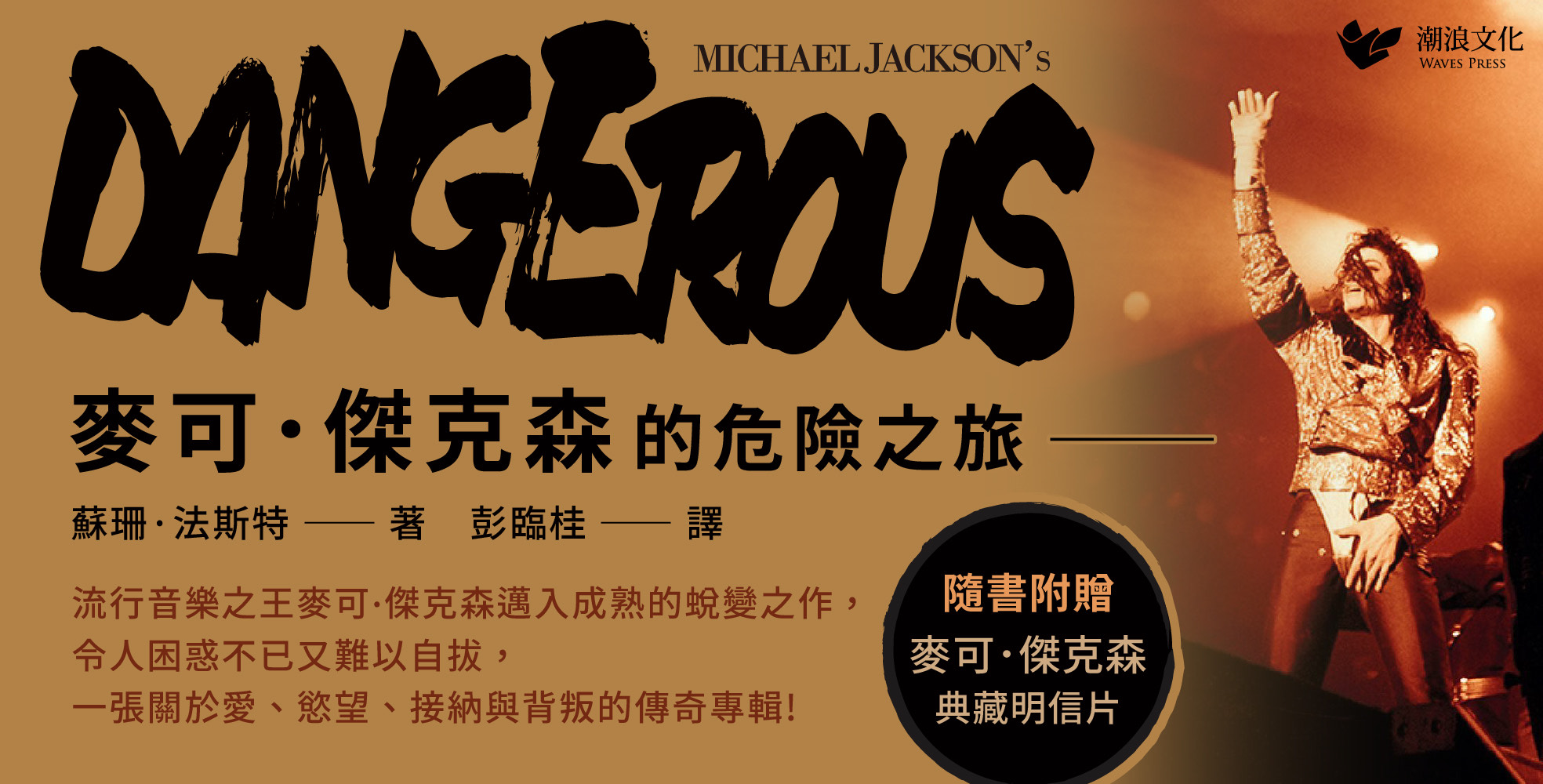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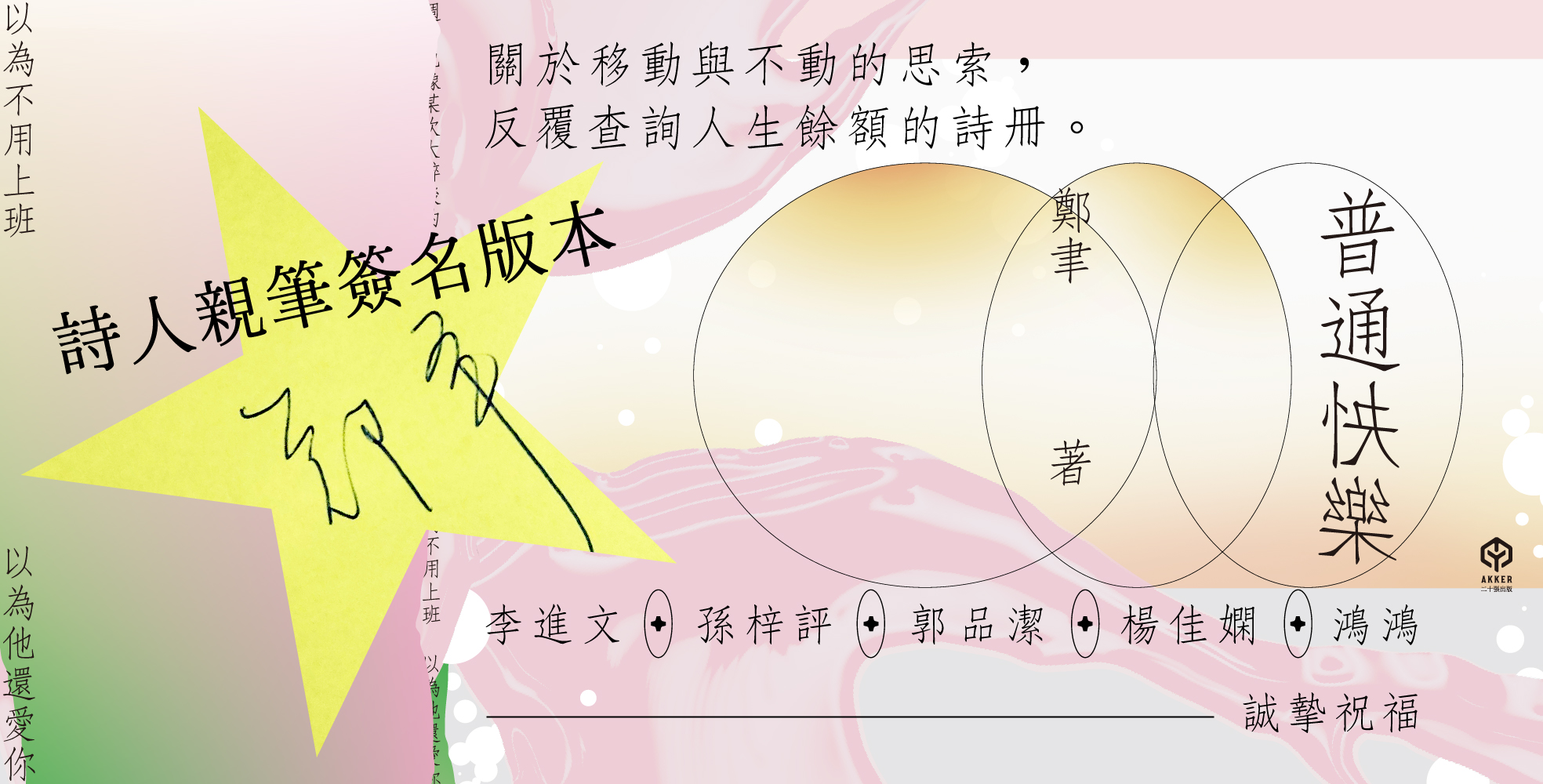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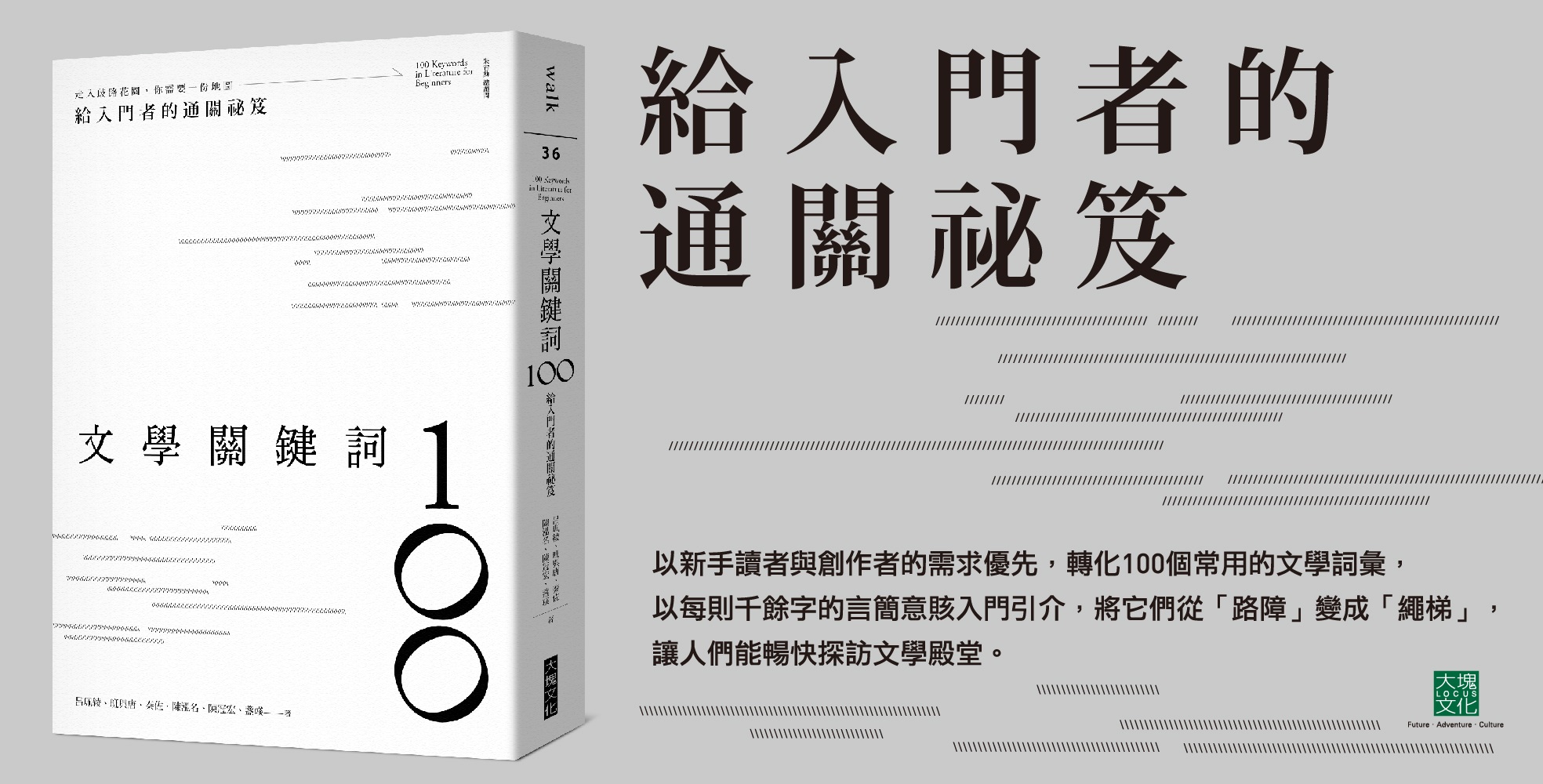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