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為新竹區具代表性的高中文學獎。由新竹女中、新竹高中兩校輪流主辦,至今已邁入第三十一屆。在一年一度的文學盛事中,每位對寫作寄予極高理想熱情的學生,都期待藉此機會彼此交流、自我提升。文藝獎徵稿新詩、散文、小說三組文類,本次刊登的是三組首獎作品。
青春大作家 ╳ 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 ╳ 小說組首獎

每座城裡,都近乎必然的有個瘋子。
以前母親騎車載我四處兜風的時候,常常提起這些。
那些日子的微風在我臉上吹拂,一想起便喚起心臟微微的震動。那時的我輕輕敲擊摩托車尾部的握把,不去在意任何一道夕陽殘喘消逝,一切可以是如此的簡單。
那些瘋子各式各樣,有的對一旁的空氣碎念,有的在街上咆哮。那時我總猜想著他們回到家裡又會是什麼樣的生活,他們會倒臥在沙發上,揮舞著遙控器嗎?他們會清掃地面上的灰塵嗎?
其中一個瘋子常引起我的注意,他的嘴唇乾癟,兩眼卻是如晴天的藍。
他矮小而黝黑,肌肉卻意外的結實。他每天會跑遍整個市中心,從清晨到傍晚。他騎著一台生滿鐵銹的腳踏車,沿途高喊。他的聲音宏亮,像是要喚醒所有睡著的人一樣。他準時的經過每一個廣場和大樓,像是另一個康德,對於時間的忠誠難以動搖。他頭上一定會戴著一頂磨損的橘紅色鴨舌帽,在車站前的人群中看到那頂帽子如蝴蝶一樣輕盈滑過時,可以看看手錶,上頭一定是三點整。
難得今天是父親的車來接我。我把頭探出車窗外,太陽在對街的房屋上堆疊出搖擺扭曲的陰影,從馬路另一端飄來有柏油氣味的風撫動我的頭髮。戴紅帽子的瘋子騎著車通過,一如往常的吶喊,他繞過行人和停在路邊的摩托車,如在台上翻滾的舞者。我問父親,那瘋子是不是家裡發生了什麼變故才變成這樣的?
父親的車穿梭在高樓的影子間,他忙於注意對向的車流而沒有回答。
班上的那女孩撐著傘走回家。
我將眼神稍稍橫移,爾後又很快的將視線轉至攀爬牆壁的藤蔓上。那眼球的軌跡恰如藤蔓的葉,隨風飄起後又隨興落下。我不想要她發現我看著她,因為我甚至還沒想好怎麼接近她。雨滴打溼學校的圍牆,水滴匯集至凹陷的角落,浸泡在那處熟睡的雜草。行道樹的樹根在雨水中變得光滑,散發苦澀的氣味。
我倆距離三大步,好似我們未曾說過話,或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有如宇宙兩端的兩粒石子。當她走入小巷前,她回頭望望四周;她的瞳孔游動在空氣中,彷彿裡頭住著什麼。
等到她的後腳也踏入了巷子。我才意識到,那只傘下還有別人。
回到家裡,餐桌上已經擺好了晚餐,兩只碗和兩雙筷子在橘黃的燈光下閃耀。母親總說我專挑某些菜吃,體格也因此比別人小上好幾圈。母親睡著後,父親才回到家裡,看報紙配著冰箱裡的剩菜;當我半夜爬起來喝水,總會看見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墜入夢境,白色的燈泡照亮他丟在一旁的公事包。我覺得父親大概是太繁忙了,而難以趕到那張在橘黃光線下的餐桌。
十點的時候我剛洗好澡。沙發傳來父親的鼾聲,時鐘的針顫抖著移動。我望向窗外,從這裡可以看到社區的大門外,我看到戴帽子的瘋子騎著腳踏車回家,此時他沒有吶喊,搖搖晃晃地前進,兩眼望向天邊,彷彿那裏有其他人看不到的事物似的。秒針劃過時鐘的頂端。我望著夜空一邊聽歌,趴在床上讀三十分鐘的小說。家裡的冷氣冷得像的真空,而裹在被窩中的我就像一顆漂浮的小隕石。
我想起方才母親洗碗時,她甩乾手上的水珠,開始在一本棕皮的筆記本中寫著明天要採買的東西。抹布、衛生紙和蔥。廚房的燈泡壞了一顆,另外兩顆也開始閃爍。母親凝視著筆記本裡的花紋許久,突然在一處角落畫下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
我和女孩唯一曾有過的互動,是在剛開學的某個午休。
頭頂的風扇打轉,依然揮不去教室裡的悶熱。我用食指撫著粗糙的桌面,一面讀著希臘神話。我聽到後方有腳步聲接近我,爾後是一段氣息扶在我肩上。
「你覺得,祂們存在嗎?」女孩小聲問到。
我歪著頭,想了想。我好像也只是單純為了打發時間而讀,從未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女孩見我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又問:
「那你覺得,如果祂們存在,我們能見到祂們嗎?」
這兩個問題和女孩的微笑,從此烙入我的腦中。
去學校的路途上,我又遇到那個戴紅帽子的瘋子,他騎著車經過我身旁,搖著手吶喊。路邊的孩子們喊著他,對他做鬼臉,他依然用一貫的的力道踏著踏板,持續搖手吶喊著;還穿著睡衣的老伯從窗戶探出頭,大喊著要那瘋子閉嘴。他依然維持一樣的速度,也從未脫下他的帽子。
沉悶的教室內,我轉頭望向其他同學,有人趴在桌上把頭埋進雙手中,有人則是用臂膀撐著頭。我伸展筋骨,使自己的身體脫離剛醒的痠疼感。粉筆撞擊黑板的聲音孤寂地迴響,砲彈如雨一般落下時的聲音。教室的另一角,女孩抄著上一節課的筆記,她的筆凝在空中,瞳孔抓著行行文字中的某個點。我不自覺地把手上的筆下壓,呼吸也變得緩慢。
自動鉛筆的筆芯啪的一聲斷裂。斷裂,我望著筆尖低語著,斷裂。有什麼將要斷裂,在他們的心臟,或是在我的心臟裡。
週末到來。為了打發那些過剩的午後,我在家中老舊的置物櫃中翻找著。我從塑膠袋中取出一疊照片,裡頭是少女時的母親。照片裡的她留一頭黑色的長髮別著髮夾,黑色的基底,鑲上橘色的水滴狀裝飾。她開朗的笑著。那時的她好美。
我在置物櫃的最底部抽出幾本畫冊,裡面滿是速寫和水彩畫,有超過一半以上的畫裡都有出現蝴蝶,各種顏色的、特寫的和遠看的。筆觸生動,畫面上事物如飛躍的舞者被凝結在空中,不知道那條河何時會繼續流動,也不知那幾隻蝴蝶何時會在不知何時繼續閃爍的陽光下繼續顫動粉色的翅膀。每幅畫都在右下角簽著母親的名字。最後一冊卻有將近一半的畫被撕毀,從殘骸中能看出是之前幾冊沒出現的炭筆素描。
家裡書櫃的角落有個上鎖的盒子,每次我試圖打開它,母親總會將它拿走並藏到別處。那時的她眼神急切的如被追捕的蝴蝶。
正午,戴紅帽子的瘋子走進公園的廣場,張開雙臂,對乾涸的水池發表演說。影子在水泥地上波動如海面的起伏。坐在涼亭的老人只是咂咂嘴,彷彿已經看這齣戲幾十年了。
太陽將水泥地照出令人暈眩的氣味。
瘋子對水池旁的榕樹一鞠躬,喊著明天仍會在同一時間出現,並預告演講的內容。
窗外的陽光穿透窗戶,熱辣的打在我的背上,將我一點點的蒸發。
父親打開家門,微微的喘氣,到廚房到一杯水喝,他的汗衫胸口處有被浸濕的痕跡,但我記得車上的冷氣才剛送修過。父親看到我手中的照片,眼神突然凝聚了一會,像是像機聚焦的鏡頭;他閉上眼,將水一口喝盡。
我收拾著置物櫃裡翻出的東西,照原本的順序放回。望向海的方向,凝視著一朵雲飄過,我想起班上的那個女孩。用手托著腮的她,在我的腦海中微微笑著;她撩了撩她那綁法簡單俐落的馬尾,又把目光放回桌上的筆記;教室的風扇無聲的打轉,光從燈管上黃灰的污漬間灑下。等我回過神來,天空已經被燃成一片橘,灰燼的部分則是艷麗的紫。父親的鼾聲從臥室傳出,像是潛水者從水底吐上的氣泡。
母親剛從市場買菜回來。紅條紋的透明塑膠袋歪著腰坐在桌旁,家門的鑰匙落在不遠處磁磚的交界線上。母親手上拿著父親的手機,手指定時的滑過螢幕,好似一根時針;藍色的光暈染在母親臉上,讓她看起來像是海裡白化的珊瑚。
水槽裡杯盤疊成小丘,油漬和醬料痕蔓延著,沒有任何的水紋打擾。出水口旁乾燥的像是被午後的陽光給曬過。
週三的傍晚,我在車站等母親來接我。
我坐在平滑的石平台上吃著三明治,裡面的蛋發著令人作嘔的味道,不是腐壞了,而是我感覺我的胃在抗拒它。我兩三口將三明治吞下,舉起水瓶灌了一點水到喉嚨中,混著麵團快速的滑入胃中。女孩在斑馬線那端等著紅燈熄滅,直挺且不動的站著,我看著她的馬尾發愣。她像是被陣風吹動的樹葉,突然回頭,焦慮積在她的眉頭上。似乎是沒等到人,她左右看了看,決定在燈熄前橫跨馬路。
等她閃過了幾台車到了安全島,我才發現原本在我手上的水瓶不知何時落到地上,沒喝完的水瞬間成了一座小湖。一旁傳來大笑,我用眼循著聲音的來源,卻看到了那瘋子。他用左手食指指向我,又用右手比向掉落的水瓶。我才意識到,他早坐在同一個石平台上了。
而今天卻是父親來接我。我詢問母親為何沒來,他的眼神落在方向盤上而沒有回答。等了五分鐘,他才踩下油門;一句話也不說,像是剛從夢中醒來。
睡前我因為口渴而走到廚房倒水,發現母親坐在桌前。她的手指反覆敲擊著手機鍵盤。在冷水注滿我的杯子前,她掛斷語音信箱,又開始按起號碼。突然間母親停下她的動作,凝視著櫥櫃裡的時鐘。
她又按了螢幕一下,這次加重力道,長久而不願放開。
母親走去陽台,趴在圍欄上。隔著玻璃窗我看見滿月下的母親,如初戀的少女一樣笑著,也像剛失戀的少女一樣哭著。她的神情讓我想起那個雨天裡班上的那個女孩回頭張望的眼神,她們眼裡都帶著某種渴望,如剛點亮的燭,亦如剛學會飛翔的蝶。
覺得家裡少了聲音,一種低沉而穩定,但又有些吵雜的聲音。或許是冰箱今天比較沒有噪音吧。整個家的重量感稍稍的減輕,逐漸在脫離引力的掌控,飛向宇宙的彼端。我想像整個房間從大樓中如磚塊一樣被取出,滑過土星和冥王星的表面,邁進遙遠的塵埃間,偶有幾束星光照亮家門。最後,在接近北極星時漸漸的消逝。
差不多是少了一個公事包的重量,我想,但更衣室裡的體重計量不出來。
那天晚上,母親望著筆記本發愣,從我的房間可以看到母親房間的小檯燈亮著,不時傳來原子筆的劃記聲。我窩在被窩中想著女孩,已經是隔天的凌晨了,這時本該在廚房吃宵夜的父親卻尚未回家。
半夜,我從母親的書櫃中的一角挖出那個盒子,紅銅色的外殼,上黑漆的鐵栓,散發淡淡的腥味,刺痛鼻子的深處。緩緩地打開,金屬摩擦的聲音在半空中震盪。盒子底堆積層層紙片,我翻閱著它們,卻發現它們是好幾幅被撕碎的炭筆畫,掩埋一本棕皮的筆記本,前半本寫的是關於繪畫的筆記,卻在中間的地方,突兀的停住,而後便是一片空白。而停住的日期正是父母結婚的那天。
我將成堆的碎片拼回,那是一隻被火焰吞噬的蝴蝶。
臥室那邊傳來噪音,我趕緊收拾。此時卻有片東西,羽毛似的飄下。
戴紅帽子的瘋子開始了他一天的例行公事,騎腳踏車在魚肚白照耀的柏油路上歌唱。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變化,沒有動機或著如骨牌的因果。他像是完全獨立於這個世界,超越了整個銀河。他或許心底有和我相似之處,都有著某種期待,並把這份期待投射至某種實體上,那可能是一台腳踏車、一本筆記本、一只公事包,甚至只是一道一閃即逝的影子。有一段鋼索繫住了我這份期待,要是另一端有所震動,我心臟旁的血管也會以同樣的頻率回應;但那瘋子的期待則像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可以任意的擺布。換句話說,他的期待來自他期待的世界。
母親發現書櫃裡的盒子被人翻過了。
餐桌上的氣味被寧靜蒸發,母親直盯著我,像是在思索下一個問題。她手中握著照片中那只髮夾,她的大拇指用力地搓著它,來回著像是在畫圈似的。
「為什麼動我的東西?」
我沒有回答,我想起那晚在急忙地收拾中,那本小筆記本掉出一張照片,照片裡的人是母親年輕的時候,但擁著她的人不是父親。空氣突然重重的壓上我的背。我輕輕咬著舌。
「那天,妳打電話給誰啊?」我問,母親倒了一杯水,沒有回答。
寧靜已經擄獲了整個室內,還意圖持續擴張。它啃食所有接觸到的存在,咬成碎屑,再大口吞下。像是那幅畫中的火焰,慢慢吞噬著蝴蝶
「你覺得,凡人和神差距多遠?」母親喝完那杯水後問到。
我完全不懂母親為什麼要問這個,但這問題卻狠狠擊中了我心中的某處。
午飯後,父親頹坐在木椅上,他今天不用上班。他宛如一只木偶呆然地瞪著窗外,連呼吸都停止似的寧靜。他突然大笑起來,聲音在廚房裡來回碰撞。原本正在洗衣的母親走進客廳望著廚房。
「怎麼了?」母親問。
父親抬起頭,那眼神好似完全不認得眼前的兩個人。父親看向餐桌,又笑了起來,這次是痴痴地笑。過了十分鐘後他已經癱倒在桌上睡著了,而沒有發出鼾聲。
女孩數天沒來學校,整間教室像是少了一份重量。像是秋日裡少了一片落葉。聽說她將成為另一個源頭、另一個端點,在低空懸浮的詞語滋滋作響,大力震著我的耳膜。昨日還是新月的她,今日就成了滿月,而我還活在新月的黑夜哩,反覆歌唱沒有聲音的歌。
凌晨的時候我猛然想起,某個大雨的日子,女孩的傘下還有另一個人,他倆的肩緊緊挨著彼此,好像急於和對方合而為一。
在被窩中我的手向下延伸,我盡力的去想著女孩,想著她的臉龐和嘴唇;但每當想到她的眼睛,羞恥像洪水一般填入我的心頭,此時我變得無法硬挺。於是我只好閉上眼,皺著眉在腦海中尋找其他多汁的、悶熱的畫面。
她距離我太遙遠了,遠到我甚至無法了解她身上有什麼能帶給我如雨一般的滋潤。大概是我太膽小了,不敢去傾聽那些來自千個光年外的喘息和笑聲。對我而言,她處於樂園的中央,而我只是世界盡頭的崖邊的一株草。
汗珠延額頭流下,我很慶幸我沒有夢到女孩,但為何淚積在我的眼角?為何我在清晨失眠了?
瘋子回到了公園,重複了之前所做過的事。鞠躬,然後演講。今天的講題是「論何謂阿基里斯」。
他在演講後卻沒有馬上離開,反而爬上附近的一棵榕樹。他抓緊氣根,在樹枝間穿梭,為了不讓自己掉下去,還不時的用腳抵住樹幹粗糙的表面。當他成功地站上伸的最長的樹枝上時,他張開雙臂,閉上眼,像準備演講前那樣,不禁讓我想起某些雕像。當他將手臂完全伸直的那剎那,風逐漸轉強,刮動整片公園的樹葉,發出像急躁翻動紙張的聲音。
昨晚的失眠中,我聽到客廳傳來了這種聲音。如一隻貓,我貼著牆緩緩前行。母親蹲在客廳的書櫃旁,從那盒子中翻找著。挖開成堆的素描紙,迅速撥動筆記本的每一頁,最後終於在盒子底部的角落找著了那張照片。母親凝望著它許久,像是在灰塵飄落且黑暗的房間,看見了唯一亮著的檯燈。窗外的天空滿是深藍色的烏雲,像是家裡的霉味沉重的凝聚。
前門打開了,父親跨入家門。他看起來喝過了酒,滿臉通紅。前胸的襯衫被扯開,有幾個扣子已經不見了。他和母親兩人對著眼,除了細微的呼吸聲外,一片寂靜。
父親和母親各坐在餐桌的一端,兩人的眼神浮游著,餐桌上沒有食物也沒有藥品,空蕩一片如無人居物的原野。我撇見父親腳邊的公事包是空的。父親的襯衫上有股香氣,有別於母親身上的氣味。我想,約莫是公園裡的野花的味道吧。
母親似乎要說什麼,她的嘴唇才微微張開,父親便用力槌響桌子。母親流著淚回到臥室。從我的房間可以聽到微弱的、撕裂紙張的低語。我踮著腳尖走到門縫旁向母親的房內看去,橘黃的夜燈下,母親將她的筆記本撕碎,大小不一的紙片佈滿床單,她將那些碎片聚集起來,往頭頂丟去,望著它們如雪花般下。透過朦朧的光線及旋舞的紙片,母親似乎試圖將自己回朔到某一刻,於是她一再的重複著這些動作。上拋,望著雪花,上拋,望著雪花。
母親撇見了我,她像是剛從夢中醒了過來,停止了手上的動作,眼神愣愣地盯著前方。像是她習慣的世界漸漸崩塌了。
我走入廚房,父親一雙眼瞪著我,但當我看像他的公事包時,他卻突然慌張起來,把公事包緊緊擁在懷中,整個人轉身背向我。
風聲停了,瘋子仍維持一樣的姿勢站在樹枝上。
陽光成片的貼在他身上,此時的他看起來像是剛誕生的神祇。祂呼吸著此處的空氣,卻不需要將它們留任何一丁點在肺裡。我走向祂所在的那棵榕樹,他卻如風一般回到地面,離開了公園。
他沒有預告下次的演講內容。
週五的晚上,父親說自己去加班,母親出外採買要傍晚才回來。
一個人出外買午餐,外頭正下著雨,我撐起一把深藍色的大傘,在如棉絮的細雨中前行。泥土和落葉的氣味在公園旁的人行道上漫步,天空的灰有如牆角的塵。我想起昨晚當我看向父親的公事包時,他慌忙遮掩的神情。公事包是空的,而父親的眼神也是。而母親頭上別了一只髮夾,黑色的基底,鑲上橘色的水滴狀裝飾。
雨天的小麵攤生意不是很好,胡椒的氣味刺著我的鼻。我結了帳,窗外一輛腳踏車如風一般穿過,是那戴著帽子的瘋子,他正在吶喊,巨大的聲音如雷一般在騎樓間呼嘯而過。老闆的手指敲著櫃檯桌面,講起那瘋子的事跡,從他在車站喊的話到他在公園某次的演講。
「他一直是這樣嗎?」我問。
「是啊,打從會說話大概就這樣子。」老闆回答,手指依舊敲著桌面,但節奏卻放慢了。
吃完飯沿著相同的路走回家。坐在書桌旁看雨,家裡唯一的光源是我的檯燈。雨滴變大了,落在窗戶上像是有人在敲門一樣。我原本期待那瘋子有個故事,但他是個完全的瘋子,在荒誕中活著也終將在荒誕中死去。那甚至不只是一種期待落空的失望,而更像是發現急切需要的事物根本不存在。
雨像墜樓的人,達到所需的速度後,摔進雜草旁的土讓。
傍晚,母親回來了,但她帶回來的卻不是蔥或衛生紙,而是一整袋的畫筆和顏料。
那天凌晨我被沉重的腳步聲吵醒,廚房裡癱倒在餐桌旁的父親醒來了。而另一邊則是傳來塑膠袋的翻滾聲,母親房間裡的檯燈亮起來了。
母親在臥室的牆上畫起成群的蝴蝶,她用手指塗抹,用畫筆沾上顏料潑灑。她時而張開雙臂,或著雙膝跪下。兩眼空洞無神,她彷彿正在祈雨的祭司,濺到身上的顏料則是意義不明的紋身。
在廚房那端的父親又開始癡癡地笑著,在客廳搜刮各種雜物塞滿他的公事
包,不管他放進了多少,那公事包在他手上看起來卻像絲毫沒有變重。他扯開襯衫的衣角,閉上眼拼命吸取上頭的某種氣味。
女孩的影子逐漸在我心裡盤據了每個角落。我甩甩頭,期望這無意義的動作能帶來什麼改變。那些影子變得流動、炙熱、使人窒息,但我依舊無法硬挺。
社區外的馬路上戴紅帽的瘋子騎過。我想起麵店老闆說的,他是天生如此。他在路上隨風吶喊,像是隻歡樂的蝴蝶。
「你是瘋子,瘋子瘋子瘋瘋瘋瘋,你是瘋子!」他喊著,我覺得他的話說只對了一半,因為我沒有像他那麼快樂。我如宇宙中的一粒石子,面對星夜陷入無盡的沉思,期望著擁有恆星的光,卻缺少了來自體內的一股熱。這裡沒有所謂正常人和瘋子的區別,在瘋狂中出生的他們早已對瘋狂免疫。
又想起了那些母親載我兜風的日子,那時的夕陽、那時指尖觸碰車殼的觸感。一切可以是那麼的簡單。
我衝下樓追著那個瘋子,我加快腳步,卻始終沒辦法追上他。他像一隻自出生起就知道如何飛翔的蝴蝶,熟知各種氣流,亂流對他而言也只是另一種階梯;而我像是剛從牢籠中被放出,雙翼上滿是各種傷痕及破損。我用力推動腿部的肌肉,腳底撞擊柏油路面。但我們之間始終維持著正好三公尺的距離,我放聲大吼,淚水順著我的雙頰向後飄出。瘋子聽到了那聲吼叫,回頭看著我,但始終沒有停下踩踏板的腳,速度也從未變改變。在清晨稀薄的空氣和陽光中,他卻開始笑了起來,和我吼叫的聲量相當。
或許凡人和神的距離就是如此吧,三公尺。
作者簡介

曾亦修│新竹中學
一杯溫水,配一本小說,如此消耗一個午夜。喜歡下雨的日子,或奪去所有哭嚎的狂風。無聊時會講關於存在主義的廢話。
主業是個怪人,兼任lofi重度成癮者。
看更多得獎作品
1.【青春大作家X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新詩首獎:孤兒
2.【青春大作家X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散文首獎:鯨落
3.【青春大作家X織錦文學獎】散文首獎:印
4.【青春大作家X中山女高織錦文學獎】小說首獎:保鮮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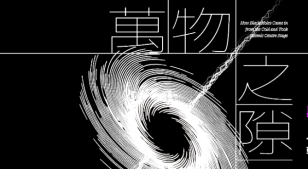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