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妮可.克勞斯《烏有》的日子,並不短暫。
學院與生活的訓練,不知何時,已將我的閱讀速率調至一種文學裡非必要的社會化,像巨型城市裡的手扶梯速度與行人擦肩引起的微小風漩,妮可.克勞斯時隔七年的新作,一出手卻將時間抽成真空,逼人思考,可能很久沒思考過的文學與人生,意為何又意在哪,但不提供解答。這不是常見的景況,一如《烏有》也並非常見的小說。
漫長而一再復始的閱讀裡,我經常想起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卻不是某部單一作品,而是我心中視為當代最佳西方論述文的那篇諾貝爾得獎致詞:〈父親的手提箱〉。不只是因為《烏有》的雙線敘事裡,與作者同名的女作家「妮可」,曾在小說裡與據說裝有卡夫卡遺稿的手提箱同行一段;更因作者曾在上部作品《大宅》(2010)的序裡,如此自剖她的小說結構:「構造出一個完整的架構——即使,或說尤其,我無法預期那將是哪一種架構。我在興建一棟房屋,一座城市,手邊卻無藍圖。」上下文般,與2006年帕慕克的一小段致詞稿接續首尾:「同樣地,一個人也可以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建起一座大橋或是大廈,我們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作家的秘訣不在於靈感——因為誰也不知道它來自哪裡——而是靠固執。」
妮可.克勞斯當然固執,她一向固執。從《大宅》裡西班牙詩人賈西亞.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的書桌,到這回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與他的手提箱,她固執的總在小說裡安插不同的作家,是卡夫卡、是羅卡、也是她,過去與現在的寫作者,唯一能共有與穿時的卻不是死物,最終還是得回到創作。《烏有》的出采之處,更在藝術品與創作者的私我辯證,不管是曾經權財傾朝,能在總統國宴上失禮中離只因尿急的猶太男人艾普斯坦,與《烏有》作者同名的主角猶太裔小說家妮可,我們看到小說家為著卡夫卡遺稿幾乎困死沙漠,送盡家財名畫只留一幅《聖告圖》於大宅的老翁,當一切堅固的煙散,當繁華化為烏有,被留下的還是極致的藝術。

妮可.克勞斯曾以小說《大宅》入圍「2011年國家書卷獎」。(圖片來源 / 作者官網 ©Goni Riskin)
真的是如此嗎、這樣就足夠了嗎?妮可.克勞斯固執地再踏前一步,還是不夠。她暗示著卡夫卡當時的死亡,不過一場天才編輯術,卡夫卡最終成了老園丁,在以色列大城特拉維夫住了好久。就像小說最終,艾普斯坦決定賣掉僅剩的《聖告圖》時,名畫卻在一場白日夢般地追鷹中,遺失紐約的公園長椅;卡夫卡的遺稿與皮箱,也比不上活著,被棄沙漠。意義推翻意義,思考無用思考,「天堂真實存在嗎?」,都比不過活著當下,這卻只是她小說的第一層。
小說的第二層,是廣袤的隱喻,豐厚的意象,以及它們相加相乘所逼顯的一座森林,森林可以喚作「民族」。在小說主角各自的人生困境,創作與婚姻、出生與終老的引領下,小說主角妮可與艾普斯坦都來到了特拉維夫的希爾頓酒店,美國連鎖酒店品牌在備受爭議的國家與城市,方正如林。即使,它其實沒那麼重要。雖然,妮可.克勞斯還是忍不住說了一些,隻字卻如萬言:「激發他幻想的並不是以色列可能真實,而是以色列不真實;唯有巴勒斯坦跟文學一樣不真實⋯⋯巴勒斯坦依然可被虛構。」
1948年5月,猶太人宣布以色列建國,在聯合國介入下,原先的巴勒斯坦國土被分作兩國。「以色列」原先做為猶太民族名,接著成了幾千年來第一個「猶太國度」的國名,巴勒斯坦則被派指回歸「伊斯蘭國度」。歷史與權力之下,真實竟比小說還靠近虛構,國土民族被指點創生,但那些可能發展出來的殖民思考、國族意識,比起特拉維夫、比起真正的森林,一切他人小說中拿來當作正餐的,左不過《烏有》裡的伴菜與配料。
打開小說的第二層,她的手提箱裡不大,堪堪裝下一座森林。《烏有》的原文書名Forest Dark,出自但丁《神曲》第一部《地獄篇》:
人生的路程走到一半
我卻發現自己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我已迷失明確的方向,不見眼前路。
MIDWAY upon the journey of our life
I found myself within a forest dark,
For the straightforward pathway had been lost.
而小說裡,艾普斯坦最後成功捐出的財產,是一片價值200萬美金的森林,只因他忽然對往昔發動想像:「曾有一時,整個地中海的南部與東部,從黎巴嫩直至北非和希臘,處處都是森林。」大地因戰乾涸,黃土取代森林,不管是深綠翠青或黑黯的森林色,都只剩沙土,
森林也可以喚作其他,因它總在說話、不停說話,它告訴我們,愛情與小說、事業與小說、家庭與小說,甚至民族與小說都好,行至中途與末路時,都得回到森林。小說裡,藉由艾普斯坦反覆咀嚼這個單字,妮可.克勞斯才略帶不甘地分享一些她的世界觀。「Forest。這個字他糊里糊塗地用了一輩子,直至此刻,他才意識到Forest其實是由For和rest組合而成。」在血緣的森林、文學的森林裡,回到源頭,只為休息。就像耶路撒冷曾確實被松柏、杏仁、橄欖圍繞過,最動人處,皆成烏有。
讀《烏有》得慢,就像看畫作與雕塑,總得先細細地看微處。比如15世紀波希(Bosch)的三聯名畫《人間樂園》,你得先尋寶似地看「人間」裡,誰偷偷穿上衣服,再退後幾步看盡全貌,天堂、人間與地獄,原來就是真實世界,甚至可以通達現代世界。

荷蘭畫家波西(1452-1516)《人間樂園》,從左至右代表伊甸園,人間樂園和地獄。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藏(圖片來源 / wiki)
所以我退開一點讀《烏有》,畢竟有那麼多的長椅與樹林、名畫與小說,甚至是小說主角童年在希爾頓飯店泳池底拾到的心型紅寶石耳環,退開一點,讓暗示與隱喻回到本位。如果可以,我們也不用非得將小說放進後現代,我希望它不是如此,因為它不只如此。
因為小說家幾近告白地寫道:「敘事承受不了無序,正如光明支撐不了黑暗。敘事是無序的反題,因此,任何形式的敘事都不可能忠實地傳達出無序。敘事始終得背棄混沌與無序,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你若想要架構出精緻細膩、揭示人生種種真實的敘事,你就必須捐棄真實之中鬆散紊亂的一面。近來寫作之時,我愈來愈覺得自己偏向炫技,而非書寫真實,我感覺自己強將無序變作有序。」這本小說,大約也是妮可.克勞斯的以色列森林,有許多看似對小說與婚姻的辯證,片片掉落。她一邊休憩,卻不放棄,「我想找到一種足可承受無序的形式,這樣一來,我說不定可以掌控敘事,追尋其中的意涵。」小說家請讀者退開三步,看她的人間樂園與浮世繪,三聯畫也似三層化。
小說的魔力,是否在忠實呈現人生?妮可.克勞斯與幾乎所有小說家所信仰的,或許不過是故事,因為「我們的心智始終想要創造一個可信的故事。」《烏有》也似是電影《婚姻故事》的解答與起源,「為什麼會走到那裡」的「為什麼」,其實並不存在。在生活成為故事前,話語一樣是無序的無帆之船,那些我們想要使用、不准使用、害怕使用、可能使用的字句,都是小說裡寫不出來卻想盡力靠近的敘事。
遠遠才能看見,《烏有》的第三層,原來覆蓋著厚厚一疊,吳明益多年前為《大宅》導讀時,所說的「哀傷的呼吸」。生命的哀傷已然昇華,猶太人不被祝福的新家園、婚姻與敘事巨獸般的無力嘗試,小說裡的妮可感嘆無法成為卡夫卡、小說裡的艾普斯坦也大約等不到那部大衛王電影的殺青,幸福、來世、迦南美地,都是烏有,可「烏有」在《烏有》裡,不是偏義複詞,而是相對相生,從無裡看見有。
「妮可」當然不是卡夫卡,她感嘆自己無法如卡夫卡的小說般,精湛凍結「即將之前的永恆」。但世界不需要兩個卡夫卡,在森林中間休息的小說家,那些沒有寫與寫不出的巨大,無聲地轟鳴,拖慢了我扶梯的轉速、閱讀長河的流速,有時我得蓋上書頁一會兒,才能再讀。
《烏有》就是這樣的小說,妮可.克勞斯是寫出《烏有》的小說家。
作者簡介
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 2017年出版《寫你》, 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OKAPI專訪】散文是「看自己」和「怎麼被看」的遊戲──蔣亞妮《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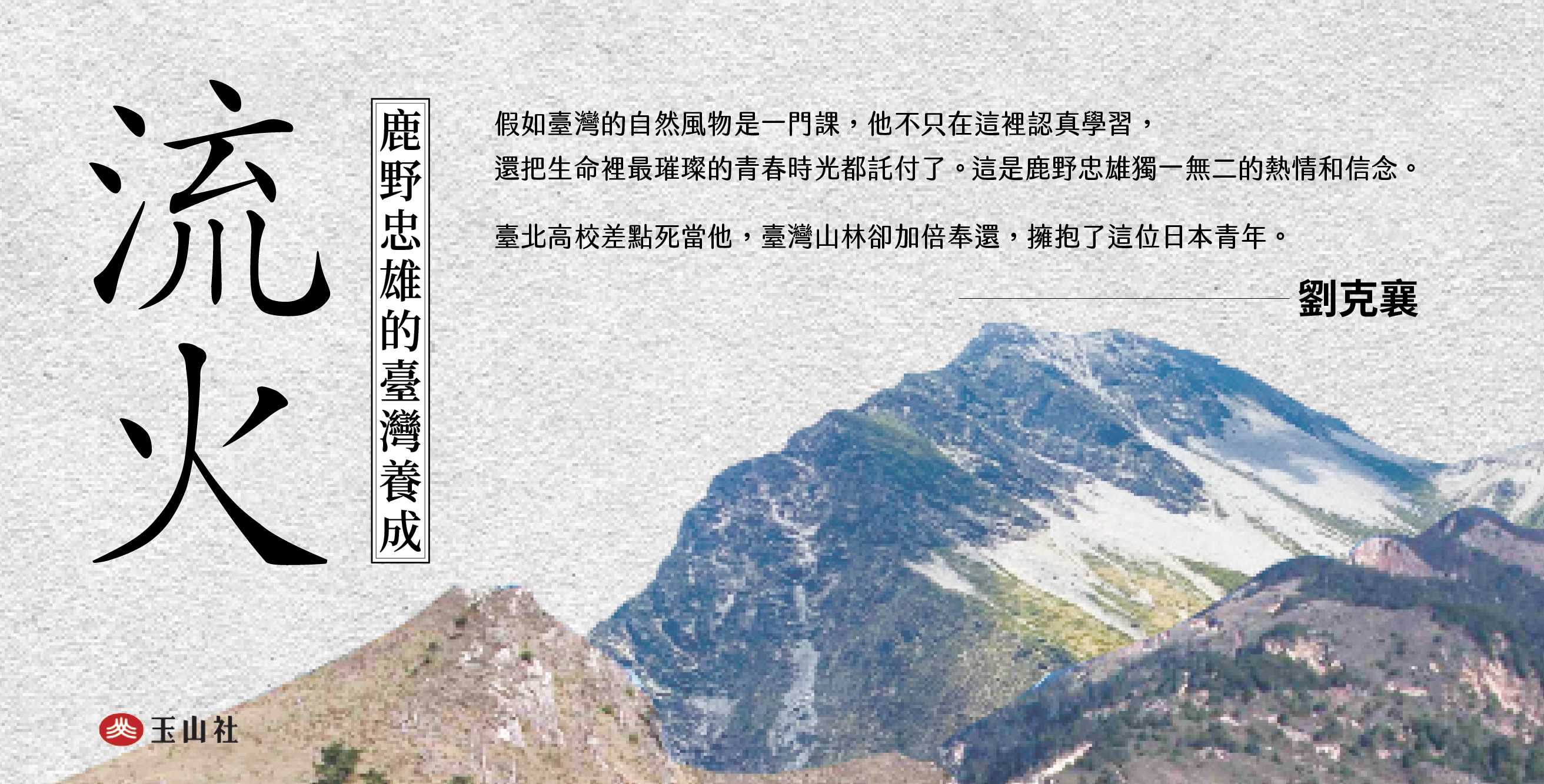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