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乃文學經典,即使長篇萬言、寫入559個角色,但文字簡單、流暢但充滿哲理對話。2013年,木馬文化曾經出過俄語翻譯極富盛名的草嬰譯本,然草嬰版雖簡潔,「信雅達」中的「信」卻失意甚多,與原文意旨有所缺漏,故更替為有深厚哲學底蘊的婁自良版重新出版。
2019年國際政局動盪,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香港運動、日本邁入令和、環保革命大興……2020,我們又會迎來什麼?托爾斯泰在1869年完成出版《戰爭與和平》,距今150年,這位具有博愛精神的俄國文學大師,留下的「革命」、「反權威」、「反暴力」精神,為何直到150年後的現在,還要反覆地嘗試、實踐──人類終究有迎來更好的未來嗎?
電影《天才柏金斯》中,小說家湯瑪斯.沃爾夫(Thomas Wolfe)被柏金斯(Maxwell Perkins)改稿火大,反嗆編輯,還好你最愛的托爾斯泰沒有遇見你,否則《戰爭與和平》就要變成《戰爭與沒有》了!我不清楚這段話是否出自導演虛構,不過,這一幕確是我讀《戰爭與和平》時,放在心底反覆琢磨的:我們要如何肯認,這樣的「篇幅浩繁」有其必要,而作者又想藉此傳達什麼?
關於篇幅,我們首先意識到《戰爭與和平》是一部與「歷史」對話之書。更準確的說,作者指涉且介入的,正是距其不遠的近代戰爭史。托爾斯泰的野心,顯然不只是「將歷史重新記下」,更牽涉「何謂歷史」的反身性探討。因此,在尾聲第二章中,他批判那些「天真的學者」,總是將歷史視為「群眾意志→歷史人物」這樣的簡單格式,而忽略戰爭時期各種民間力量的動盪角逐。在小說中我們讀得明白,作者筆下的戰爭史,不只有帝王將相,不只是政治決斷,更展繪了浮生百姓的臉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於戰爭的態度是曖昧的:我們讀不到反戰的吶喊,「和平」亦往往顯得可疑。
在故事前段,讀者明顯感受到「戰爭」與「和平」被切分又並置,作者尤其寫活沙龍裡對戰事將臨毫無認識的貴族。到了第三部,隨著戰線延展,「戰爭」逐漸滲透日常生活。戰火卻不以屠殺展演,作者呈現的是空蕩的廢城;托爾斯泰寫道:「隨著敵軍日益逼近莫斯科,莫斯科人對自身處境的態度不是更嚴肅,反而是更隨興了。」而後,他又讓皮埃爾奔赴戰場:「我想親眼見證戰爭。」這看似是故事的重要轉折,但皮埃爾不僅沒用「上帝之手」刺殺拿破崙,甚至連個影子都沒摸著。托爾斯泰讓皮埃爾在獄中向囚犯學習,大篇幅的躊躇才是主角的任務。
 《戰爭與和平》中對戰爭的態度是曖昧的:我們讀不到反戰的吶喊,「和平」亦往往顯得可疑。(圖/《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的拿破崙》by弗朗索瓦·熱拉爾)
《戰爭與和平》中對戰爭的態度是曖昧的:我們讀不到反戰的吶喊,「和平」亦往往顯得可疑。(圖/《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的拿破崙》by弗朗索瓦·熱拉爾)
與此相關的是,作者藉漫長篇幅探索了「自由意志」的幽深與不可能。有一句老話叫「情場如戰場」,在《戰爭與和平》裡,少年少女金風玉露般的戀情,總是引人注目。然而,一見鍾情的情人易成怨偶,年輕的愛往往敵不過現實考驗。例如尼古拉和索妮婭這對,破產的尼古拉最終為了家業,選擇和瑪麗亞公爵小姐成婚;美其名愛上公爵小姐的善良,卻害得重信諾的索妮婭孤老終身。又或者,皮埃爾和娜塔莎這對。在第一部初見面時,皮埃爾被人們視為古怪的「他者」(小丑、私生子、「國外回來的」);隔了百萬字,兩人竟還是被作弄似的走在一塊。托氏著意書寫娜塔莎「後來」的邋遢懶散,失去早年的女神風采;他剝奪了娜塔莎的妙齡與靈動,賦予其無聊的「節儉」美德,以與「成長」後的皮埃爾匹配。這是多麼反愛情的故事啊。猶如小說中,男子稍有不順就去當兵,他們有個「遠方」可以耕耘;女人卻得留守,等待著良人歸來(或者乾脆變心)。在我看來,托爾斯泰對「浪漫愛」的態度猶如看待「自由」,甚至帶點沙文主義與冥頑不靈。他是不討喜的老家長吧:人生最重要的,永遠不會是粉紅色泡泡與戀情。小說那麼長,那麼多人物,卻只是一再演繹更多的言不由衷,更多的身不由己。
小說將近結束前,皮埃爾和娜塔莎有段簡單對話。娜塔莎聊起孩子,她說:「真的沒事,都是小事。」《戰爭與和平》很長,但似乎還不夠長。托爾斯泰似乎意猶未止,然而再長的小說終會結束。或許那些來不及寫的,「真的沒事,都是小事」的,才是人生?
陳柏言
1991年生,高雄鳳山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在讀。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大獎,入選臺北文學獎年金補助計劃、臺北國際書展小說組大獎等。出版短篇小說集《夕瀑雨》、《球形祖母》。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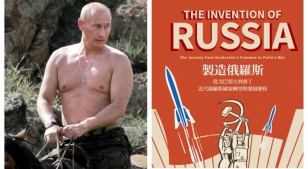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