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作家片惠英(편혜영,1972-)(圖片來源 / namu.wiki)
文/崔末順(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片惠英於2000年因短篇小說〈抖落露珠〉榮獲《首爾新聞》新春文藝獎而登上文壇,從第一本小說集《青色庭園》(2005)問世到近作《洞》(2016)為止,她一共出版了8本小說集,在韓國文壇可說已經占有不易動搖的一席之地。在《青色庭園》中,片惠英展現出韓國文壇罕見的蠱怪(grotesque)風格,描繪了遍布屍體和傳染病橫行的失樂園,構築出一片充滿恐怖和殘酷的小說天地,帶給讀者既陌生又充滿衝擊感受的美學世界。
觀察片惠英近20年創作,可以發現無論她用什麼題材講述任何故事,小說處理的總是與大大小小的「龜裂」問題有關。片惠英自己也在受訪時多次提到,「龜裂」是指人物突然間產生波動的「界線」,也是讓人看到一向看不見的「隙縫」,更是人生中可能瞬間即會碰到的一個「空洞」。她在小說中刻畫的「龜裂」,無論是看得見抑或看不見,總讓人有種在安穩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崩塌,隨時都可能寸步難行的不安或不舒服感。總之,「龜裂」是了解片惠英小說的一個關鍵詞,因此她的小說總能帶給讀者一種不安或不快的美學感受。
就此,我們或可分成三個階段來觀察片惠英小說所呈現的「龜裂」樣貌。
第一階段:《青色庭園》時期(2005-2006)
 青色庭園
青色庭園
該本小說集一出版,即因描寫各種失蹤事件及恐怖怪異氛圍,引起韓國文壇注目,因此而獲「問題作家」稱號。收錄於《青色庭園》中的小說,每篇都會出現屍體、被支解的人體、疾病或者惡臭等讓讀者感到噁心的場景,這種幾近偏執的描寫,導致這些小說免不了得到怪異、獵奇、殘酷、蠱怪、鮮血狼藉等的評價。對於小說中濫發的恐怖、詭怪意象,評論者常會拿它與「硬血腥(Hard Gore)」的電影手法相提並論。所謂「硬血腥」是指影像充滿著鮮血、內臟或斷肢等讓人不忍卒睹的場面,而這類恐怖意象充斥畫面的電影,除了刺激觀眾的末梢神經,其最大特徵就是敘事成分非常貧乏。這一時期片惠英的小說也同樣呈現出此種樣態,《青色庭園》中各篇小說具有的共同特徵,就是恐怖殘酷的意象描寫蓋過敘事。如此強烈意象和驚悚場面,也成為阻礙讀者理解敘事的主要原因,同時因敘事太過貧弱,讀者即便面對殘酷場面或恐怖意象,也不會特別感到緊張或不安。如〈人孔蓋〉中人物被科學家獵捕後遭到解剖、〈萬國博覽會〉中鬥犬胡亂闖入博覽會場威脅著觀眾、〈青色庭園〉中人物產下青蛙等等情節,登場人物在奇異恐怖的世界裡固然痛苦不堪,但對讀者而言,他們並不認為這些場景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自然也不會為此感到不安,頂多只是心裡覺得不舒服或不愉快而已。
由於強烈意象占了大部分篇幅,小說中描寫和敘事之間的連貫性變得非常薄弱,導致兩者之間產生「龜裂」,作者犧牲了敘事而得到殘酷意象,這些描寫雖然非常逼真,但卻很吊詭的,讀者感受到的並不是現實性。小說中的世界為游離於現實的非邏輯性空間,它只是能夠刺激末梢神經、造成不舒服的假想世界。因此可以這樣說,片惠英小說形塑的幻想世界和誇張的痛苦,引出了小說和現實之間的「龜裂」,而這樣的描寫和敘事之間、現實和小說之間產生的「龜裂」,可說是片惠英早期小說的主要樣貌。
第二階段:小說集《往飼育場方向》《晚上的求愛》和長篇小說《灰燼與猩紅》時期(2007-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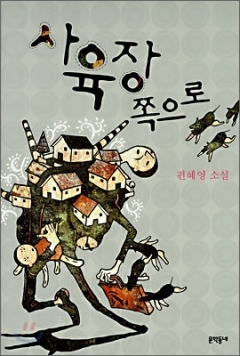 往飼育場方向
往飼育場方向
 晚上的求愛
晚上的求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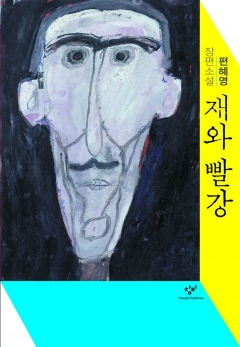 灰燼與猩紅
灰燼與猩紅
與前述小說背景不同,這時期片惠英拿日常的現實空間做為小說舞臺,開始描寫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龜裂」,以及由此引發的崩解現象。平凡的日常生活突然因特定事件發生而被打亂,生活步調一切變得凌亂不堪。此時所有熟悉的日常事物瞬時變成惡夢,變得非常陌生,人物也瞬間被獨自留下。問題在於日常和惡夢間的界線,只是極其平凡的日常小事,而非特別事件,它帶給讀者一種災難隨時都可能到來的莫名恐懼。相對於前期小說,此時「恐怖片」帶來的不只是不快感,它已昇華為不安和恐懼感。
一如韓國評論者所謂的「日常的惡夢化」一般,該時期片惠英小說著重在描繪發生在隔著日常和惡夢那道牆上的「龜裂」面貌。惡夢往往由遺失、失蹤或事故等外來事件開始,不過日常的惡夢化過程中,這些事故並非發生的核心原因,它只是扮演一種扣扳機的角色而已。破壞人物和日常的最終原因,是日常生活本身具有的「同一律」屬性,以及發現此屬性的主體本身。小說人物在日復一日每天重複的生活當中,發現逐漸失去自我存在感,在此同時,都市文明中的熟悉日常,瞬間也變成既陌生又令人恐懼的迷宮。從中我們認知到日常其實非常脆弱,即使只是不起眼的小事也能輕易將它擊碎,從而慢慢變成失去主體個別性的同一律迷宮。而在此同一律迷宮中感到倦怠時,主體才能成為獨立的個體,成為被我們所熟悉的現實生活離棄的異鄉人,此時可能就會拋出「該如何在惡夢般的現實中生存下去?」的問題。這些存在性的問題,可以說就是片惠英此一時期小說所要指涉的日常和惡夢之間的「龜裂」。
第三階段:長篇小說《去了西邊森林》《夜晚正要過去》《線的法則》《洞》時期(2012-2016)
 去了西邊森林
去了西邊森林
 夜晚正要過去
夜晚正要過去
 線的法則
線的法則

片惠英於201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洞》,主要是講一位名叫奧吉的大學教授因為嚴重車禍變成植物人般躺在病床上回憶著過往的故事。該篇小說不僅獲得美國雪莉傑克森驚悚小說獎(Shirley Jackson Awards)的肯定,在韓國出版後,也被評價為擅長細膩刻劃內心世界和人物矛盾的佳作。小說以一場突發車禍和太太死亡帶給奧吉的生活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做為敘述主軸,故事的每個場面都層層建構起緊密的內面關係,以及人物之間的矛盾,營造出相當緊繃的敘事張力。車禍發生後,一連串如同惡夢般的事情接連出現在奧吉身上,一種無法挽回過去的無力感也襲上心頭。致命性的突發災難,瞬間把平凡日常弄得一塌糊塗,遭受身心重創的奧吉,不僅要接受太太死亡的噩耗,還要面對身體殘缺的無奈。除了眨眨眼以外,他無法做出任何動作,醫生甚至還說如果缺乏求生「意志」,可能就無法存活下來,他開始認知到自己將「完全崩解消失,什麼都不是」的事實。奧吉遭到身軀癱瘓、生活崩解,當然是由那場嚴重車禍引起,但是作家卻把焦點放在事故發生前他的生活上面,並以相互交錯方式披露他們夫妻間相處的實際面貌,尋找事故發生前即已存在的「龜裂」和「空洞」。
他和學妹J之間的外遇、為了尋找教職想盡辦法抓住對手辮子並設法陷害對方的行徑,透過奧吉的回想和敘述者的陳述一一浮現。自己曾經那麼厭惡的父親,總是隨意嘲弄他人的意志和想法,還導致母親自殺,甚至是造成自己性格卑怯的元兇。然而曾幾何時自己的模樣卻愈來愈像父親,教訓太太要她「找個能讓妳長大的事情做吧!」的嘴臉,就完全是父親的翻版。尤其在讀到「四十歲時套用到所有罪名都無妨」的詩句而頗為認同時,不去反省已經變得鄙薄庸俗的自己,反而認定「不僅是我,別人也一樣吧」,輕易掉入自我合理解釋的陷阱中,不難想像,他的人生已經出現了如同建築在沙灘上閣樓般的危殆與不牢固。如此一點一滴累積的龜裂,終究造成奧吉的人生出現了大空洞,也就一發不可收拾地瞬間將他吞噬掉。
透過交錯描寫車禍前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以及他與太太間的互動情形,作家想告訴我們,奧吉的不幸並非單純的「事故」所引起,而是由他自己的意志所造成。在這一點上,《洞》帶給讀者的恐懼感更為深刻。奧吉和太太互相無法了解對方,他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太太的不順遂和內心感受,以及只能執著在庭園種樹的種種苦悶;太太的情況也差不多,她懷疑奧吉有了外遇,還記錄著想要告發先生過錯的種種猜疑。從回憶夫妻不了解對方而產生的失望和痛苦,以及不斷上演猜疑對方的戲碼當中,奧吉終於了解到他們之間存在的「縫隙」,以及「自己人生中的巨大空洞」,最後掉進丈母娘替女兒挖出的黑色坑洞裡死去。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所有災難和不幸,往往是我們自己不去了解對方所引起,所有悲劇的根源也是從我和你之間的小龜裂開始,這就好比說小空洞(the hole)徹底崩壞了奧吉的日常。
如上所述,片惠英的文學一直在處理同樣的問題──各種形態的「龜裂」,只是其程度和樣貌的不同而已:在《青色庭園》階段,她用破壞性十足的驚悚意象來呈現敘事和描寫、小說世界和外部現實之間的乖離和龜裂;到了下一階段,她安排無預警的偶發事件,揭露平凡日常隨時可能變為威脅個人主體性的同一律地獄,日常和惡夢的區分因此發生龜裂;進入包括《洞》在內的第三個階段時,片惠英開始集中敘事必然性及人物內心,尋找招致惡夢的龜裂起點,並說我和你之間的不了解、主體和他者之間的龜裂,才是崩解日常、陷入悲劇的真正原因,而且她還進一步揭示,無論如何努力,我們終究還是無法完全了解他人的「存在性」悲哀。那麼,面對這種殘酷無奈的事實,片惠英又將如何展開她的下一個文學旅程呢?她又將如何講述抱著「龜裂」和「空洞」卻不得不活下去的我們這些平凡人呢?但願她能以充滿關懷和憐憫的眼神眷顧我們這些平凡人悲苦的人生。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