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此書之前,請容我先提問。你有想過,《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中的配角應思聰,若是居住在其他國家,他的幻聽會生做啥款嗎?史丹佛大學的醫療人類學家譚亞・魯爾曼(Tanya Luhrmann),曾以民族誌的方式,詮釋文化如何影響思覺失調症的表現形態。她發現,平平是「幻聽」,一些印度的患者認為「幻聽」提供了幫助和建議,有些人甚至形容這聲音活潑、有趣。相反地,美國患者的幻聽較為「暴力」,命令成分也較高。這歧異多少反映了兩個社會的本質,印度,某程度上,較為強調社會成員間的情感連帶,美國則容易讓人聯想到「個人表現」跟「績效」這幾組關鍵字。
回到《成為一個新人》這本書,這可能是晚近我所讀過,台灣本土書籍,以「精神疾病」為節點,輻射出最深刻的報導。《報導者》記者張子午從2016年起,深入追蹤精神疾病相關議題。
張子午引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於2016年4月3日婚禮上發表的演講,「如果今天我是新人⋯⋯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痛苦有更多想像力的人⋯⋯」。
我認為,這段話即為此書基調:一場想像力的擴建工程。
想像力的摯敵為刻板印象,張子午試圖消融兩者之間的壁壘分明。他就數個議題進行採訪、整理、並提交個人的反思,書中處處是兩難與掙扎的痕跡,聲音與聲音之間偶爾和諧,更多的時候相互角力。讀者不難感受到,在這個議題上,不論是精神疾患或其照顧者,單單是為了維持自己的處境不要塌陷,每個人都得卯足全力。相殘或許無心,但往往註定。
容我摘錄書中片段來讓各位讀者感受聲音交鋒的現場。
當初《與惡》劇集熱映,仍可見許多觀眾習慣性地使用「精神分裂」為稱呼。從「精神分裂」到「思覺失調」,試圖跨越的究竟是什麼?張子午提出:「在疾病本質不變的情況下,背後反映的與其說是醫學進步的成果,毋寧說是長久以來累積的污名,專業界不得不以更客觀、不帶情緒、強調正面積極的意涵來洗刷,使其與其他生理疾病平起平坐。」
但書中很快地也援引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胡勝翔的分享,逼人直面正名的侷限:「當中很多結構問題沒有探討,對我來說疾病不可恥,感冒也是疾病,我還是會選擇說精神疾病,而不用精神障礙⋯⋯與疾病共存是我們的特色,是生活的一部分,說康復很奇怪,他不是感冒(吃藥就好),而是跟著一輩子,怎麼康復?」
沿著胡勝翔的問題繞下去,作者張子午提及藥物技術不斷突破,精神醫療的領域如今看似由「藥物控制」站穩領導地位(暫不論其隱憂),但藥物就能完全克服精神疾病嗎?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生湯家碩(曾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做為碩論主題)並不認為:
「精神藥物的功能,只是在建立『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礎,但終究無法回答: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這其實有點像哲學問題⋯⋯但一個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瞭解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否則繼續在那個混沌的世界慢慢消逝無蹤就好,幹嘛康復?」
類似的糾纏,於全書反覆地出現,想像力才剛堆疊起又遭逢解構。好不容易明白了什麼又因為更新的說詞而翻案。最終讀者或可感應到隱約漂浮在這些報導與訪談底下的,實則是至為尖銳的問題:什麼情況下,群眾會認定一個個體失去了身為「人」的資格?
卡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命值不值得活,就等於回答了哲學最基礎的問題。」
因此,張子午自然也沒放過自殺這個議題。透過他的穿針引線,台灣本土的自殺版廓隱隱浮現,不僅有企圖尋死之人的聲音,也有伴同者,甚至自殺者遺族的迴響。
不諱言,閱讀前,我對於關懷員的理解多停留在朋友們於社群上的埋怨「只會打來問一些不知所云的問題」,但,透過張子午的報導,我首度明白到,這份「不知所云」可能是真的,但我們不可忽略這「不知所云」背後的乏力與哀傷。國家把一群工作者推上第一線,試圖防堵個體的自死與墜落,然而,後勤的資源與訓練、充裕的時間、合理的案件量與薪酬等等,全部付之闕如。
書中引用了魏明毅(著有《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的觀點,魏以基隆工人的情形出發,試圖詮釋自殺與社會的連動:「那不是源自個人認知的問題,是由文化所給定的價值界定問題,若能跳出文化的框架,跳出整個台灣告訴你什麼叫人生勝利組,誰是魯蛇,我們才有機會成為一個『叛道』的人,他的力氣就會出來,用自己的方式界定人生是不是活得下來。」
我也很訝異書中出現一個人的聲音:夏雪,詩人葉青的妹妹。今年六月,出版社黑眼睛文化發文公告,「《下輩子更加決定》及《雨水直接打進眼睛》印量已達萬冊,尊重家人意願,流通本數銷完即斷版」,那一陣子,所有平台這兩本書動得飛快,讀者奔走相告,唯恐向隅,讓人不得不轉身推敲葉青如何挪移了我們的部分審美。夏雪緩緩抽絲剝繭,講了姊姊,也講自己,但,講最多的還是姊姊跟自己。
吳念真在《成為一個新人》序裡談到,弟弟在遺書承認,當他的弟弟也很辛苦。夏雪則是相反過來,葉青始終是家族裡閃閃發亮的人,夏雪照顧葉青,也承擔著眾人獨獨寶愛葉青的剝奪感。發光會痛,站得離發光的人太近也痛,我不得不屏息,感受到所有與精神相關的,疾病也好,障礙也好,都得回歸到一個最原始也最艱難的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人跟人之間出了毛病。
在小燈泡事件後,反省精神鑑定的意義
此書的第二部重頭戲是從刑法第十九條切入,深刻剖析「精神障礙該由誰來說,又是誰說了算」。這部分相當考驗讀者的耐心,可能得頻繁地停下來,整頓數個陌生名詞之間的關係。
當初小燈泡母親Claire「非典型受害者家屬」的冷靜表現,直陳要看見「全貌」,讓許多人感到不適。張子午則以相當從容的篇幅,讓大家看見Claire生命的篇章,你才能明白為什麼她心底掛念王景玉的生命篇章。
著名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在《可侵犯的尊嚴》書中提及,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為「人之尊嚴不可侵犯」,他認為「這一句話之所以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因為人之尊嚴常受侵犯」,更具體的說法是「人權其實一如友誼,在黑暗、艱難的日子裡,尤其要經得起考驗,否則就毫無用處。」
回到這個章節,為什麼在這些人犯下「泯滅人性」的重大刑案後我們仍得為其奔波周旋,在法庭上進行縝密的攻防與對話?因為,越是令人髮指的案件,我們就得更嚴苛地去審視我們的人權是否經得起考驗。真正的免死金牌絕非精神鑑定,而是我們對人權的保護。
而在最後一章,張子午筆力未弛,緊扣回命題:如何評價,哪一種「人」不適宜與我們共存?主要定錨於龍發堂與花蓮玉里社區家園。多方意見交織,讀者可以清晰地辨識出不同位置所衍生出的不同立場,龍發堂與玉里社區家園兩者之間也產生了值得深思的對照。
《成為一個新人》中,每一篇文章都彷彿對讀者調頻,不一定會完全接受,不過,若耳聞微弱且斷續的聲響,或有挪移偏見的奇效。你也會發現整本書一以貫之的精神:「身而為人的尊嚴」。張子午筆下每一承受磨難的靈魂,你都能順著他們有限的分享中,找到他們生命中的光彩轉趨黯淡的一刻。相反地,讓他們恢復、尋回部分自理能力的關鍵,往往也與受到誰的重視肯定有關。
此書必然有幾個時刻是你想大喊,天啊人跟人太複雜了我為什麼不轉頭打開Netflix呢,不諱言,「逃避困難」也是很珍貴的人性,但我仍珍惜自己再次打開書頁的心情。這背後自然有我對於林奕含的私人懷念。
她說過:「那些可以輕易說出『該去看精神科了』的人,真真無知到殘暴,無心到無情。我幾乎無法羨慕他們的健康了。」
此書的命名甚好,成為一個新人,也莫忘一位故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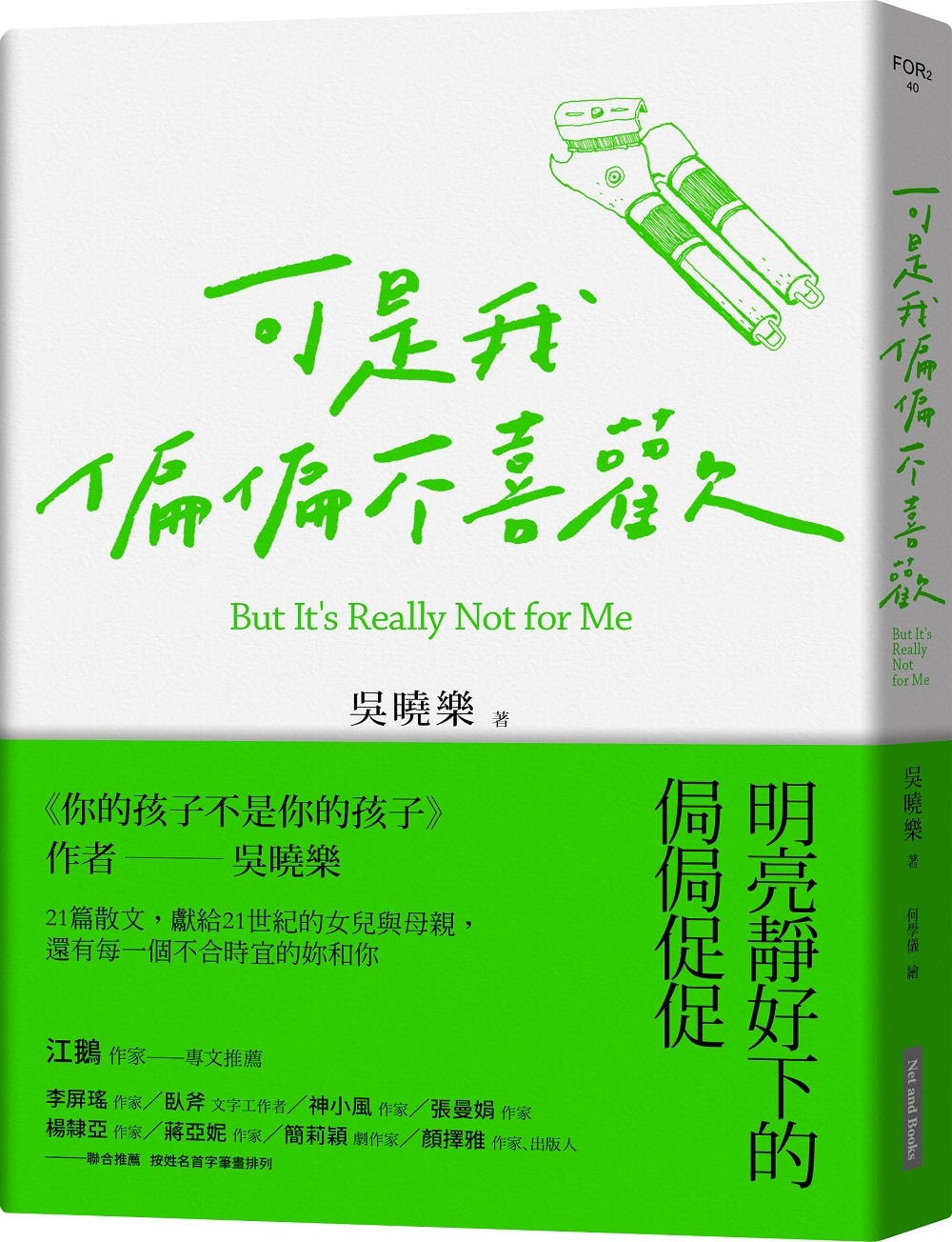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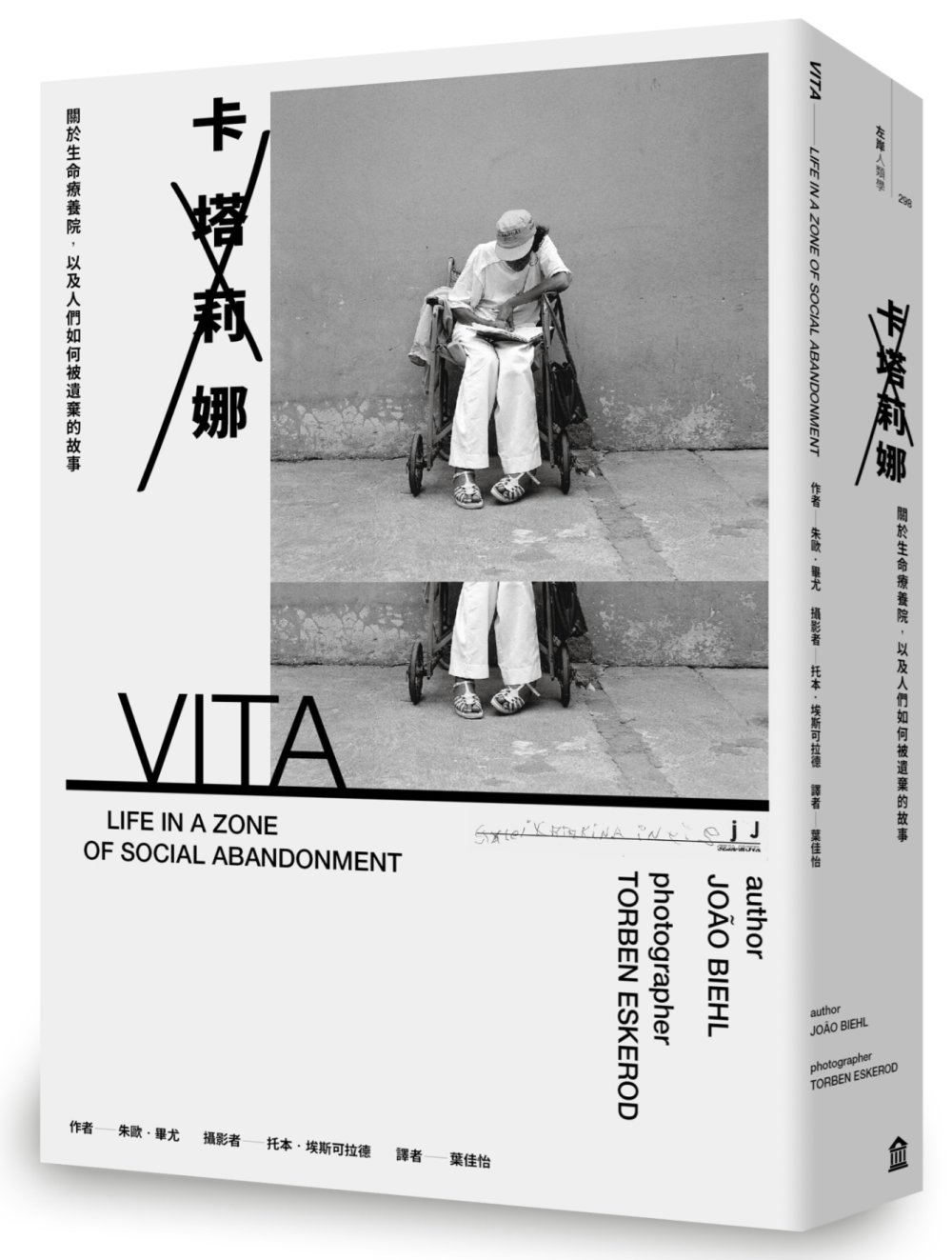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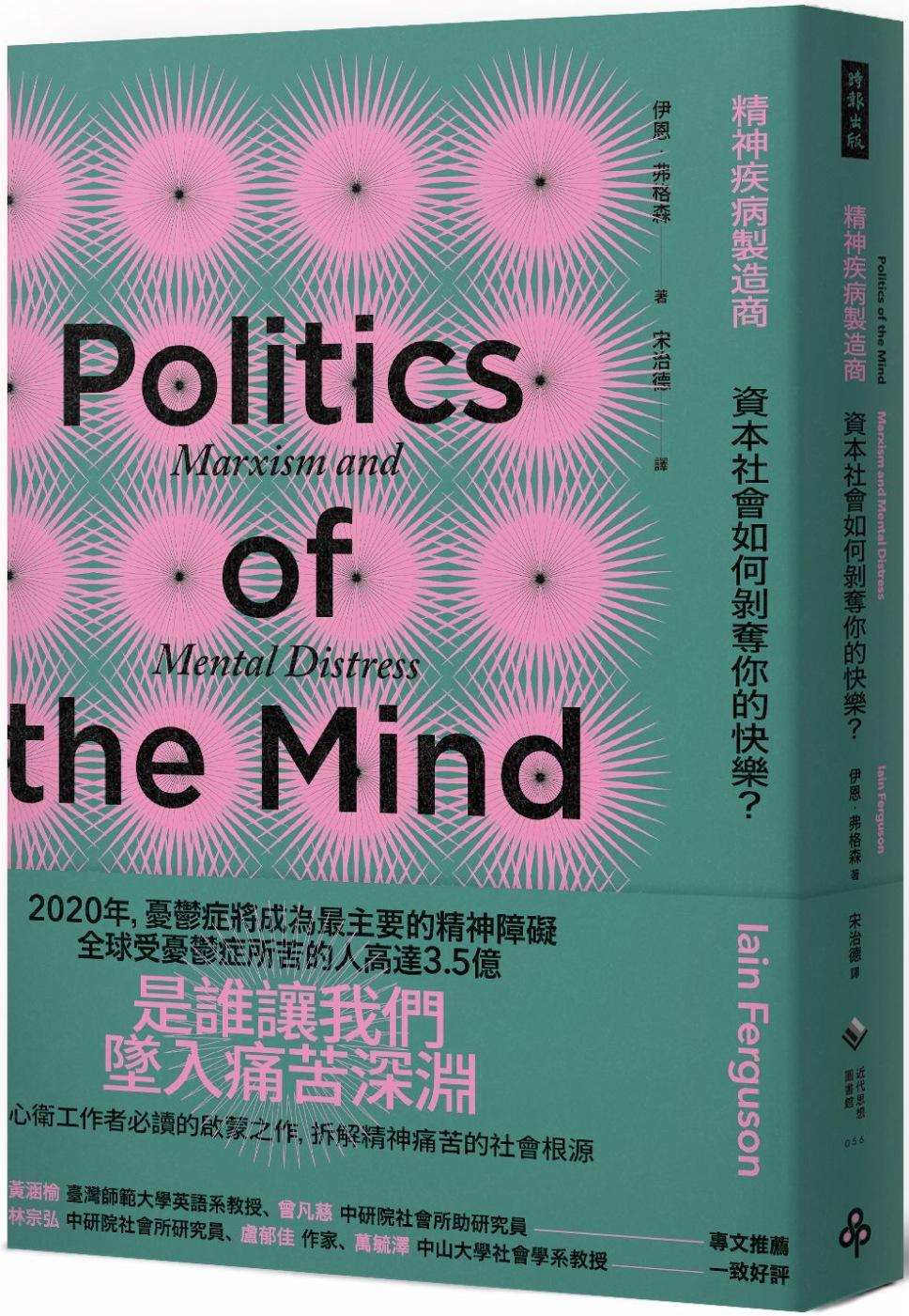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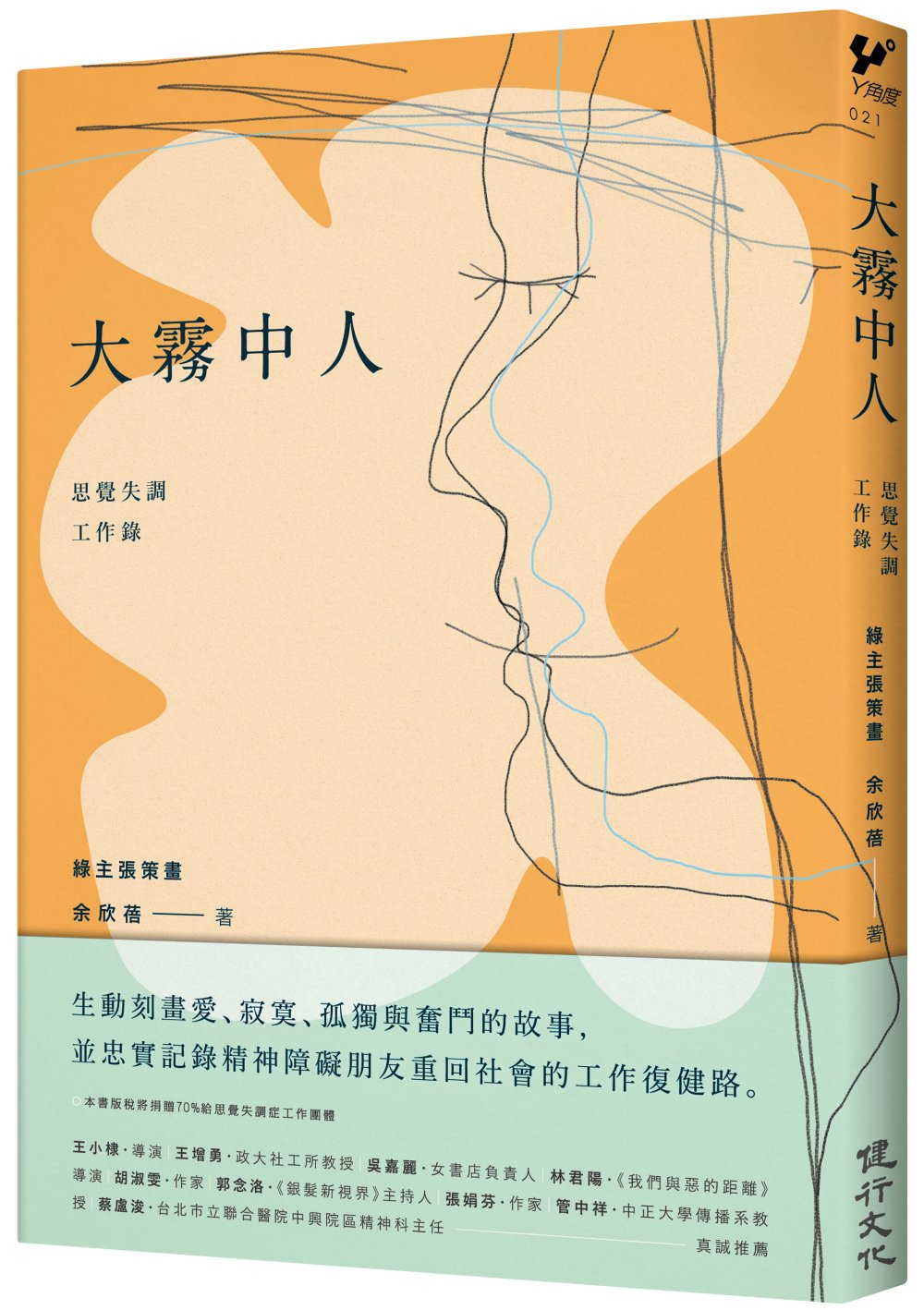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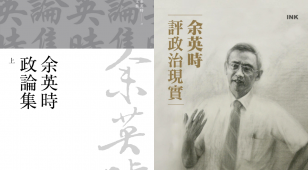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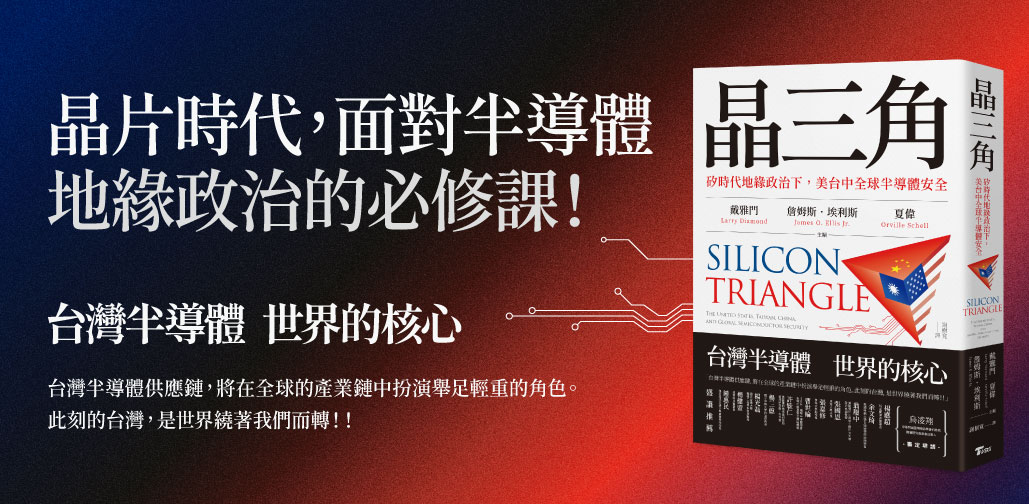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