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發明了一種個人緊急求生裝備。這本小說,在戰亂的日常中,建造了奇特、足以安身的寧靜。儘管主角受盡折磨,但靠著這種攜帶式碉堡,總不至傷痛太深而無以復原。這種裝備叫做「陪伴」。回憶的陪伴,他人的陪伴,既痛,且暖。
《門》的第一個主題,是戰亂、流亡對生活的侵犯。書中透過一對難民情侶的眼睛,訴說主體經驗。內容令人意外。在臺灣,許多人告訴我,投降等於安全。但本書中難民並不是少數被通緝的反抗者,而是安分守己的順民。政治冷漠的大眾厭惡反抗軍,不曾對政府有異議,仍然人人隨時死於突發暴力。若非死亡迫在眉睫,誰會拋下家人、地位財產、生存保障,兩手空空被扔到天涯海角。
《門》原本悠緩靜美的老派情調,在這戰慄氣氛下,加深了父母的溫情憂慮、戀人的纏綿牽掛。宵禁讓戀人無法見面,只能網路通訊,「他人不在她身邊,卻變得無所不在,她對他亦然」,兩人飢渴隔空撫觸,「他們已任對方進入自己,卻還沒接吻」。
謝依德幽會手機沒電,上車回家接上備用電池,手機嗶嗶響不停,一堆爸媽驚恐的未接來電和未讀。因為那一晚,很多家的孩子沒回家。
此時誰可相依就是知己,戰亂升溫戀情,催化浪漫。物資吃緊時,謝依德送娜迪雅露營煤油爐、消毒食水的氯錠,感心已遠超過玫瑰花束。相約流亡,更把性命寄託在了對方身上,就像在一個男女禁止牽手的國家,兩人同行偶爾觸及對方指節之珍貴,象徵了每個下午都可能是兩人最後一個下午。然而,脫離焦灼恐懼,擠迫、貧困、詐欺橫行的難民營,會掀開兩人怎樣的另一面?
●
《門》的第二個主題是愛情。戰亂像繃緊了的絲弦,男女主角的性情經由那股張力迸出琴韻。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說「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其實沒有愛,轟炸過後只有兩個杯弓蛇影的中年男女。原本怕的是人性險惡,范柳原玩弄女人,白流蘇也只因需要男人養活而被逼嫁他。兩人不知愛為何物,一心算計自保;只因戰爭而恐懼死亡,對方才顯得可信、可靠起來。小說看人,是輕蔑、憐憫的。那麼《門》看待男女主角是怎樣的人呢?
《門》抱持全人的觀點。它說,人的個性不是藍色或白色那麼簡單,而是發光的螢幕,反映的色調取決於環境。
謝依徳戀家,房間裡留著從小到大的一切,抽屜內還黏著小時候貼的貼紙,喜歡本地的流行樂團。保守、虔誠,重視責任感,拒絕婚前性行為,因為違反教規。喜愛禱告,因為令他想起與父母相伴的溫馨童年,所以成年後他用禱告來愛別人。喜歡用望遠鏡觀察城市、星象,我想那是因為不必真正接觸,只要從舒適小窩朝外遙遙眺望就好。他喜歡上了同班一個穿黑袍的女孩子,黑袍代表她可能同樣虔誠保守,但他猜錯了。
他的課題是,怎樣抓住別人從樓窗扔給他掩人耳目的黑袍,趕快套上,以策安全。
娜迪雅違反「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監管傳統,離家出走獨居,騎機車通勤,上學、談戀愛、聽流行歌又嗑藥,全盤世俗化。她叛逆衝動、直覺大膽,作者筆下的女主角總有這種夷然自信的氣派,從無自我懷疑。娜迪雅經常說出自己意外的話,有時脫口而出引爆家庭革命,有時生氣說出口的卻是體諒男友的話。她熱愛探索、尋求冒險,覺得樂手男友還有其他女人,根本不在乎她,但她仍跟他為性而性。她不受道德拘束,務實權衡應變,如魚得水:為了租到房子,她毫不介意向女房東撒謊;如果一屋難民都劫掠缺席屋主的財物,那麼她覺得貿然反對是笨蛋;但是擔任收銀員遇上搶劫,她也不會乖乖奉上收銀機現款。她穿上穆斯林黑袍,是認同這件黑袍能保護自己,在銀行擁擠時阻止陌生人性侵犯。像是加州聾啞女傭年紀大了不再身材性感奪人注目,反而為避開危險的男人慶幸安全了。
娜迪雅的課題是,怎樣脫掉那件黑袍所代表的防衛心態,弄懂自己想要什麼,得到自由去成為自己。適應有時扎疼人的自由,長成自己從未想過的模樣。
 娜迪雅穿上穆斯林黑袍,是認同這件黑袍能保護自己。
娜迪雅穿上穆斯林黑袍,是認同這件黑袍能保護自己。
她的課題是,怎樣脫掉那件黑袍所代表的防衛心態,弄懂自己想要什麼,得到自由去成為自己。(圖/wiki)
他勢單力孤、格格不入,無處可逃。難民營奈及利亞女人抬腿攔路挑釁他,他光要保住尊嚴就不可能。海濱成群男人一看就來意不善,他不戰而逃。難民劫掠屋主,違反他的道德觀。他變得更虔誠保守,歸屬感來自天天和本國同鄉一起禱告,把他離棄的舊世界抱得更緊。
受保護的她,像個孩子隨遇而安,展臂擁抱新世界,像大熱天騎摩托車時她欣然接納漫天沙塵、小蟲飛進嘴裡,吐完就狂笑。她扎營安家不忘上山頂觀光,抓網路音樂聽,從垃圾堆裡也能挖出生活樂趣,讀者很難說她是難民或浪跡天涯的背包客。她融入奈及利亞難民的民族議會討論,即使語言不通都能成為一員。
他驚見她眼中獸性,原來她是個潛在的勇武抗爭者。可能她其實不需要男人,在各種意義上。
而他先前沒發現自己其實不願拋下老父離家。老家樓上的血案,曾經把兩人夜裡湊上一張床尋求對方安慰。而另一樁死亡,也使兩人疏遠。他一次次遷怒怪罪她。
男孩保護女孩雖然淒美浪漫;但換個環境,也許女孩不需要男人保護也能自立。也許,男孩需要女伴保護時,他心理上無法接受,覺得自己太廢,遷怒對方。小說一步步把讀者拋進絕境,究竟怎樣才能解套?
●
《門》的第三個主題是聯繫。村上春樹《黑夜之後》角色瞬間出入於房間和房內電視螢幕:「我們就化為純粹的一個點,穿越了分隔兩個世界的電視畫面。從這一邊移動到那一邊。通過牆壁,飛越深淵時,世界大大地歪斜,崩裂,一度消失。一切化為不相混雜的微細塵埃,往四方飛散。然後世界重新構築,新的實體包圍住我們。」《門》也用幻想手法,把偷渡旅途轉化成「通過黑暗的一道門」。現實中擁擠的難民船、卡車載運人蛇、跋涉沙漠高山,搶劫、謀殺、窒息擠迫而死,被強姦,被轉賣,被索賄,在《門》當中消失。通過任意門就到了另一個國家,目的地還是一塵不染的異國大理石豪宅,過程乾淨俐落像瞬間移動,帶著對新款科技產品高度便利特有的暈眩。
作者的第二部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寫移民無縫接軌穿梭於第三世界汽機車煙塵蔽天的老家,和華爾街精英的金融權力遊戲之間,原是作者的真實人生。作者莫欣.哈密(Mohsin Hamid)1971年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父親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讀博士,所以他也在美國上小學。回拉合爾讀完中學,再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公共與國際事務,是小說家歐慈(Joyce Carol Oates)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文學創作學生。從哈佛大學法學院讀完法律博士,到紐約曼哈頓的財務管理公司擔任管理顧問,後來派駐倫敦。如果他是臺灣人,就會被封為臺灣之光,和林書豪、吳季剛神話一起上雜誌,然而小說家的使命並非成功。莫欣.哈密的小說以巴基斯坦經驗向英語文學叩門,每部都帶著民族認同,要求英語世界前來感受第三世界的處境。
 作者莫欣.哈密(Mohsin Hamid)(圖片來源/作者官網)
作者莫欣.哈密(Mohsin Hamid)(圖片來源/作者官網)
《門》有一重較急迫的使命,期待讀者在主角旅程中經歷自己成為難民的艱苦疑懼,從而脫離孤立、對立,同理原本的假想敵。男女主角流亡主線之外,穿插一系列各自獨立的極短篇,像科幻小說《末日Z戰》,鳥瞰全球八個難民與居民相遇的現場,猶如警衛室多台螢幕轉播不同衛星畫面。
一篇透過不同的監視器鏡頭接力,剪接杜拜難民一家四口的軌跡。室內保全監視器、街道監視系統、無人機空拍、遊客手機自拍,藉監視器無機質的畫風,傳達外人待難民的冷漠,視為非人,他者化,妖魔化。這八篇始於懸疑險惡,逐篇回暖,由難民和居民原本陌生、敵對,到居民走進難民所來處,在另一世界成為浪人,成為戀人。八篇由寒冷而炙熱,順序就像漫畫《將太的壽司》全餐出菜由鹹到甜、由淡而濃、由冷而熱。支線和主線的情感起伏曲線拉開距離,也緩和了主線失落的衝擊。
這起伏曲線是作者的期待,盼望仇外份子和移民、難民,任何對立者,由猜忌、排擠,走向同情。
有一重較悠遠的使命,就是探問人心互相理解的界限在哪裡。書中有許多錯位的精采設計,像是華卓斯基姊妹導演的美劇《超感8人組》,兩人心電感應交談時,雖然天各一方,畫面卻以促膝相聚的心象呈現。《門》寫熱戀時,兩人透過手機、網路,遙遙相繫;疏遠時,雖形影不離,卻貌合神離:「兩人在不同的時間,各自在山頂待了一會。」
這事透過兩人欣賞網路照片而重述。有位法國攝影師拍紐約、里約、上海、巴黎夜景,但滿城燈火都修圖修掉了,原本受光害而黯淡的夜空反而換成燦爛星空。原來攝影師苦心去找同緯度的無人煙之地,地球自轉幾小時後、城市會走到那星空下。一樣的天空,不同的時間。
說了兩遍,想說什麼呢?一樣的戀人,不同的時間。兩人在加州抽大麻,想起出走前在老家吃迷幻蘑菇,情景不再。悵惘難言。
這種對照,不僅止於抽離當下,互相封閉隔絕,陷入獨處;也帶來驚奇和穿越。一次娜迪雅坐在戶外台階上滑手機看新聞,赫然發現網路上有張自己此時此地的照片,就像從監視器上看到自己的即時影像。雖然故事另有謎底,「偶開天眼歔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自身變成他者被看,他者也就因此成為了我。
雖然抱持這種善良的願望,祈願消弭衝突。但是,人能互相理解嗎?
就像小說用「門」取代了偷渡苦旅,戀愛也隱去了相愛相殺、血肉模糊,乾乾淨淨、漂漂亮亮地跟讀者見面,無憾無怨。書裡不會有人問「你為什麼不能陪我」,不會有人回答「你為什麼不能體諒我」。似乎作者像小孩想向外人迴護遮掩爸媽吵架,努力證明爸媽還是好人。小說男女主角當然是好人。只是和平雖然足以支撐他們逃離壓力,但還不夠遠到邁入自己的內心。使讀者只好寄望於,找到對的人就行了。如果謝依德無法瞭解女人,那麼聊觀星就好,喜歡他的女人,自然會覺得聊星星很有魅力。而需要被瞭解的娜迪雅,自然會去找女人來瞭解她。人生變化並非他們所期待的,但有時那樣也已經夠完美。
●
作者是什麼樣的人呢?《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寫女主角從自家街屋向外眺望一座基地台:「在一堆衛星天線之上還頂著紅的、白的好幾根大柱直衝雲霄,就像是建來要為天空中的浮雲導航的電磁桅杆。」
《門》寫成群直升機「螺旋槳轉動的轟隆聲,迴盪在窗戶與小巷間,像是壓縮著機身下的空氣,彷彿每架直升機下方都有一根隱形支柱,一個會呼吸的隱形圓筒,撐著這些個奇形怪狀、來去如鷹,又會動的雕塑」。
無論有什麼在空中漂浮,在書中,都需要支柱撐起,或是大柱為之導航。作者看到自由漂浮之物,便會想到安全支柱;看到支柱,便會想到漂浮之物。他總會替它們安上想像中的配對。就像《門》中,謝依德想要回頭往窩裡蹭,想要安全;娜迪雅想要往外探索,想要自由。根據馬斯洛的人類需求金字塔理論,人得先滿足了基本生存、安全感的需求,才有餘裕需求親密、歸屬感,然後渴望得到自由去自我實現。然而實際上,馬斯洛的理論無法涵蓋我們全部的人生。對安全和自由的需求,總是隨著環境變化,交替騷擾著我們。似乎安全和自由是稱呼同一件事的兩個名字,而作者是左右尋找、無以平衡的人,就像你我。
歌手陳昇的歌詞裡,形容對方像風箏迷失風中,有一天總會回頭尋找拉住它的那根線,需要自己給他歸屬感。而莫欣.哈密心目中,它不是線,是支柱。我不禁覺得過去風箏與線的想像,小看了人對關係的需求、和關係穩固人的力量。支柱的想像訴說著「我相信你就是如此強烈地需要我,而我也是同樣堅定地需要你,不能失去」。莫欣.哈密不僅僅行文總是溫厚寧靜,連譬喻的方式,都在召喚穩定、歸屬感。
作者的前一本小說《直到有錢的那一天》,預告般地談到流亡:「我們全都是被迫逃離兒時的流亡者。所以我們轉而去讀小說,當然還有別的東西。寫小說、讀小說,就是逃離身為難民的狀態。作者和讀者都嘗試要找到某個方法,解決時間流逝的問題……」在他眼中,每個人都是難民,流亡於無情的成人世界。在戀愛中尋求童年的完全被接納,渴望親密歸屬感的復歸。《門》描述的,伴隨相互責任感的羈絆,也許就是作者在這個階段的理想。它溫情脈脈,盡力自抑,抓住機會表達善意,相約不出惡言。
而讀者無法從故事中得知引起這場戰亂的罪行和訴求。正如我們仍不知,體內那股將人們互相拉近、推遠的蠻暴力量從何而來。這本書最終的使命是,暫時擱置政治與愛情,從難民生活的點滴膚觸中,讓讀者感受這些人的真實存在。
小說中,難民會幫助難民。難民會詐騙難民。小說中,難民有好人,有壞人,就像每個社會。過程需要溝通理解,懲罰背叛信任之舉,在治理的基礎上才能構築信任、開放、融合,這是上百年的近代化長路。在真正的治理實現以前,《門》預先許諾我們信任與安全感。因為無論在政治或愛情中,都是這明亮的願景,引領我們願意走向對方。但願不辜負這願望,受挫但不失望,失敗但無後悔。只要雙方不騙人、不暴力,那麼信賴總是能夠無窮延續,總是有能力再去愛人。
莫欣.哈密教了我們不同的人能夠好好相處的秘密,就是彼此珍惜。在熱情之後,珍惜對方帶來的暖意。受怒火傷害時,珍惜對方的善良。跨過名為「我」的這道門,踏入「你」的世界,在對方臉上看見嬰兒的純淨脆弱,因而口氣放軟,用雙手輕輕捧起。
童年熟悉的、企盼的歸屬感,就在這當中萌生。無論未來是戰亂或和平,總有一種值得過的人生等待著我們。而它只能在這當中萌生。
盧郁佳
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人、《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輯、《明日報》主編、《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全職寫作。曾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有《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亦參與《字母會》小說創作。
延伸閱讀





![傾城之戀:短篇小說集(1)一九四三年[張愛玲典藏新版]](https://www.books.com.tw/img/001/047/28/001047284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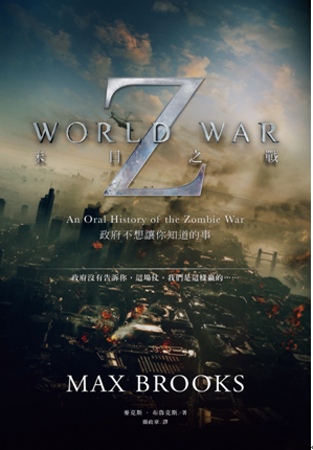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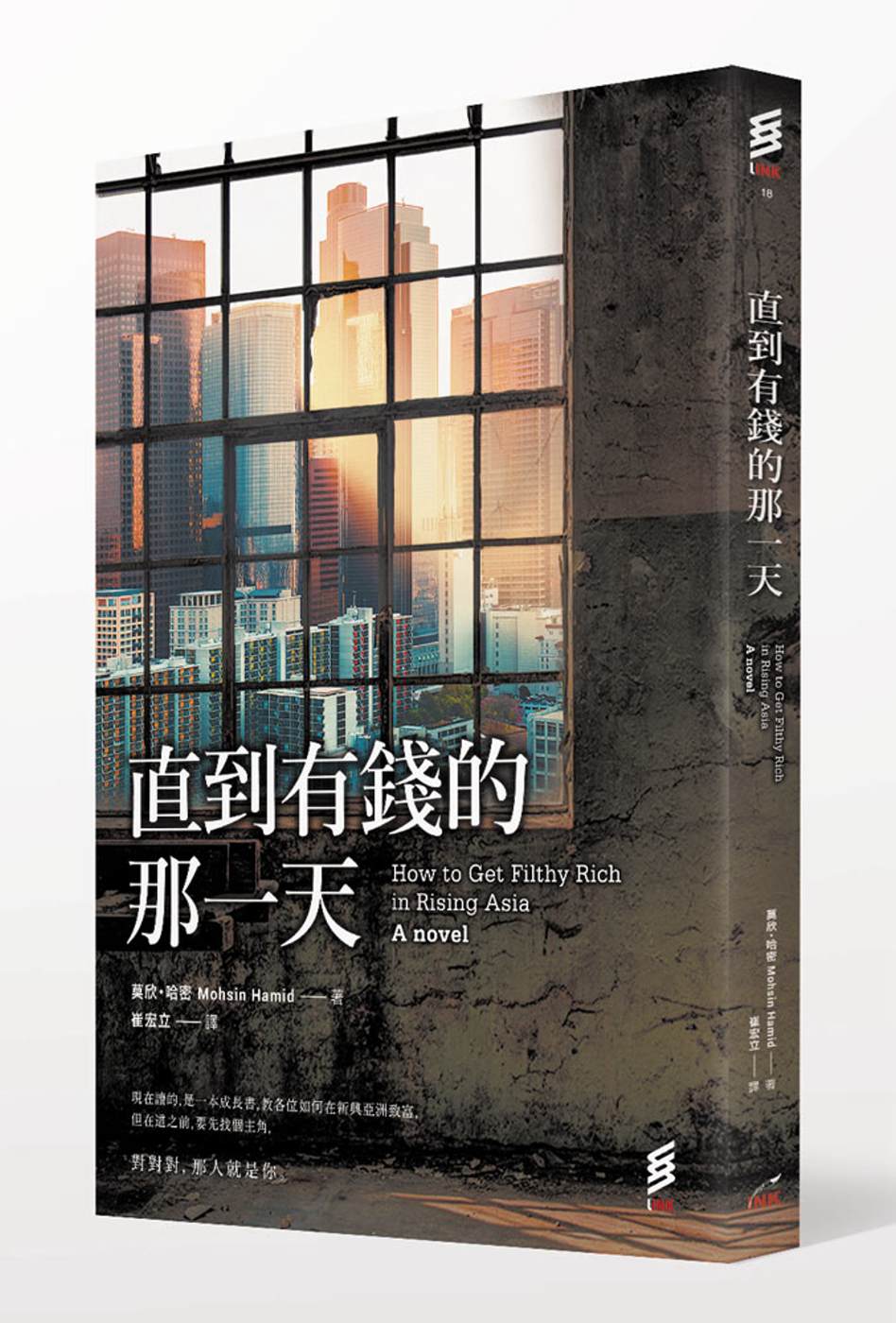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