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個社會的真相會展現在兒童身上。世間最美麗與最醜陋的,也往往是兒童經歷的人事物。兒童因此不該被當成下一代,而是完全的社會行動者,他們在形塑其日常經驗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專題評論《羅莉塔》、《最藍的眼睛》、《麥田捕手》、《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五本與童年有關且極度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這些少年角色做為行動者,深刻見證了種族、性侵、階級、性別認同的世間悲劇。評論者將帶我們到小說家描述的成長現場,文學使童年抵抗具備永恆的人性之姿。
成為黑人
自個人第三部小說《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年)起,摩里森(Toni Morrison,1931∼)成為我們理解的摩里森:一位寫作目標,「不是去對抗白人威權」,而是「想誠實描述一個黑人的社會,並在她的描述中寫出黑人語言韻律中的文學性及美感」的非裔美籍小說家。接續前作《蘇拉》(Sula,1973年)遙置的時序終點,1960年代,《所羅門之歌》直探這一美國種族民權運動勃興時期裡,黑人社群的內部衝突。在前作裡,本於同一原型的兩位女性角色,妮兒與蘇拉,由小說家在《所羅門之歌》中,延異並更確切分化為一組男性角色,即奶人與吉他。兩者共有童年情感記憶,在成年後因現實認知而別異,最後,且又相遇於曖昧終局—不知「兩人究竟是誰遭到另一位弟兄雙手扼殺而畢命」—的這一整體敘事設計,示現了摩里森想在相似空間跨度裡,以更多現實細節,針對黑人主體尋索此事所做的討論。
做為角色,吉他的動機相對可解:經歷了種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他加入暗殺團體「七日社」,本於自言的,對黑人同胞的「愛」,但逢同胞遭白人殺害即行報復,源本複製殺害手法,以牙還牙。復仇行動引致自身混亂,使他起而獵殺奶人:也許,是因對「愛」之純粹性的想像,使吉他心中,深恨那些模仿白人的同族之人,更甚於恨白人。
奶人則承載相對複雜的辯證,帶起對黑人存有之純粹性的反思或自譴。早在他能自覺前,在成長過程中,他已由父親隔離於資產階級生活內。這生活型態仿擬白人資本家,無處,不銘印父親獨力脫貧的自矜暨自傲,匱乏與貪婪,及對窮困親族的徹底鄙視:父親的自我成就,在於終獲立場,去賤棄那些與自我根源相似之人。小說後半,當奶人代父重探美國南方,一方面,他複製父親感知,惶惑於這「一群可鄙的黑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野蠻人」;另一方面,就自我根源而言,他開始對藏存祖父一系集體記憶的黑人口傳敘事,及祖母所來自的美洲原住民血統與文化,均不無矛盾地,產生了鄉愁般的感懷。奶人的自我覺察,是在親歷裂痕重重的過往後,他已然失去單純立場,去指陳因於特定的某種傳統,「我」,該當是誰。
祖父系歷史,與祖母輩故土。《所羅門之歌》的終局,收束且離散於個體的多向鄉愁,直證了橫亙近半世紀,黑人詮釋社群對自身之「黑人性」(négritude)的艱難重構。就此而言,摩里森後續小說,不為提出單向而恆定的解答,而為將此命題重新問題化:原鄉既已渺無定址,往歷重建者,能多大程度,傾身容受此時此地,多元並存的現實;一如《所羅門之歌》全景明喻的,那種起於「慈愛」,終於「若降服於大氣,便可御風而行」的悖論式飛翔。
這是摩里森為美國文學史重置的起點:小說家擬以作品前瞻歷史想像,平議排他論述,從而,可望以自身創作,點出如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所定義的複數「起源」(beginnings):星群一般,摩里森作品,無論實踐上純熟與否,無疑的,均一體呈現了反思己身的勇氣;皆是對意義之刻意製造,與和既存典律決裂的第一步。這些作品的企圖,是在觸發後續文本的可能性,且也為將來的「我們」,更寬廣地預演了,什麼是應該被共同理解與接納的。
摩里森的首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年),即以極端貼近小說家本真情感的方式,明白標注上述反思勇氣,與未來意向。就修辭本真而言,《最藍的眼睛》直觀近於詩,類似王安憶對作家第一階段作品的著名見解:既「帶有非常純粹的感性」,尚未被作家將來識見,或技藝進步給「汙染」;也呈現了作家本人,非常難以在後續創作裡複製的「原始」詩學。
或許,這個詩學的原始目的,尚不在提出辯證,而在落實斷言。大概因此,
摩里森發動書寫的聲明(thesis statement),很奇妙的,即是小說結論,寫明在《最藍的眼睛》最後幾頁—小說家想說,最後,且也卸下虛構審酌去正面直說的,是「一位黑人女孩渴望有一對白人女孩的藍眼睛,她的渴望其核心誠然窩藏了某種猙獰可怕的東西,但更猙獰可怕的是讓這渴望得以實現的邪惡」。當小說的聲明即結論,就敘事結構而言,《最藍的眼睛》的重點,已不在如何完整鋪陳虛構情節,而是在如何將一切情節,截出相似的銳利斷面,導向上述結論的一次次具實。簡單說:小說的目的,是在以勾勒出活在「邪惡」裡的真確體感,直接刺痛它的讀者—即摩里森想像中,這名黑人女孩的同族之人。
於是,《最藍的眼睛》最簡明扼要的解讀法,是將整部小說,定視為發生在主角琵可拉身上的苦難,向著場景前後延伸的複寫。這是說:雖然小說篇章,依著四季線性分布,而顯得若有進程,且摩里森也的確為琵可拉,設計了初經來潮之震撼,這類「女孩們經常被告知」的啟蒙橋段,然而,線性時程,僅是聚合敘事跳躍與轉換的必要機制。一如就我們所知,當摩里森首次潛入主角內裡(第一篇章,「秋」),去摹寫這名黑人女孩的感知時,我們不確定究竟是從何時起,但總之,已有「整整一年」,她夜夜禱告著,祈求能有一對漂亮的藍眼睛。一方面,是她猜想,若能擁有這樣一雙怡然明淨的眼睛,她那深陷貧窮泥淖,也因此愈發彼此虐待的父母,就會在她的目視下莊重相持。另一方面,是因向來,備受歧視的她,「只看得見那要她看見的:另一種人的眼睛。」
在一個人行道地磚碎裂、蒲公英蔓生,一切皆使人心生柔慈或自憐的秋日,她走入街區小雜貨店,沉默且卑怯地,容受白人店東的嫌厭,終於買得喜愛的瑪麗珍糖。她走出店外,被地磚絆倒,自己再站起,覺得憤怒或恥辱,一時都好了,因包裝紙上,金髮藍眼的瑪麗珍正對著她笑。「她吃起糖果,甜得恰到好處。咬囓這糖果彷彿咬囓眼睛,咬囓瑪麗珍。愛瑪麗珍。成為瑪麗珍。」這場景使人悲傷,不僅是因歧視本身,更因這名承感歧視的女孩,衷心渴慕著,想成為那能歧視自己之人,以異於奶人父親的方式,以自己齒牙,以血肉,以如摩里森所言的,「受限於年齡和性別,只能實驗各種隱忍的方法」,這般靜默地消解可憎的自己,在自所據在之地,甜滋滋的,同化成一個不是自己的,「另一種人」。
小說循此精神分裂式的自我解離,從過去,越過上述場景,到未來,為我們先後追蹤琵可拉父母的相仿體驗。在「春」之篇章裡,我們首先見歷一個冷酷場景:在白人家裡幫傭的母親寶琳,重視廚房地板的清潔,更甚於燙傷的女兒;她無比憤恨,一巴掌打倒彷彿入侵者的琵可拉,隨即轉身變貌,溫言撫慰雇主那名金髮小女孩。繼而,摩里森以第一及第三人稱交錯的雙聲部,為我們細說從頭,檢視何以寶琳,會以替白人幫傭、討他們喜愛為榮;何以當執行白人家管的工作時,她「把這次序,這美麗,當作一個私密的世界,為自己珍藏著,從不引進她住在店頭的家,或者讓她的孩子分享」。
接著,摩里森轉而回溯琵可拉的父親韭里,那千里流徙的一生,從出生才四天,就被自己母親拋棄於鐵道旁廢物堆上,直到撿回、並庇護自己的姨婆之死。從情竇初開的他,與女孩達琳在野地歡愛時,遭兩名持槍白人,如觀看兩隻幼獸交配那樣,喝令他們「繼續他媽的幹,黑鬼。」的那一屈辱場景,直到他穿渡整個令他深覺「汙辱是人生必須忍受的煩擾,就像蝨子一樣」的美國南方。從他與寶琳墜入情網,兩人北上俄亥俄州,依憑勞力,尋索自由生活;從在國境北端,無望地察知事實上,對黑人而言,舉國並無自由之境可去,直至最後,在一個陽光稀薄的春日午後,在自家廚房地板上,恍惚的他,強暴了再度自我消解的女兒,琵可拉。
由此,在摩里森的藍圖裡,上述家族病歷史的追蹤,乃揚長始終、疊合且收納於琵可拉的受創體驗。直到這般體驗仍然持續,在最後的「夏」之篇章裡,我們重見琵可拉,仍然在祈求一對藍眼睛,依舊,一如走入故事之初那般渴慕。像之前已述的,關於她的具體遭遇,事實上,並無法再更加重她本就沉重的存有處境。當時間進程的意義如此,在《最藍的眼睛》裡完成自我抵銷時,關於琵可拉的重複受創場景,也就沒有任一個,是心理學意義的「原初場景」(primal scene)了:那最初的銘印或撼擊,彷彿來自個體已無可考察的更久遠之前。於是,做為敘事之不變歸向的琵可拉一人,也就全景轉喻了她父母的普同存在癥狀;一如摩里森嘗試以寶琳和韭里,轉喻再更長程以來,美國黑人的普遍處境。
個人短暫的生命履歷如此,指涉向集體長程受辱經驗。也於是,《最藍的眼睛》雖然動用成長啟蒙小說框架,但也許,這框架亦注定形同虛設。主要因為對主角琵可拉而言,並無個人啟悟,需要由成長小說仰賴的情節編排來序列發展與陳明。也因為初始,雖然摩里森設定了童蒙旁觀者,來敘述整個事件,並承當受啟蒙的任務(這是成長小說的另一常見套路:一名稚幼的「我」,借著「旁觀他人之痛苦」獲致啟蒙,從而走出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一如哈波.李(Harper Lee,1926∼2016)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1960年),然而,相對於《梅岡城故事》裡的白人女孩「我」,可以用孩童式的直接修辭,有力表述她對種族歧視之不義的直覺,摩里森想藉《最藍的眼睛》,向女孩同胞(即想像中的讀者們)指明的,同族之人的可悲與可鄙,顯然,超出了孩童「我」的單純視角,所能負荷的程度。
大概因此,在《最藍的眼睛》裡,摩里森的敘事,必須不時拋開敘事者「我」的視角制約,一再曝現小說家自己的聲音;因此,不免也就讓整部小說,在過度無知,與極端全知間搖擺不定了。全書不乏強作解人之處,例如對敘事者「我」,事實上不可能窺知、亦不可能聽人完整細述的強暴場景,摩里森著意敲磨細節,代言,獨語論斷其為一個充滿「憐憫」、「柔情」與「愛」,甚且不無宗教氛圍的行動—也因此,琵可拉一家的姓氏「哺愛」(Breedlove),終究顯得像是一種過於刻意的覆核。例如對小說家自言的所謂「愛」,在小說結語處,頌歌式的熱切言表。所有類此修辭,可能,均不具有太大說服力:當小說家並未(如她保留給寶琳的那樣)給予韭里充分的自訴空間時,她對強暴場景的細描,也許無論如何,均無法不顯得太過一廂情願地浪漫化了。
另一個過於刻意的覆核,或意義製造,是摩里森將強暴場景,及是年的土地不毛,綁定於1941年。原因無它:這是美國開始參與二戰的殺戮之年。我個人認為:這誠然是十足「美國化」的想法;彷彿二戰殺戮,不是早就在美國境外,舉世且經年長存。事實上,要到《蘇拉》,小說家才能藉由虛構小鎮裡,一戰倖存與病廢者薛德瑞的感知,為這時點設定,做出更具意義的討論。而如上所述,要到《蘇拉》之後的《所羅門之歌》,摩里森才能以奶人和吉他的角色共構,與敘事任務分化,更豐富地統合前作未竟的啟蒙陳述。
這具體說明了小說家之虛構技藝的持續進境:從《最藍的眼睛》、《蘇拉》,到《所羅門之歌》,這三部完成於1970年代的小說彼此索引,一方面,為我們將一種內向詩學,逐漸外顯為未來,更具對話能力的摩里森小說。另一方面,比較三部小說所調度的場景,我們當然也能明確看見,小說家正緩步將牽涉更廣的空間,從個人履歷童年的時代,延伸向距寫作時間更久遠之前,或聚焦於更當下的此刻。這是說:在面向自身詮釋社群,當小說成為一種以「文學性」,去繞徑對話的載體時,摩里森的創作,其實已是個人,對「黑人性」之提問的,一次次更全面,且再更深思的答覆。
也於是,做為個人首部作品,《最藍的眼睛》以其迫切源湧的直訴,為我們封存的,正是摩里森的最初答覆,與總結向後續作品的重新提問。小說為它所刺痛的讀者,表明了種種苦境裡的病變,或摩里森直言的「邪惡」。其中一種最使人不忍直視的也許是:在「體悟出對白種人的恨」之前,黑人總已先憎恨自己,與「那個親眼目睹他的失敗、無能,他無法保護」之人。一如與女孩達琳,自野地生還時,韭里的當下感知。而在終於悟出這樣一種恨之後,韭里無論如何,會更需要自所憎恨之人。韭里需要自己的妻子寶琳,因「她是少數幾個令他厭惡但卻搆得著因此傷害得了的東西」。因為「恨她,讓他自己豁免於受傷」。
小說亦為未來的摩里森,與她面向的理想讀者,動態重啟種種關於「我們」的探索。其中,最牽引小說家後續作品的質問也許是:是否「成為黑人」此事本身,終究是一種令人悲傷的另類啟蒙體驗,因為「我們」,不會一次性地跨過「過渡」階段,就重新而永遠地與世界「融合」了── 一如世人對成長儀式的預期。是否,意識到自己是黑人一刻,所肇啟的痛苦,不僅是因從此,「我們」只能在自己國家裡流徙,且也更是當這理解一發生,「我們」也就注定了,要終身與自我離異,就地成為自己的陌生人。無論「我們」,能暫且安身何處。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
延伸閱讀
1.【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書評】胡淑雯:記憶,你還要我嗎?──讀《羅莉塔》
2.【專欄】通往幸福美滿的生活,從擁有白膚藍眼開始:談《黑女孩》與《最藍的眼睛》
3.在希望與心死之間──2015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當代美國黑人文學最重要的論述《在世界與我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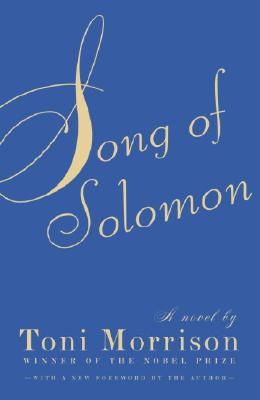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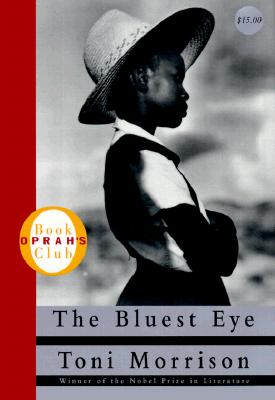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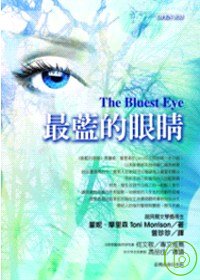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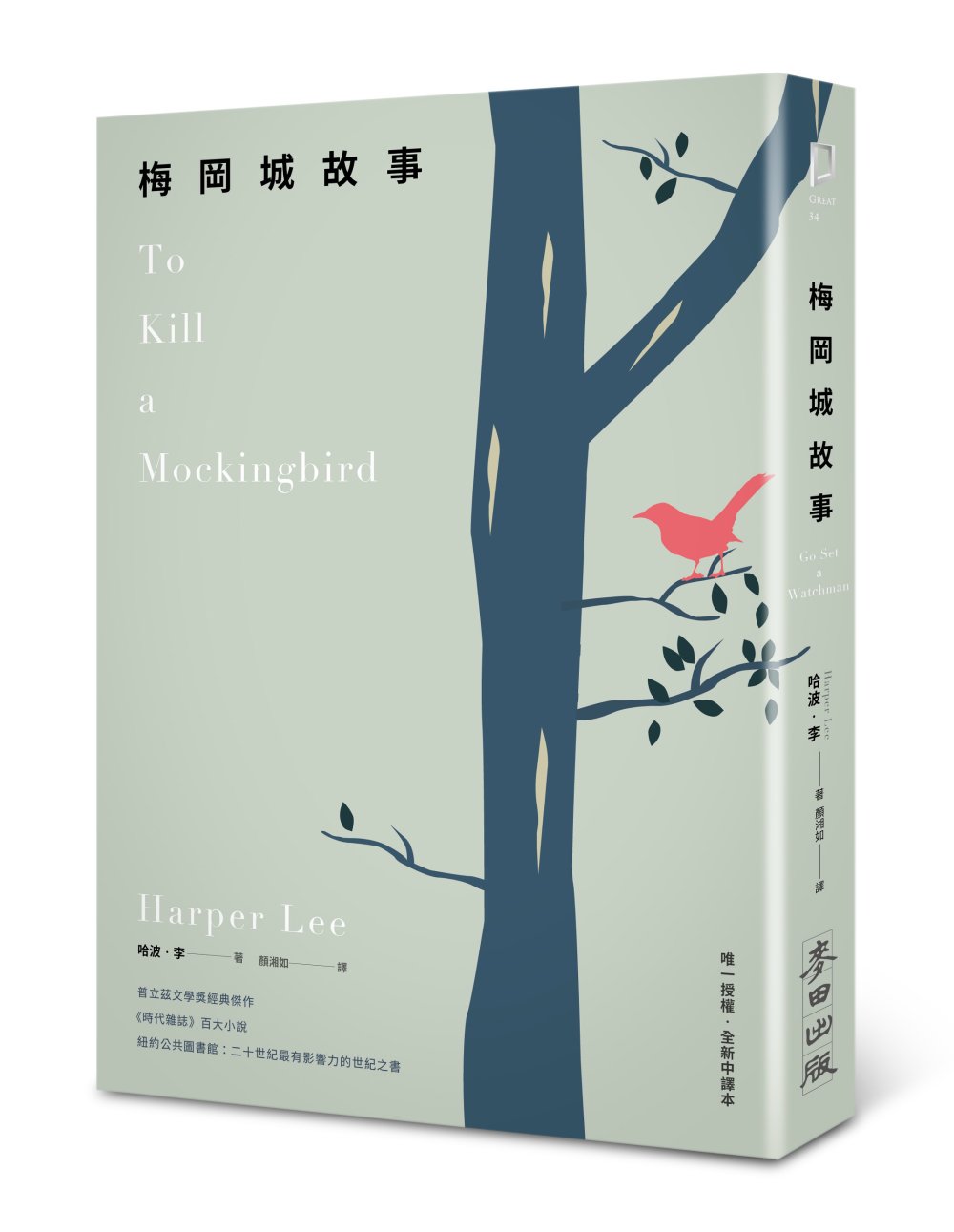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