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出版繁中版是件大事,雖然台灣對於日本交流甚密,但台灣出版市場對於日本詩歌的翻譯量與小說相比落差極大,除了谷川俊太郎有比較完整的繁中譯本,其他日本作家的詩集在台灣並不多見。高村光太郎作品兼具情詩的渲染力,在日本文學史也是相當重要的作者。讀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你會發現有一條隱形的時間軸,從如何愛上到相思之苦,詩人捧出自己的心,坦誠一片讓讀者閱讀。開始愛的時候,舉凡一切都是詩,這不難理解,舉凡一切都可被愛拯救,不良也會從良,世間情歌都有一種普世價值,一如情人間的思念不用翻譯,可以跨越語言國界直抵人心:
每當想念你的時候
我最能感到永恆
有我 還有你
此是我的一切
我的生命 與你的生命
互相糾纏 糾結 融化
歸於混沌不清的原始狀態
所有的歧視在你我之間失去價值
──高村光太郎,〈我們〉
 左為高村光太郎,右為其妻子高村智恵子。(圖/wiki)
左為高村光太郎,右為其妻子高村智恵子。(圖/wiki)
愛令人擁有快速通關證,所有關卡放下檢查,所有閘門自動開啟,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兩人,貴賤與貧富瞬間因為愛而變得無差異。愛人變得超凡,變成打破尋常規矩者。就像高村光太郎與智惠子當時不顧一切的結合,面對愛,只有對於愛索求更多:
我不願意
不願意你離開我──
就像結果比開花早
就像發芽比種子早
夏天跳到春天似
請你不要做
這種不合情理的舉止
──高村光太郎,〈給人(我不願意)〉
但高村光太郎的情詩不單單只是如此而已,當愛是如此絕對,愛也最禁不起考驗,當愛情的純粹被現實的不幸折磨得體無完膚,這對因為藝術而結合的神仙眷侶,面對憂鬱自殺乃至於雖然救回生命,眼睜睜看著智惠子日益枯槁的精神,高村光太郎寫給智惠子的詩,在此階段來到一個新的大氣層:
──我快要不行了
山風冰涼地撫摸被眼淚弄溼的手
我沉默注視妻子的面貌
從意識邊界最後一次回頭
摟住我不放
此生已無計可施挽救這妻子
我的心此刻裂成兩半脫落
──高村光太郎,〈山麓的兩人〉
面對精神疾病纏身的愛妻,彼時,高村光太郎在〈乘風的智惠子〉一詩用彷彿顫抖的字寫下──「藍鵲和白鴴才是智惠子的好朋友╱對於早已決定不要繼續當人的智惠子來說╱極為美麗的早晨天空是絕佳的散步場地」,對於早已決定不要繼續「當人」的愛妻,作者已經心知肚明自己正在經歷漫長的告別。愛仍然在,詩仍然在,愛已分泌出苦的乳汁,高村光太郎在智惠子臨終前仍用詩紀錄著這份情感,作品〈檸檬哀歌〉藉由妻子在病逝前啃咬一顆黃檸檬,檸檬的酸冽「忽然讓你的腦袋恢復正常╱你清澈的眼睛微微一笑╱握住我手掌的你力量何等健康啊」,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用生之燦爛寫死亡寫「器官從此失靈」。肉身的死亡是愛的完結嗎?這首詩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對愛的意志仍然堅決:「今天也要在遺像前裝飾的櫻花後面╱放一顆涼爽發亮的檸檬」。檸檬已是永恆的象徵,是她的借屍還魂,也是他在心中無法被取代的位置。
 智惠子1938年病逝於東京南品川ゼームス坂醫院,醫院裡設有紀念碑。(圖/wiki)
智惠子1938年病逝於東京南品川ゼームス坂醫院,醫院裡設有紀念碑。(圖/wiki)
品讀之時,我們也可以從高村光太郎的散文紀錄〈智惠子的半生〉、〈九十九里濱的初夏〉等篇章補白了兩人相處的細節,高村光太郎在智惠子往生後寫了許多「亡妻詩」,這也是他備受後人認識的系列作品,面對一方的肉體已經達到永恆,一方的身體面臨衰老,高村光太郎如是寫著:
在我細胞上燃燒磷火,
與我玩耍,
打我,
不讓我昏庸老朽。
精神便是肉體的別稱。
──高村光太郎,〈元素智惠子〉
又如〈裸形〉一詩,想念愛妻有形的身體:「我想念智惠子的裸形。╱謹慎充滿的╱彷彿星宿一般森嚴╱山脈一般波動╱總是籠罩著淡霧,╱這造型的瑪瑙質中╱具有深邃的光澤。」肉身埋葬後歸回天地山川星辰,想念的介質也變成了山川星辰。儘管努力的想念,但回憶仍禁不起時間和遺忘,那怎麼辦呢──「我連智惠子裸形的背上黑痣╱都記得一清二楚,╱如今被記憶的歲月磨光的╱存在即將明滅。」在此,詩人用詩句回答:「由我雙手再次創造」……
愛要如何再次創造?這令我想起「木化石」的形成道理,或許,這份愛像是形體枯槁的樹木,卻因為石化而質變成植物化石,木質結構和紋理仍在,但木頭已質變成更堅硬的礦物。如果愛像是樹木的年輪,年復一年都會留下痕跡,高村光太郎的詩就像是巨大的神木,我們可以藉由閱讀他的詩作,體會愛在時間巨河的各種風景。
最後,想提一下對於高村光太郎詩具有標籤意義的「亡妻」書寫,古今中外都可以在文學史上找到精彩的作品,一如中國古典詩詞作家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等等。相對於男性作家對於妻子的弔念,女作家「亡夫」書寫可以說是相當稀少,難道,這代表女性書寫者對於伴侶的不深情?每每想到這裡我就忍不住發笑,扣除識字率和男性作家多於女性作家的數量等外緣問題,我的推測是──丈夫對於妻子的依賴,沒有了可比天崩地裂,相反的,妻對於夫的離世,會不會反而是鬆了一口氣?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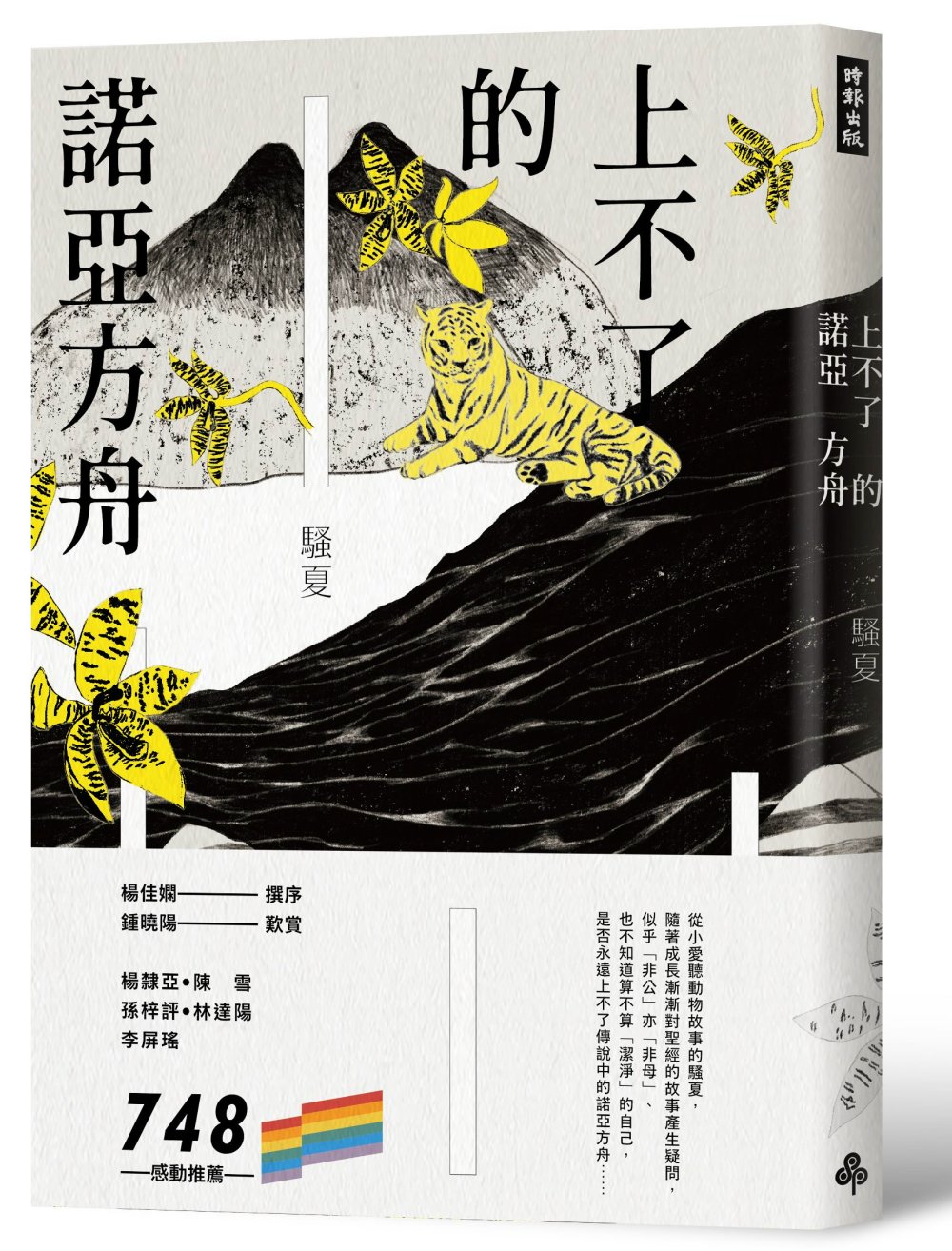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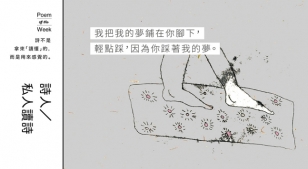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