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世界啊!我沒有什麼本錢跟你齜牙裂嘴的搏鬥,
但我仍有一支筆來當小刀,以為陰暗可以被我劃出一道一道縫隙來。讓那裡透出來稀微的光,能刺眼出我久違的眼淚。
一起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吧!
它被我們搞壞了,但我們仍有傾斜看它的角度,一眼認出它曾經的美好,於是抱得滿懷,即使即將失去。
這就是電影存在的理由,紀念我們所有可能失去的美好,還有我們曾經被拍下的純真。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阮玲玉身為一代默片巨星,演過所有女性制式的悲劇角色,但銀幕上她總是笑著,到後期每一笑都是眼淚。她是演活了面具本身,也演活了身為女人難逃活在謊言的悲劇,至今她仍對照著自由,提醒著世上仍有「無數個阮玲玉」內化了男人千古的視角。
阮玲玉身為一代默片巨星,演過所有女性制式的悲劇角色,但銀幕上她總是笑著,到後期每一笑都是眼淚。她是演活了面具本身,也演活了身為女人難逃活在謊言的悲劇,至今她仍對照著自由,提醒著世上仍有「無數個阮玲玉」內化了男人千古的視角。
 1930年代活躍影壇的女星阮玲玉
1930年代活躍影壇的女星阮玲玉
關於女人的悲喜劇總是過度的,像看倌嗑瓜子一樣都圖的是那一口閒情與勁道。
更遑論是專職演悲喜劇的女人,她們聲嘶力竭著、她們杜鵑泣血著、她們喜上眉梢著,彷彿這些那些都是命定的。不敢太過得意、安分著、端著、歇斯底里著、巧笑倩兮著,如我們看膩的上海仕女圖,都是腴白的,不動聲色如浮在水面的,讓你賭著她是好運還是壞運哪個陣線的。銀幕上女人的悲喜劇都調得濃稠,都不像真的,有太多雷同,看戲的對待她們如同就算哪顆瓜子嗑不出仁來,也就呸了一聲,繼續在瓜子堆裡找新貨。
我們從小看著女苦旦長大,誰與她們的哪個角色較真過,至今也沒有一個。
關於「阮玲玉」的悲劇哪只是人言可畏,而是她無論扮神女還是聖女,成全的都不是自己,被妖魔化或天使化成就的都是他人的一地寥落。銀幕上的幾刻真情,入人眼後終究是矯情。如同張曼玉要演「阮玲玉」前得知她之前都演花瓶,所吐露的那句真心話:「那不就跟我一樣?」非要以一個激烈的角色,如阮玲玉以一個以血餵孩子的貧苦母親轉型,這般聖女形象哪是哪個女人擔得起的,這些幾百年來輪迴的聖女十字架總得要換人擔著,不是訴諸哪個真實角色,演得更像一種女性幾代宿命的暗示。
而這些演得像樣的美女,角色落幕後仍跟著這些女演員,讓人們議論著她們人生的好壞運,是悲還是喜劇?除非妳是像歸亞蕾、吳靜嫻那樣良家婦女的密不透風,若妳曾有幾分昂揚、幾分自我顯露於人,眾人對於妳的賭盤就開始了,無論妳是林青霞、張曼玉、王祖賢,還是擁有盛名如阮玲玉,人們都會把妳的人生一把梭哈一樣地丟在賭桌上,趁著幾分餘溫,猜妳際遇是落了地還是上了天,更有甚者將大量女星猜測為聖女或是神女,對待阮玲玉如看待她的角色,除了聖潔或是墮落外,沒當妳是真人一樣的踩踏過去。
我們看戲總在賭一個女人的面具戴得是否夠牢,甚至以此為榮。歷來女人欣賞的角色甄嬛、武則天、魏瓔珞,無非都是將自己的面具卡得死緊,以騙局來報復,誰管妳是否輸了自己,一旦把面具拿掉了,即便是《控制》的愛咪、黛安娜、惠妮休斯頓,誰不是在自己面具裡尖叫過。於是我們誰也都不認識「阮玲玉」,但都藉著導演關錦鵬整理歷史資料後的傳達,為她的悲劇悲泣著,因為這是一個女人被面具控制,終不得自由的故事,「她」是許多個女人。
由關錦鵬傳達出來的這位30年代的巨星是什麼樣的呢?從電影裡的默片中看到的她演出早年親人亡故的孤女悲劇、被剝削後在床上最後聲嘶力竭地喊著:「我要活下去。」從那少數的短簡殘篇中,看得出都是一個女人對救命符的呼喊,無論是否戲假情真,她演得總想抓住什麼。她在演一個妓女時,在被惡勢力逼迫下討根菸的身心反抗,就那麼微小的反抗,已經用盡了全力。
那一幕她弓著身坐在桌上,放棄女人的撩人姿態,是一癱死肉的反抗,你在想像這在30年代,甚至是近代,女人化為死肉般的姿態是多麼頑強的示威。非男也非女,僅僅只是團肉都更有尊嚴的終極反抗。
 阮玲玉在《神女》中,被惡勢力逼迫下,弓著身坐在桌上討菸。(右為《阮玲玉》中張曼玉的版本)
阮玲玉在《神女》中,被惡勢力逼迫下,弓著身坐在桌上討菸。(右為《阮玲玉》中張曼玉的版本)
「阮玲玉」的悲劇感更是橫跨了封建時代女性角色與新女性自覺角色,後期她開始演女性自主的戲,如後來因批判媒體而遭撻伐的《新女性》,她飾演的知識分子韋明,雖有才華,卻逃不過男性的身體壓榨。她在戲中容不得哭的笑容,與她最後的「我要復仇,我要活下去。」那點支撐她活下去的支離破碎,是一點尊嚴與自傲,她片中各種討好笑容都暗示了眼淚。看過那默片(曾在台北電影節放映過),你約略知道她為何是關錦鵬想拍的人物,她演活一個在封建時代的自覺女性,時時不動聲色的悲傷著。
因此關錦鵬以能體察女性的男性導演的距離拍攝剛好,我們看到一代巨星如何走不出女性的塵網裡,既不見容於女性,也逃不出一個男性視角的社會。即便是當時自以為的新女性,仍以比男性更嚴格的視角審視她的愛情關係,以欲女或聖女來標籤她,沒給活人路走。這由《阮玲玉》一幕中,張曼玉走在路上,明著槓上那些路上指點她的群眾,那毅然轉身的對看,對照了阮玲玉,也對照了張曼玉,當時張曼玉正因情書緋聞被口誅筆伐。無論是30年代還是90年代,女明星的處境沒有不一樣,人們永遠等女神落人口實,永遠要妳在聖女與神女兩邊對號入座。
 《阮玲玉》中張曼玉走在路上毅然轉身對著路上指點她的群眾,對照了阮玲玉,也對照了張曼玉。
《阮玲玉》中張曼玉走在路上毅然轉身對著路上指點她的群眾,對照了阮玲玉,也對照了張曼玉。
女人演戲是演戲,還是演了更多在笑容背後的荒謬?關錦鵬這部偽紀錄片給了給了多面視角,那些抗戰前的法租界笙歌、未定之天的局勢、有酒今朝醉的麻痺,那時代是不安的,阮玲玉是默片最後一代明星,有家累且無背景的她,從小在那無從自立的環境下,如何才走到能演《新女性》中哭喊自由的那一步,從孤女、妖女、妓女,演遍了所有被壓迫的女性,最後那個脫去的角色皮囊竟是「阮玲玉」,分分鐘鐘的自我醒覺,卻分分鐘鐘的不可能。
我最喜歡的是張曼玉最後在舞池中自舞的那段,似笑非笑地舞著,帶有幾分嘲笑神色,誰分得清楚我的真假,誰認真看我的虛實?對許多女性而言何嘗不是如此?妳若脫了面具,連同性都會笑妳的,所謂「新時代女性」有時竟是更內化的男性視角,無論新或舊的樣板教條,誰能干涉一個女人在這左右間,邁開的只是自己的前方?
於是關錦鵬安排了張曼玉最後大喘氣地起身,對照了阮玲玉的長眠不起,到頭來,任何高唱主義的群體都是睡著的,只有自己能起身而已,每個人的每次清醒都是孤獨的。
而「阮玲玉」會一直回來;一直回來,因總有女人不得自由,總有女人會在戲院裡為了「無數個阮玲玉」而哭泣。「阮玲玉」自此片之後得以對照了自由,願這份提醒始終不滅。
《阮玲玉》(Center Stage)為1991年香港電影,由關錦鵬導演執導,張曼玉、秦漢、梁家輝、吳啟華主演,改編自二十世紀一代巨星阮玲玉的生平故事。以偽紀錄片的方式描述16歲便踏入影壇的阮玲玉,在短短的9年中拍攝了29部電影,成為影壇一代紅星,然而她與張達民、唐季珊、蔡楚生三人之間的戀愛關係,也使她陷入「人言可畏」的困局中,之後服安眠藥自盡。此片曾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銀熊獎、日本影評人大獎最佳外國女主角獎、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與評審團特別獎。最近隨光點華山電影院舉辦的「關錦鵬【女人心・女人情】 影展」在5月24日至6月2日重新上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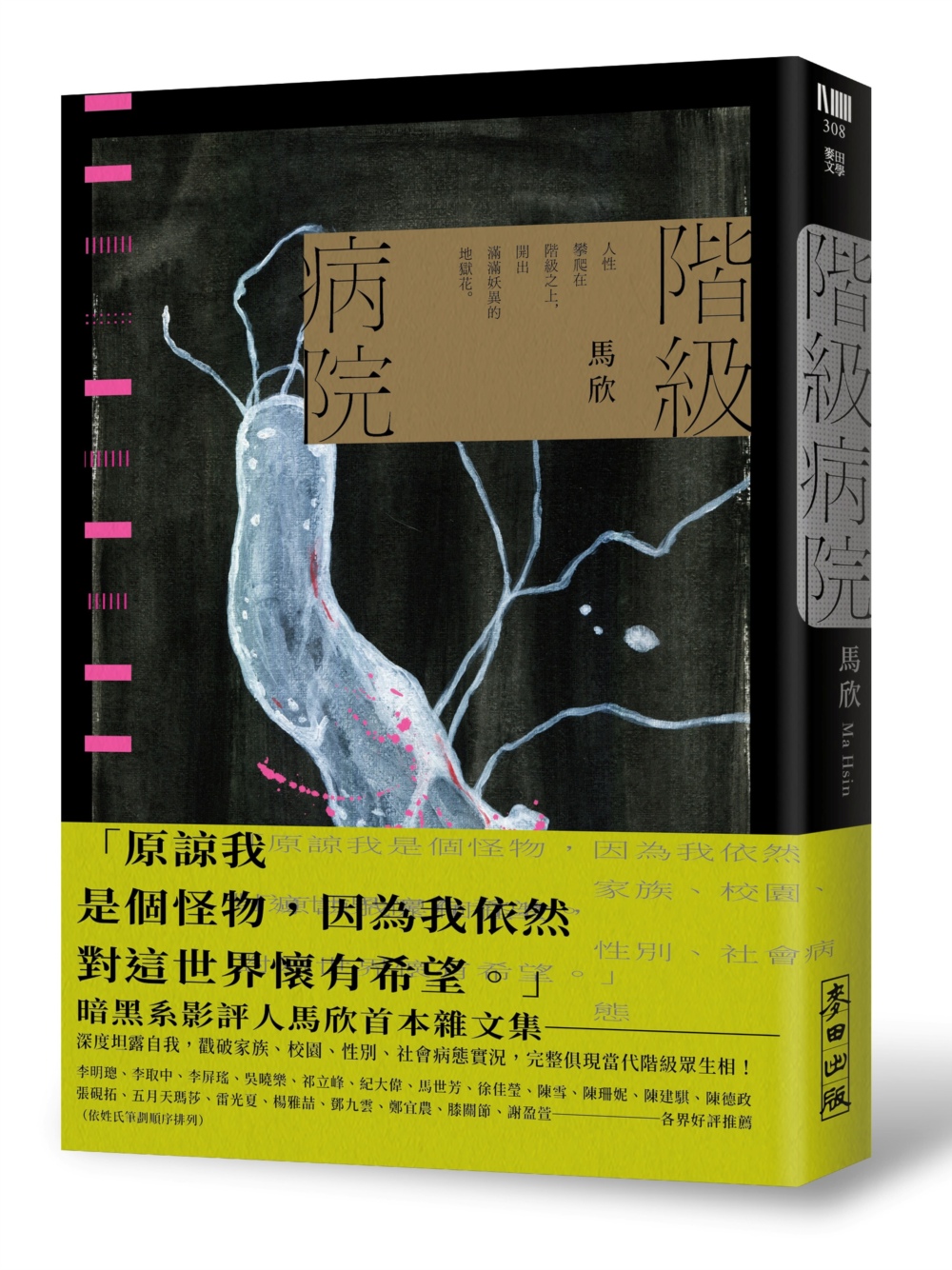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