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這把年紀,我有個殘酷又不失幽默的體悟,那就是每個女同志一生中都碰過至少一次神經病女友,每個異性戀女孩一生中都可能失去過至少一次孩子。這簡直像通關密語一樣,只一吐露,便可在各式陌生場子裡化解歧異、暢行無阻。但寫字的人麻煩之處在於,他們無法只把這些事件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說完哈哈幾聲就算,也無法對記憶貝殼裡隱隱含住的那粒沙子坐視不管。
葉揚說她發現失去孩子的作家會在一段不算太短的時間中無力寫別的,只能寫那喪子之痛,她看著黃春明、陳義芝,然後靜靜坐到他們身邊,把口中苦澀的砂礫一圈一圈包圍起來,那生成的珍珠像眼淚漫無目的串串滾落。
我的過去幾十年,突然如一班列車走了,我站在一旁發愣,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在幹什麼?
──摘自葉揚《我所受的傷》
身為一名母親,如何在擁有新生、失去新生之後,而能再度「求生」?身為一位寫作者,如何能夠直率書寫自己、卻又不落於自溺?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1996年出版的《傷心人類學》裡這樣描述:「記憶過程與被記憶物自身的難以捉摸與可動性,指出存在著『回憶與被記憶物的雙重改變,回憶受某事物影響時便會運作,而被記憶物只有當其消失時才被記得。』」又說,「記憶是一種『改變』的行動」,從這個角度看來,記憶(生者葉揚)書寫源自於被記憶物(逝者,指的便是那沒有機會好好看這個世界的孩子)的消失,而被記憶物注定永遠僅能以「他者」(書寫者葉揚以及讀者我們)角度被看待。書寫者在此以當下素材召喚他處之物事,再以此詮釋公開召喚與逝者沒有切身關聯的我們的情感,這當中主客觀的微妙轉化,便是「寫作」與「療傷」的持續進程。
雖然這樣說有些老套,但看葉揚寫「失去」,不得不說是件療癒的事。比如她寫休完長假回到職場,面對同事關心時:「在凝重的氣氛裡,我們開了第一個玩笑,就像術後放了第一個屁。」這和她寫母親與唐吉軻德的關聯相互對應,她說人們評論唐吉軻德「沉溺於幻想、脫離現實、動機善良但行為盲目。根本是媽媽的典型。他把嚴肅和滑稽,悲劇和喜劇性,生活中的庸俗和偉大,水乳交融在一起。」那樣不合時宜的悲喜通俗劇,形塑了她這場以書寫重新審視受傷事件的主軸。
然而沒有人的苦可以抵消自己的苦,沒有人的傷心可以真正理解另一個人的傷心。我認識有些人,在面對無可挽回的事件時各有他們的自救方法,有人讀書、有人運動、有人瘋狂購物,那是一種生之證明,你的身體告訴你:「你要活下來」、「你得記得」;葉揚也這樣形容與傷口共處時的掙扎:「我生病了很久都沒有好,原因是我一直好希望自己生病,乾脆病到沒有選擇更好。」那是與「求生」本能幾乎同等重量的「放棄」本能,是另一種消極到底的記得。我還認識一些人,必須與自己的「記得無能」爭戰,為自己竟落到「記得不了」都還無所謂而感覺罪惡,儘管與葉揚的經歷與努力看似背道而馳,但在無底的深淵裡與看不見的敵人奮戰,其實是同等耗盡氣力的無間地獄。
無論是「試圖記得」、「放棄記得」或「記得無能」,倘若選擇以自傳性書寫做為與記憶抗衡的具體行動,都不得不面對暴露和反身性的難題。在《我所受的傷》裡,除卻直白的自述外,使人好奇的是,身為一名寫作者,葉揚在事件發生後試著由裡至外地回觀自己如何開始寫作、如何渴望當一名全職作家、試著客觀看待「讀者的介入」,以及最末幾近放棄地以「斤斤計較起剩餘的自己」來描述生兒育女對寫作者的影響。此外,在陳述使她感覺生命斷裂的事件時,她同時還生動地呈現了事件本身如何改變「自己」與「他者」的關係。自嘲做為一種手法,極可能淪為無情或刻薄,但她相當擅長以一種看似毫不費力的口吻講述這場明明把自己搞得天崩地裂的突發意外。這是寫作者的精算之處:Less is More,凝練過的語句含藏更大密度的情感,轉化後的鋪陳與譬喻先一把將讀者推向曲折的滑水道,沖力與離心力最末再猝不及防地將我們猛地滅頂。
在不算短的寫作生涯中,這關乎自我暴露的難題時時刻刻困擾著我。尤其在我的生命經驗與前半段幾乎斷裂的這兩年之間,我曾經列出無數個看似宏觀的寫作計劃,再無數次頹然將它們束之高閣,因為每每在路徑即將成形的一刻,我的腦袋會完全卡關,一方面是生理上的記憶斷裂,使我無法再以從前同情共感的方式取用足夠豐盛的材料繼續寫作;另一方面,我的心理狀態不可避免地為此傷感,在面對那些仿佛象徵著「邁向痊癒」的書寫計劃時,我發現那些主題其實全都圍繞著自己、在意的全是關於「自己」的「失去」(看,我這不就又以第一人稱做為舉例?!),儘管過去曾隱隱感覺那樣自傳性的書寫極易耗盡寫作者的心神,但一生中從未像此刻,我為此感覺厭倦不已。
這是所有走在鋼索上的創作者的宿命:與自我距離愈近,你必得愈警醒,如何抗拒各種心靈雞湯式人生金句的誘惑、如何提醒自己是否輕易寫出看似「引導」他人前往任何路徑的文字、如何時刻意識歸納結論的危險。然而,這也可能完全是個假議題,當你執著並深陷於此類懷疑論之際,你同時將自己拋入了主觀與客觀的無解辯論中停滯不前,做為一名思索者、同時是實踐者(當然,前提是你想這麼做的話),我們僅能試圖跳脫這種對於自傳性書寫的二元想像,去理解各式關乎此文類書寫內容的評論,皆不是外人得以置喙的,沒有人能夠否定過去的自己,同時也無法完美記憶過去的自己,你選擇釋出多少弱處、如何展示傷口,別人最終能感受多少,表面上龐然的感性有時其實是以極大的理性所凝練出來的。溫柔的悲傷是多麼不容易,那倚靠的不僅僅是自身轉化情感的資質,還有賴吸取宇宙眾多陌生的慈悲。
所有人在歷經生命重大事件之際或許都曾自問:為何是現在?為何是我?這一切要帶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真正回答這些大哉問,但我喜歡葉揚在書裡給自己、也給讀者的提問:「如果妳坐下來,跟那個曾經受過傷的自己,一起坐在沙灘上,妳會跟她說什麼?」
倖存至今,面對此般情境我仍說不出什麼勵志小語。想像傷疤已結痂,輕撫其上偶而仍感覺兇兇跳動。我想這是個永恆的問句,我不願自己持續擁有相同的回答。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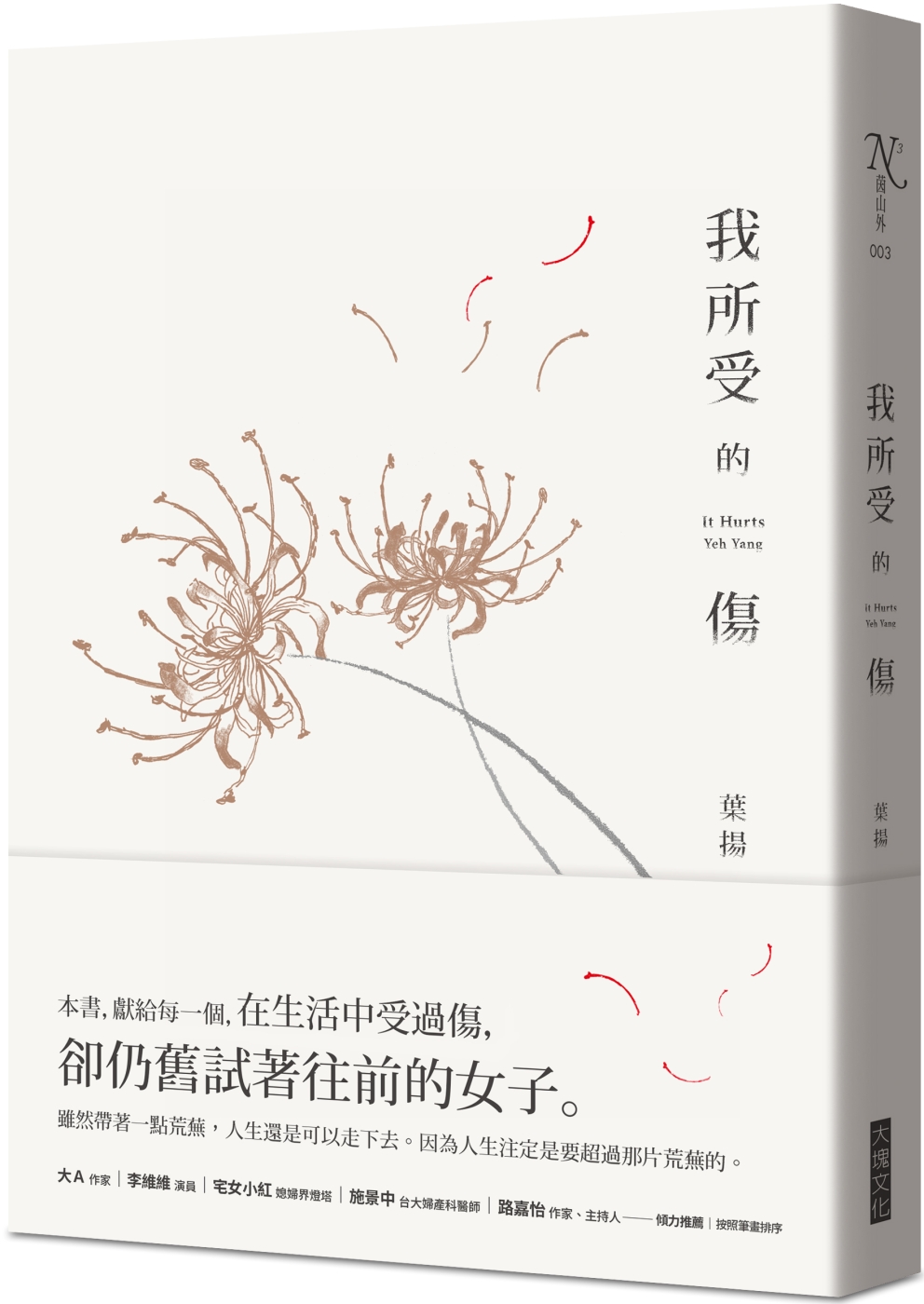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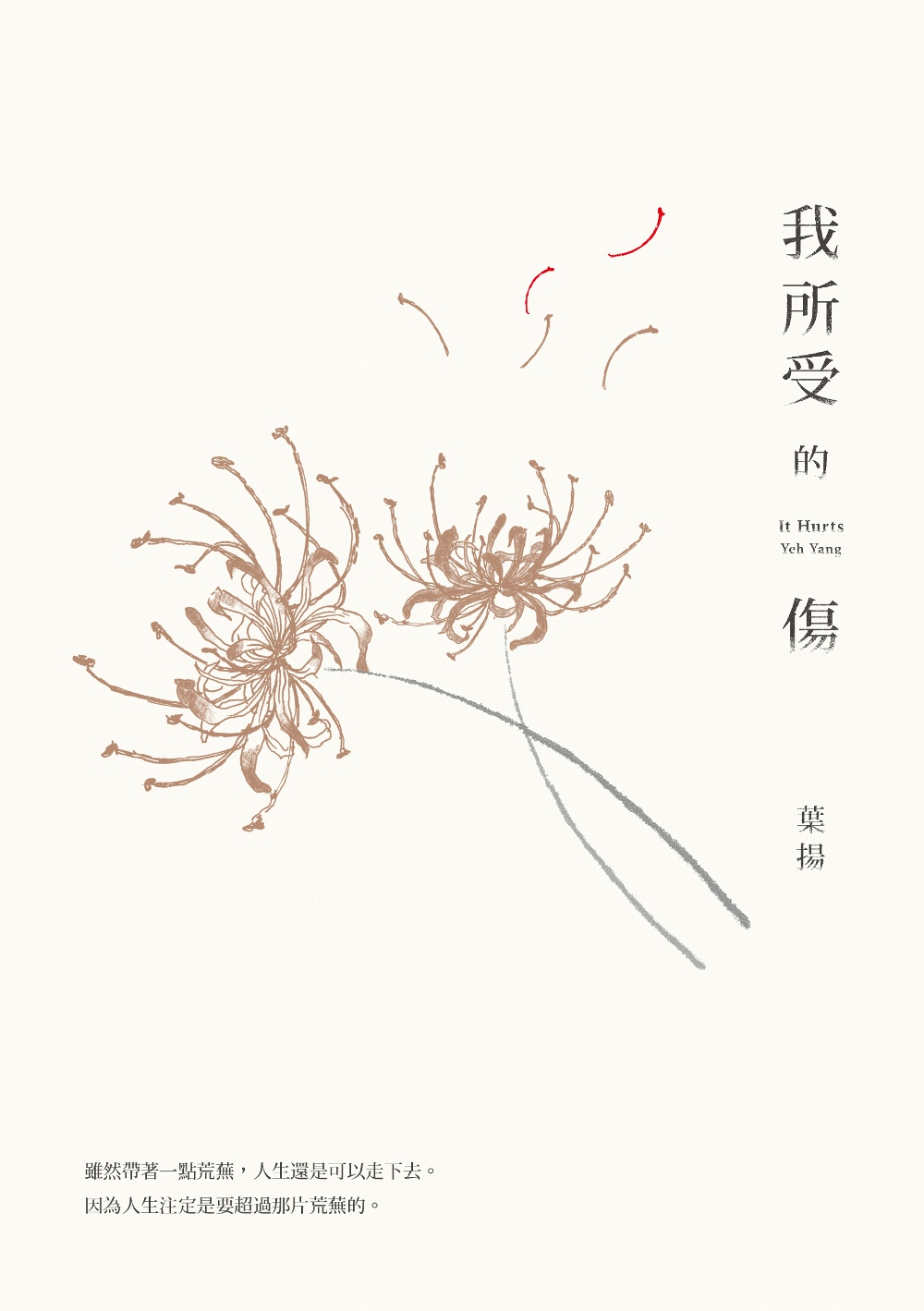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