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既是文學書譯者穆卓芸,也是科普書譯者賴盈滿,但這些都是潘信宇的筆名。有著電機系理工背景,而後轉讀哲學,現專職翻譯的他,將理科/文科雙軌思考的特質在翻譯工作上結合得淋漓盡致,這遠遠不只是「左手翻文學、右手翻科普」了,而是他用一套極理性、非常理工思維的方法來拆解文本。他說,「翻譯就像解謎,文字給你線索,每一句話都像一具屍體,但屍體不會說話,譯者就要像偵探一樣,想辦法讓它說話。」
潘信宇的比喻精準又生動。他翻譯的原則是:「原文的讀者讀到、感受到什麼,譯文的讀者就應該要讀到、感受到什麼」。翻譯畢竟是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轉換,儘管無法百分之百重現還原,譯者可以透過技術、透過觀察,來無限逼近答案。他說這也像以前數學課計算不規則田地面積時,利用「畫格子」來切割估算的方式──當格子愈小,精準度愈接近。他也強調,「這種逼近,不可能真的讓原文與譯文貼合,所以學習一套切細格子、逼近意義的『技術』就很重要。」
▌「面—線—點」的文本拆解心法
以第一本譯作《尋找松露的人》踏入書籍翻譯這一行時,潘信宇就建立一套工作方法,「每一本書都像是刑案現場,裡面的每句話都是獨立的線索,但它們又都指向一個『整體』。」
他用「面─線─點」的思維切入,並以「文化/脈絡/風格/語意」四個面向來拆解文本。「一般以為翻譯的思考順序是先把字處理完、然後處理句子,整個文章的風格就會隨之產生,這是『點─線─面』的思考。實際上,翻譯是反著處理的。」他解釋,每個詞彙都有語意的邊界,而這個邊界是由文章脈絡決定,同時受時代文化、作者表達風格影響。因此他翻譯的起手勢,不是直接進入文本埋頭字斟句酌,而是先定位出文本的『面』──即當時代的文化、作者的寫作風格,才能接著處理文章脈絡與細節。
以最近剛出版的譯作《熊與夜鶯》為例,這部奇幻小說描述的是俄羅斯尚未完全現代化、且帶著童話般神祕色彩的時期,「它有一種時代感,但是又不能太『老』。」當時他找來許多神話、童話乃至聖經的譯本來參考行文氣氛,最後以曾珍珍翻譯《納尼亞傳奇》作者C. S. 路易斯的經典神話小說《裸顏》為參照,在人物對話上,盡可能簡單白話,情節推進時,則以相對沉穩而有時代感的語氣詮釋。

▌既隱形、又現身的譯者
對潘信宇而言,這一套分析方法適用所有文本的翻譯。曾以《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10種物質改變世界》分別獲得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最高榮譽金籤獎、銀籤獎的他謙虛地說,無論是翻譯科普書或文學書,「譯者就是把譯文『創造』出來的人,只是這種創造必須本於原文。譯者把自己工作做得最好的時候,就是大家意識不到翻譯存在的時候。」
確實,有經驗的譯者懂得在譯文中隱身,既給讀者流暢的閱讀經驗,同時又讓讀者明白:這是一個被翻譯處理過的文本。這種兩面性,就是譯者隨時把持的重要平衡。
他特別提到,當西方拼音文字翻譯成中文的方塊字,許多文學性的表現往往無法直接轉譯,「比如,在英文中只需改變單詞的拼字,就能顯示出人物說話的腔調、暗示角色的背景設定,但這樣的表現在中文很難有等效翻譯。」有時,這就是譯者該現身的時候了,通常他會跟編輯討論,是否以一篇譯者序讓讀者明白在翻譯的處理中,做了哪些語言轉化上的取捨。
「我覺得譯者應該要有一套語言,去跟外界的人溝通,用淺白的方式讓讀者了解翻譯在處理什麼問題,以及這過程的價值是什麼。」潘信宇認為,「當讀者對翻譯的理解愈清楚,好的翻譯與好的譯者,就更容易存活下來。」

▌譯作就是你的名片
聊起如何踏進譯界,潘信宇說,當時從台大哲研所轉輔大譯研所畢業後,想存錢到法國旅居,儘管不那麼嚮往辦公室生活,卻也因緣際會進入電視台擔任國際新聞編譯。他說,工作雖然是外電翻譯,但其實花更多時間在新聞編輯和剪接上,還因此習得剪接技能;碰巧,當時在大塊文化擔任主編的譯研所同學(也是法文譯者尉遲秀),問他要不要翻譯《尋找松露的人》,許是譯筆不負所託,從那之後,開始有其他編輯主動找上門來。他想建議新手譯者,選擇第一本譯作時,可以從厚度上偏輕薄、有自信掌握的文本下手,「作品就是譯者的名片,第一本書最好不要『大』,但要做好。」
翻譯書從出版社簽下版權到上市,譯者只是其中一環,「以石油來比喻,譯者就是第一次精煉原油的人,但後面會變成什麼樣的產品,其實都不是我的工作。」潘信宇也建議,跟編輯從一開始就做好溝通,即可省下後端編輯過程的來回修改。他的做法是,以100頁為單位,分段交稿;遇到首次合作的編輯,先主動試譯,第一次交稿時以10頁為限,一方面校準編輯對該書譯文的期待,一方面也據此調整筆法。
那麼,翻譯科普書與文學書,最大的差異是?「文學書光是一個形容詞可能可以譯出好幾種意思,譯出來的詞,不同讀者心中的感受也可能不同,但終究譯者只能做自己的選擇,想辦法保留某種激發人想像力的『曖昧性』。」而科學的文本,則有相對明確的邊界,潘信宇說,「但這個邊界也有危險,你一旦沒準確對上,就完蛋了。」

▌翻譯必須回到「人性」本質
最後,問起人工智慧技術不斷提升翻譯精準度,未來Google translate是否將取代譯者的角色?潘信宇分享了一個故事:有個從小立志當劇作家的人,大學念了UCLA戲劇系,畢業後就按照一般路線,先到外百老匯闖盪,一邊打工端盤子。結果因為忙著打工賺房租,根本沒時間寫劇本。後來因為她的編劇背景,偶然被找去Siri開發團隊,專門教機器怎麼跟人幽默對答。她因此有足夠的錢付房租,也有時間寫自己的劇本。
「你可以選擇跟機器競爭,但你也可以跟它結盟,把它變成你的工具。」他進一步解釋,語言是不斷變化的東西,未來的創造性和可能性是我們無法預期的;機器仍持續被要求「更像人」這一點,會讓人類仍然保有被機器追趕的優勢,「所以翻譯裡面愈像人的,愈不會被取代。」
他笑著說,「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當有一天機器不再需要像人了,才是人類即將消滅的危機。」聽起來,這彷彿是《黑鏡》的近未來恐怖預言了。
未來若有機會,他想回頭挑戰社會科學類型的翻譯,比如哲普書籍。「我覺得此刻的臺灣有一種氣氛,大家開始需要這類的書來思考社會接下來該往哪邊走。」當然,他也會繼續做文學翻譯,儘管近年老聽到文學市場嚴峻,但潘信宇樂觀地說,「文學翻譯在處理的,其實是人類語言表達中最細緻的一塊,這將是人們永遠需要、也永遠不會被取代的。」

穆卓芸/賴盈滿譯作

【譯界人生】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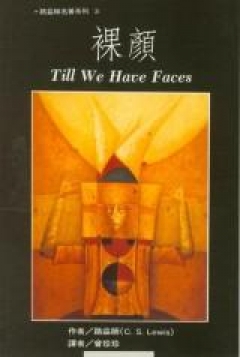 裸顏(曾珍珍譯)
裸顏(曾珍珍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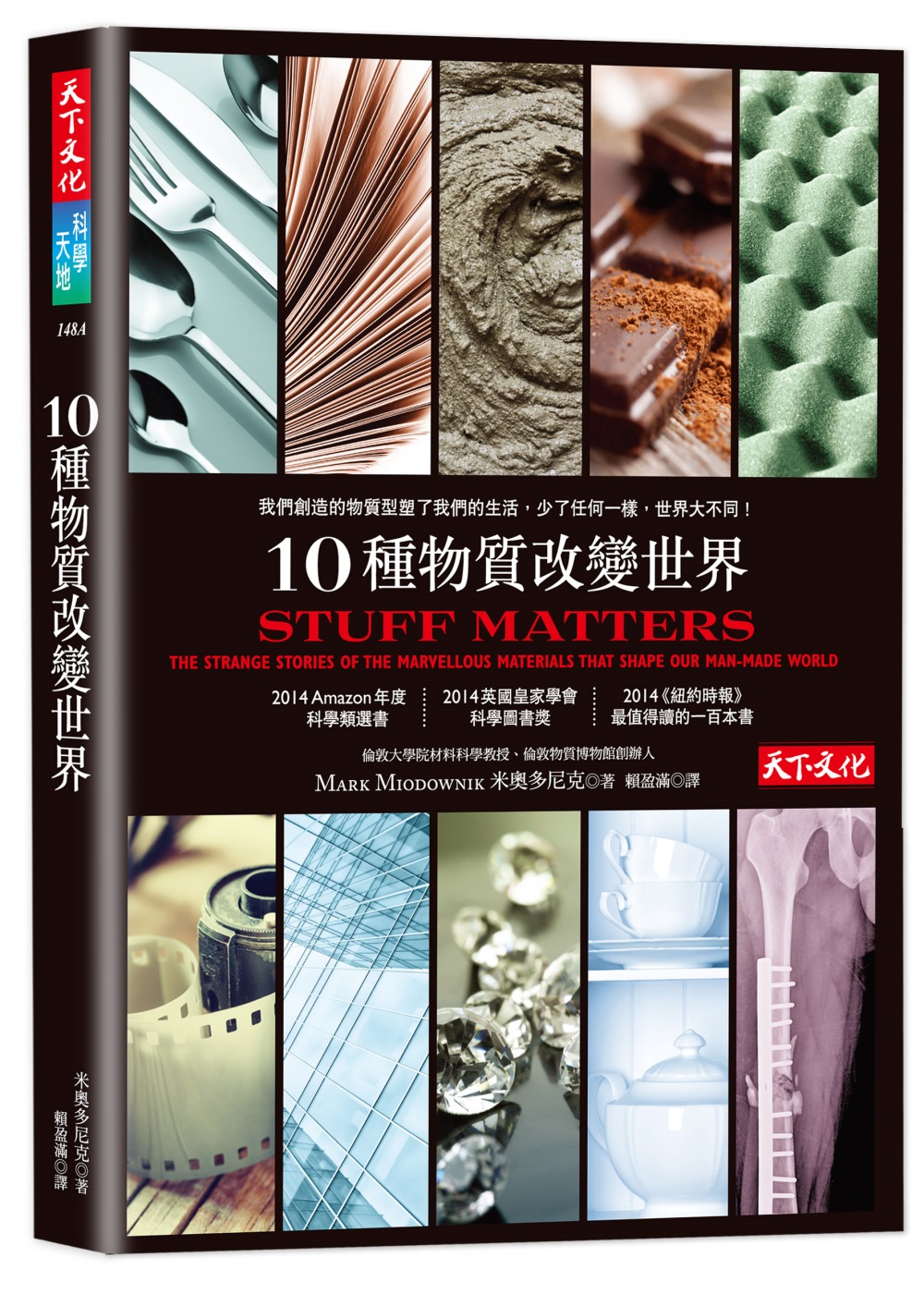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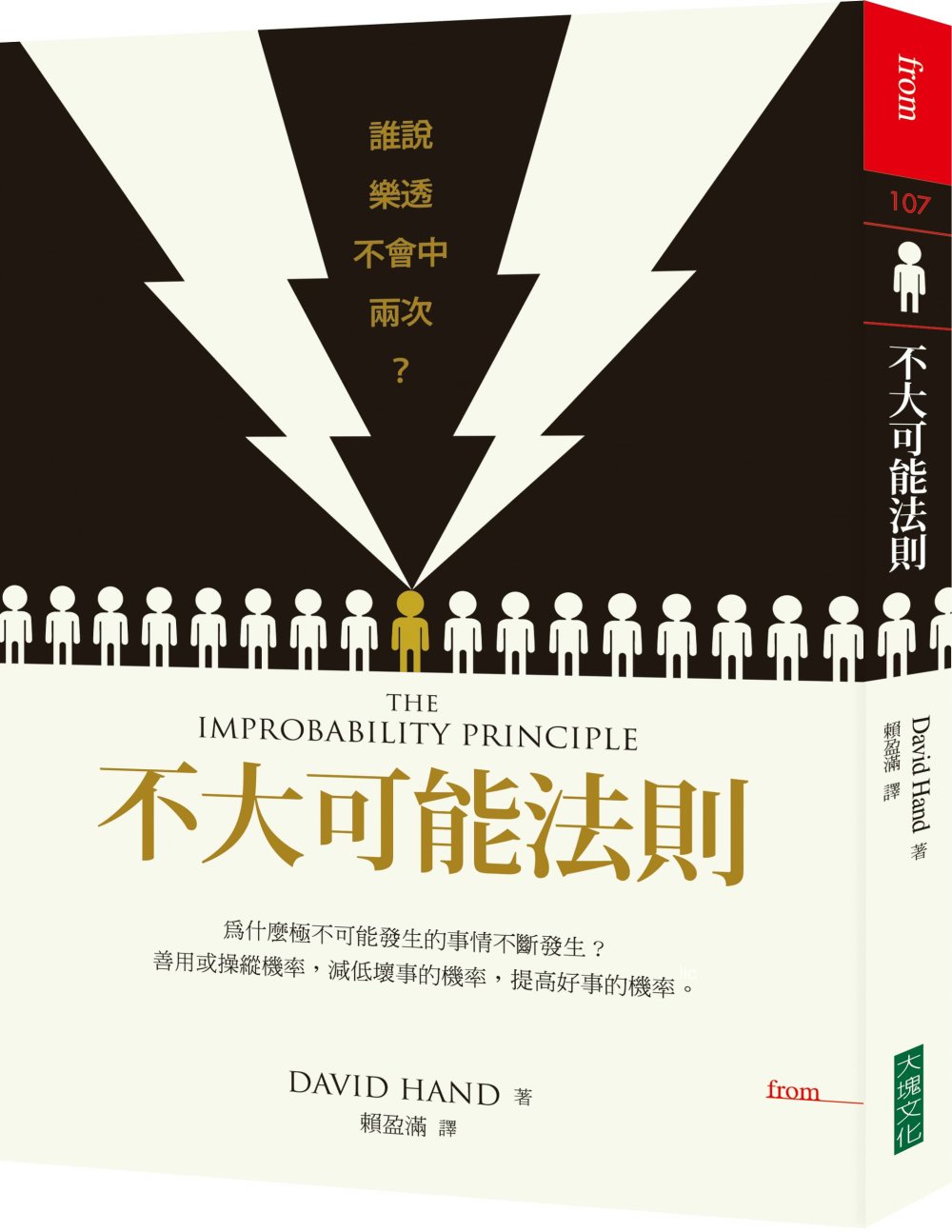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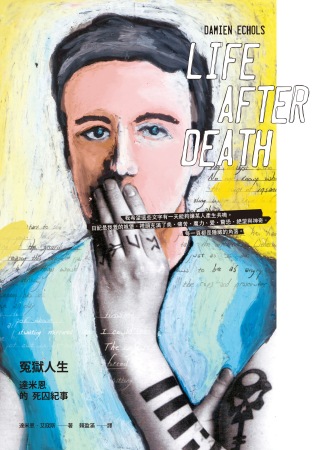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