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胡波沒死……
當《大象席地而坐》在今年金馬獎奪下最佳影片那一刻,相信許多觀眾都湧生一個念頭,假如導演胡波能親眼看見他的作品獲得肯定,那該有多好。
然而「假如胡波沒死」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如果不是胡波自戕,使電影版權回到胡波父母手裡,讓這部片以他堅持的四小時版本放映參賽,不會獲得如此熱烈的迴響;而胡波在製作《大象》時,遭到中國電影業內嚴重打壓,又讓人想起他的小說《大裂》主題,關於個人泥足於龐大體制的困境。
《大裂》收錄了《大象席地而坐》電影改編的同名小說。〈大象〉和其他短篇小說,都顯現出與電影呼應的異化與救贖命題,可說電影與小說兩種創作形式,都反映了胡波一貫的思想。電影版《大象》的橫移長鏡頭與演員極度疏離的表演方式,有導演貝拉.塔爾(Bela Tarr)荒莽末日感的敘事痕跡,而暴力前的一瞬靜滯和某些詩意畫面,又有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與塔可夫斯基(Adreji Tarkovsky)等電影大師的影子。胡波的影像風格,在小說裡轉譯成一副瘦瘠骨骼,剔除了所有華美修辭,只餘下簡單的陳述與對話,架構起一個殘酷世界。
書中多篇小說都由事件「中途」寫起,像是一刀將青椒剖半,裸露出布滿迂繞褶襞的內部結構,而小說主角多半身陷荒謬情境,只知來時的路途,卻無法洞悉命運的整體布局,對未來充滿無力感。他們無法忍受重複毫無意義的套例,虛矯從眾的陳詞,卻又無法掙脫條規的束縛,於是轉而厭憎自我。
儘管如此,在通篇陰鬱裡仍有少數美好事物熠熠發光,如〈漫長地閉眼〉裡女子的溫柔話語,〈氣槍〉中小女孩宛如皓石的鼻子。然而美好總會蒙塵汙損,因而胡波筆下的女子不是死亡,就是遭受暴力與屈辱,無法救贖受創男性的女性,成了宣洩憤怒的出口。〈漫長地閉眼〉主角代胡波說:「……人們為了不讓自己發現這些自身的真相,會竭盡所能的傷害他人。」在胡波的小說世界,傷害如傳染病般在人與人之間蔓延,沒有心靈能免於這場瘟疫。
胡波擅長描繪人類在現代化社會安於角色鑄模,無法溝通的孤立,但他將精神危機放在國家歷史脈絡中檢視,也隱約觸及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生長出的畸怪現象。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積累成形的中產階級,生活無虞,卻無能改變周遭環境現狀,精神無所依托,如死水靜滯生腐。書中最能體現這點的是短篇小說〈氣槍〉。〈氣槍〉寫兩名男子為了追求刺激,到鄉村狩獵,其中一名男子誤殺了一個女孩,檢查女孩的冰冷身體,發現被性侵的跡象,因而意圖找出兇手。故事峰迴路轉至斷崖急煞,男子意識到,若要替女孩討回公道,他要對抗的不是個別兇手,而是整個中國農村毫無道德底線的貧窮,於是他退卻了,讓同伴將他載回城市。中國書寫留守兒童的文學作品不少,〈氣槍〉的獨特之處在於袒露中產階級目擊事實的驚怖:原來在同一個國家,有種生命低賤至不可思議,無論在她們身上犯任何罪,都可以轉化為廉價交易。為了逃避這沉重的事實,視而不見是最好的方式,即便一開始因接觸真實而感到痛楚,久了總會找個舒服的姿勢,學習適應這世界,賴活下去。
胡波知道如何適應不義,卻無法習慣。他在與本書同名的中篇小說〈大裂〉,將一群年輕人投放至一間野雞學校,這群新生遭到學校改制前的「老廣院」(原廣播學院)學長群毆濺血後,發現自己無法習慣無所不在的羞辱與斲傷,動手在學校挖掘地坑,夢想能找到黃金,結果意外尋獲大量迷幻藥。於是一部分新生倚賴迷幻藥逃避現實,一部分人計畫伺機報仇,終於與「老廣院」在校園廣場血戰至兩敗俱傷,國族歷史暴力輪迴的隱喻呼之欲出。
〈大裂〉中一名酷似塔可夫斯基電影角色的神祕預言者說:「兩百年是文明的區別,一百年是國家的區別,幾十年是家族與個體的區別。層,就是這麼形成的。」透露出胡波對於中國社會型態僵固的憂忡,可以看出相較於其他中國年輕創作者,他擁有更宏大的視野和企圖心。胡波將自己對世界與國家的觀照,凝縮成小說裡夢魘般的反烏托邦校園,人與人的關係絞纏成互相毀滅的生物鏈,一切美好敗壞殆盡,土地只能張開裂罅吞噬人性,無法滋養出任何希望。
在四顧茫然的虛空裡,〈大裂〉的敘事者「我」最後伸開雙臂,模仿記憶中的舞蹈跳了起來。在此,胡波視舞蹈為藝術與創作的隱喻,彷彿肯定了藝術的價值,找到了耽溺與傷害以外的生存方式。如此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胡波為何在艱難情勢下,仍決意完成電影處女作,並且堅持不修剪四個小時的版本。觀眾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其實也以肉身參與了電影文本,歷經了四小時的漫長折磨。當他們站起身,動動發麻的腳,會發現自己能理解,片中受傷的眾人為何會在長久絕望後,企圖前往滿州里,只為了尋覓席地而坐的大象,另一頭靜默受傷的生靈。縱使小說版本的大象起身後,抬腿踩向主角,一如對電影工業的幻滅重重傷害了胡波,他到底清醒到了最後。他知道,他不習慣這世界。
而活下來的我們,遲早都會習慣所有的醜惡。
假如胡波沒死……然而創作出這樣電影與文字的胡波,或許無法賴活下去。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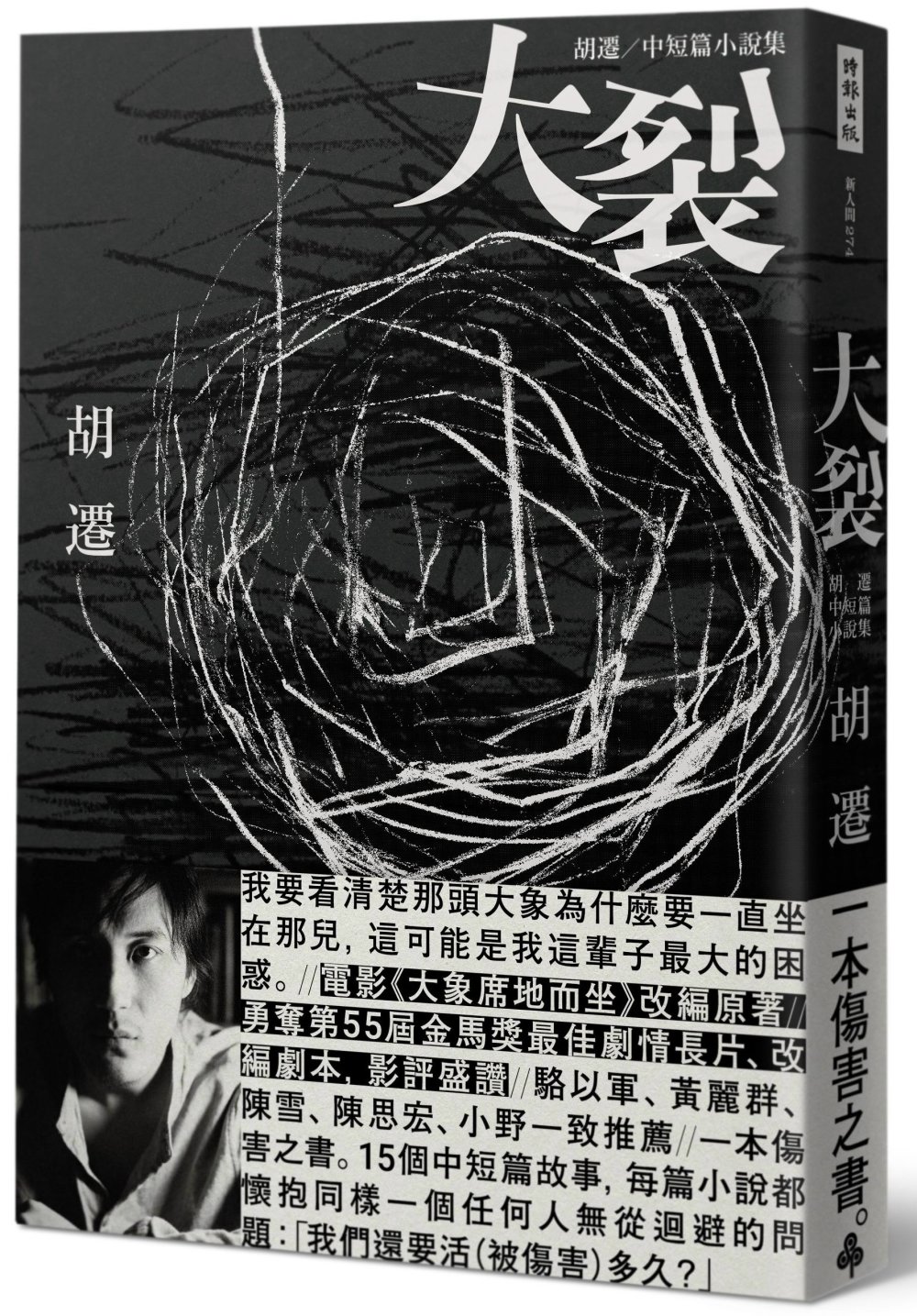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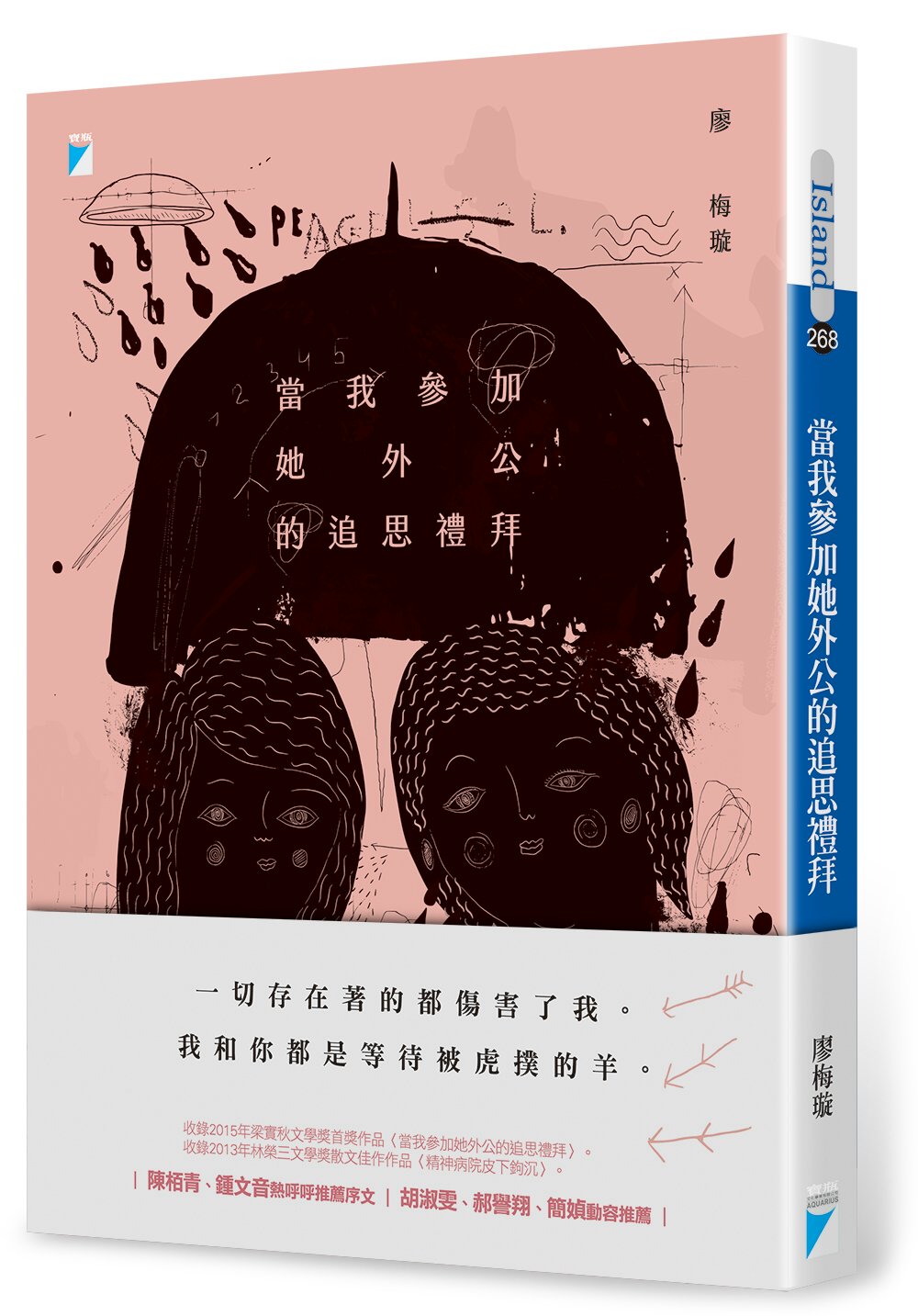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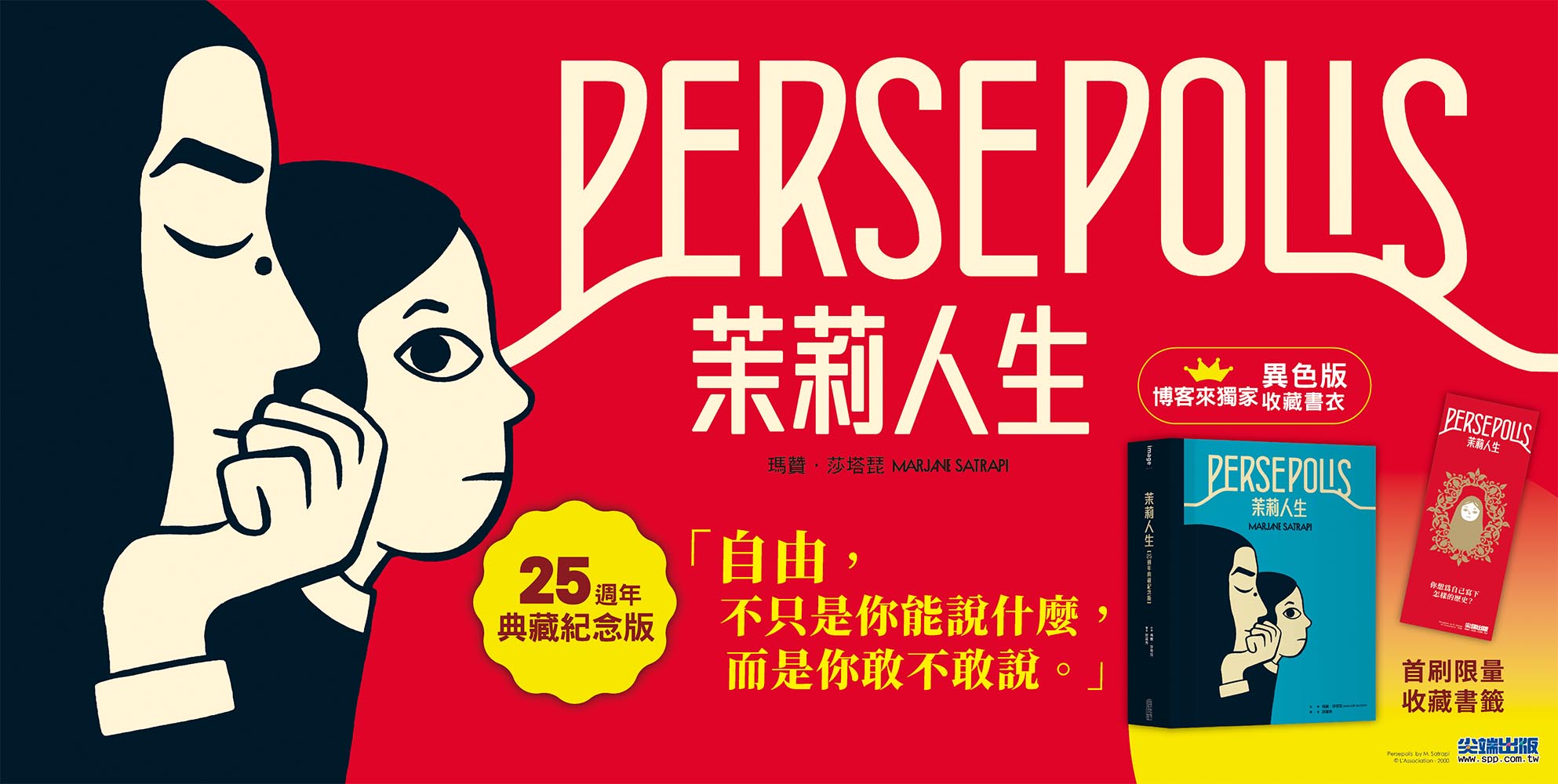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