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裡有一段金宇澄對父親晚年的描述,大意是母親發現,父親不小心把預備拿來炒菜的豌豆苗當垃圾丟了,卻留著枝梗,母親只好也扔了枝梗,很平凡的一段插曲,卻讓人想起從二戰過渡到共黨政權時期那一輩中國人。大量脆嫩的青春,被拋擲進兵荒馬亂的戰火,倘若沒化為灰燼,餘下人生便在一次次清洗運動中折舊疲敝,最後被掃進故紙堆。
金宇澄父親於1937年對日戰爭爆發之際,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成為情報員,熬過牢獄之災,卻在1955年被認定當年有「叛變」之嫌,遭到隔離審查,政治汙點如附骨之疽跟著他,文革中專職清掃廁所。他不曾料到在日本宣布投降當晚,與友人闖入人去樓空的漢奸豪宅,舉杯慶祝,已是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後半生他只能重複撈取記憶裡的漫漶話語,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身為人子,作者原不認得這位愛國青年。人一生最大的謎題,就是父母在我們誕生前的人生,畢竟父母構成了最初的山水,是一切萌芽生發的背景,已經凝結成定局。我們很難想像父母也曾經年少,曾經眼前攤著一整個人生,擁有無限的可能。他們究竟怎麼沿途不斷抉擇,一步步走窄了路,來到兩個人邂逅的時刻,相識,戀愛,結婚,誕育新生命,孩子是不會懂這些的。加之金宇澄父親是諜報人員,更絕口不提過往,乃致於少年金宇澄在文革時天真地問父親,當年父親怎麼不當工人?當了工人,家裡算是無產階級,就不會被多次抄檢,讓準備出門掃廁所的父親啞了口。
 金宇澄的父親(28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20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學生)在太湖的合照,1947年4月7日。(圖 / 新經典文化提供)
金宇澄的父親(28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20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學生)在太湖的合照,1947年4月7日。(圖 / 新經典文化提供)
唯有泅泳過時光,經歷過汙穢與美麗,兒子才逐漸意識到對父母的大哉問,回過頭認識父母之前的模樣,從鬆皺皮囊釋放少年精魂,退回生長的故土,父母從長期布景蛻化為人,浮現自身襯裡,一整個逝去的時代冉冉升起。人類的歷史原本即留存在世代相隔的層巒疊嶂,只有跨越時間壁壘,回顧哪些過往沉澱下來,哪些不可逆地毀壞,我們才知道不知不覺間,眾人的雜沓腳步,如何選擇了當下方向。
因而金宇澄在《回望》寫的不只是父母,而是那一輩人與他們活過的時代。他將關於父親的憶往篇章命名為〈黎里.維德.黎里〉,母親的生平是〈上海.雲.上海〉,兩個原鄉包夾著這對男女青春歲月的變迭。出身水鄉黎里(近江蘇吳江)的父親,因著小鎮被日軍占領後,目睹被送去慰安所的尼姑嚎泣,參加中共地下組織,化名程維德。
書中穿插父親大量筆記,與老友的通信,以及在審案時上繳的申訴報告,從各方面還原當時事蹟。由於情報組織只向上負責,沒有橫向溝通,牽涉其中的人只知片面事實,真相都是事後由諸多線索織綴出大概樣貌,然而從文字仍可以看出青年維德的性格輪廓。他擊斃過漢奸,一身硬骨挺過牢獄酷刑,卻不是典型抗逆封建家庭的共黨「進步青年」。在兒子筆下,他對長輩恭謹有禮,案頭列寧文集與廿四史並列,寫舊體詩,分明是個溫和的小鎮知識分子,不甘只用筆墨愛國,更提槍上陣捍衛理想,卻在他有份參與創造的新社會獲罪,活成了巨大的反諷。
 金宇澄父親於獄中寄出的信件、明信片。(圖 / 新經典文化提供)
金宇澄父親於獄中寄出的信件、明信片。(圖 / 新經典文化提供)
晚年父親攜兒孫回黎里,見河運衰頹,昔時行船如織的故鄉寂寞如煙霞,他又從維德回復金家子孫身分,以書寫重構記憶中的黎里:「水鄉的早晨,先從水上降臨,東方發白了,雞鳴四起,迷霧漸失,一個金燦燦大鎮,從水面上升起來。」這種搖槳攪動的語言韻律,也迴盪在金宇澄散文集《我們並不知道》的〈此河舊影〉一文中。父與子,都眷戀著淌過命運的那條河。
只是金宇澄所寫的蘇州河,畢竟不在黎里,他執迷的廠房、工人、鐵路等都會風景,來自他所生長的上海,傳承自母系家族。〈上海.雲.上海〉是母親第一人稱的口述回憶錄。出身銀樓的母親自小被當男孩養,有過三個名字,姚志新寄託了舊時代對男嗣的渴望,姚美珍是進了現代學校改的,她叫自己姚雲。少女姚雲在學校深受左翼思想影響,爾後認識作者父親,始終喚他的化名維德,這些名字透露出激情年代社會思潮的風雲變幻。雲講述到婚後生活,從對新社會充滿期望,漸漸以各種政治口號與運動做為斷代依據,銀樓千金因著丈夫被捕,學會撐起一個家,在一波波自我改造運動中輾轉於農村與工廠,私家產業逐漸被收歸公有。
身為衣食無虞的資產階級小姐,又是復旦大學生,母親卻能堅韌面對動盪中的艱辛境況。金宇澄問過母親,為何不曾想過賣掉父母給她的嫁妝細軟?母親驚道,「這怎麼可以?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金宇澄父母的性格其實極為相似,兩人一方面懷抱著改造社會的期盼,一方面卻也堅守某些傳承的價值,未曾遺忘,或許因此也造就了金宇澄善於從舊物洞見光陰遞嬗的寫作特色。他像翻修舊家具般,細細掃去塵埃,刨光、髹漆、陰乾,讓老人與亡者體內藏匿的雲與維德,微笑跨步向前,站了出來。
一個作家一生想寫的,興許都是同一件事。金宇澄在《我們並不知道》寫上海弄堂,寫文革時下鄉東北的見聞,改革經濟初期大批出售的舊鐘錶古董、製鞋匠、鍛鐵匠、國營工廠,都是消逝的事物,瀕死的技藝。他以精準修辭澆鑄一地一物,抵擋時間的滲蝕,頑強挽繫住他的時代,文革期間飄搖的花樣年華。在《回望》裡,他更進一步回溯父母那個時代,那樣多像他父母一樣被浪費的生命,並不只是時間的悲劇,彼時也曾有無限的歧路,卻被眾人踐踏至窮途。
人是歷史的遺民,總是從你所來的地方,開始度過餘生,一如你的父親母親。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 【書評】李桐豪:一聲不響,譬如梁朝偉──讀金宇澄《我們並不知道》
- 【書評】葉佳怡:一場由難民組成的鬼魅遊行──讀阮越清《流亡者》
- 【書評】在北疆,生存得赤手空拳對天去要──江鵝讀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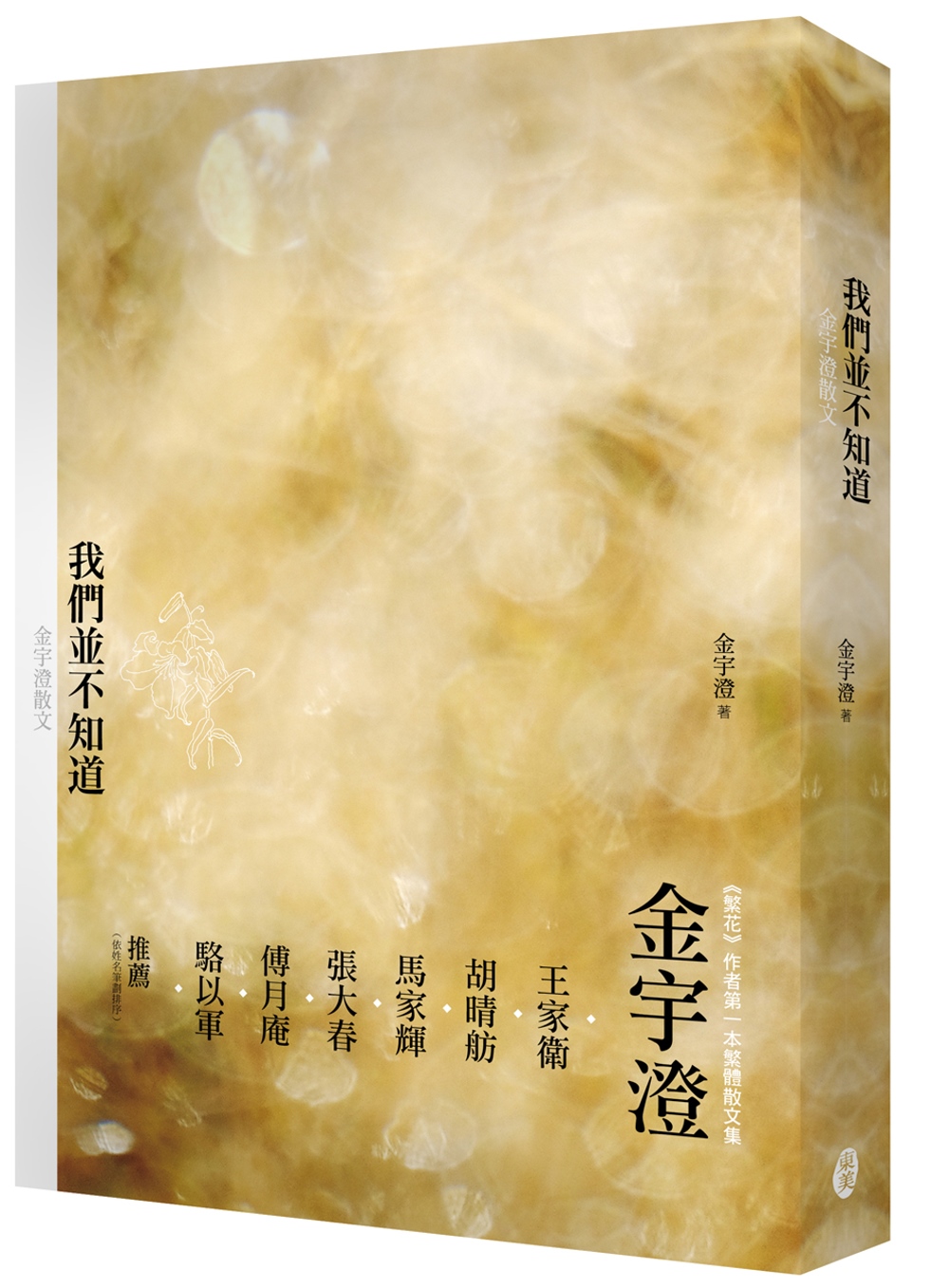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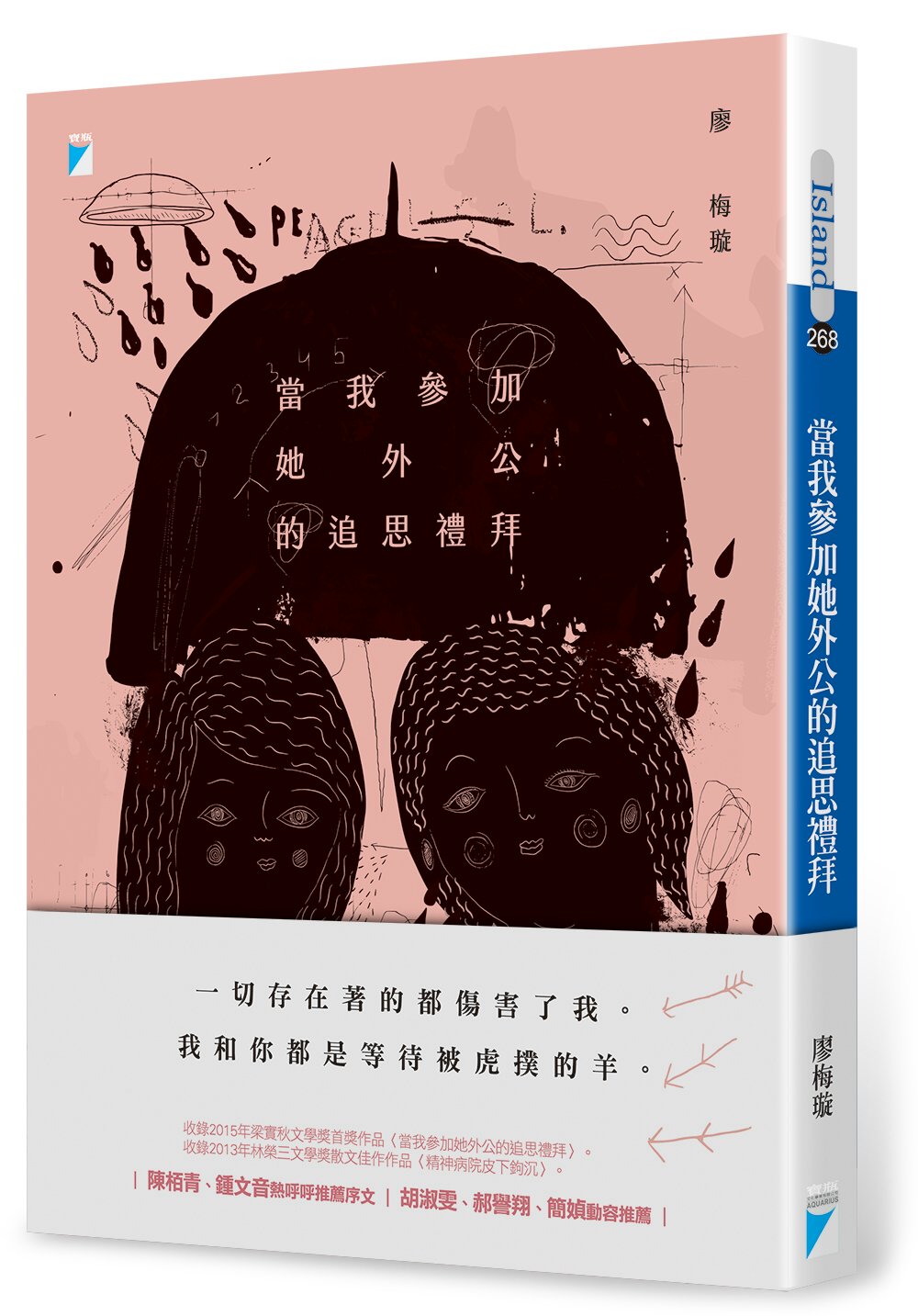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