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白先勇短篇小說集《台北人》中,〈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的眾多同性戀人物跟《孽子》諸君一樣,以台北新公園(現二二八和平公園)為發妖總部,年輕人賣弄風騷,中老年同志在旁叫好。在〈滿〉中,這批不吝展示青春肉體美感的年輕人自稱隸屬「祭春教」,他們敬稱一位本來在中國當過導演後來移住台北的老人為「教主」。
祭春教,這個名字有意思。「春」可解做「春情,發春」,但也可解為「青春」。這兩個不同意涵對應了文中兩種角色。文中美少年們忙著抒發前者,而老教主追逐後者,並終究為了追求美少年付出慘痛代價。
一般認為追求青春是人的天性(君不見醫療美容越發流行),為了追求青春而付出代價也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甚至看多了醫美失敗案例還幸災樂禍)。而正因為所費不貲的青春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我們不但寬容它還寬容它的失敗,它成為最方便的同性戀掩護裝置:有心人大可以「以追求青春之名,行追求同性之實」。青春代理了同性戀。〈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的老教主,固然可以說是因為同性戀而成為犧牲品,想要避談同性戀的讀者卻也可以盡量迴避故事中的同性戀成分而逕稱老教主只是祭春教的祭品。
我將台灣同志文學中愛慕青春的傾向稱為「青春崇拜」。誠然,在文學內外,在各種戀內外,青春崇拜都很常見。但青春崇拜在同志文學中特別彰顯,以至於不少同志文學都散發出青春期或後青春期的氣息,其中不乏乳臭未乾味。絕大多數的同志文本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年輕人角色(這個角色倒未必是同志),但各種其他文學並未如此仰賴年輕人角色。我認為同志文學依賴青春崇拜,是因為青春崇拜開啟同志想像的空間。
「到底是在寫青春美,還是在寫同性戀?」這種曖昧的態度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主要特色之一。心急的讀者可能巴不得小說家不要搞曖昧,不要用青春之名掩護同性戀之實。然而,慾望──不管是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偏偏就是不要攤牌,偏偏就是要在曖昧的情境中苟且偷生才有情趣。不然,為什麼戀人們偏愛夜晚,月光,以及燈光調暗的情趣賓館?
白先勇的少作〈月夢〉,收在《寂寞的十七歲》中,寫月色下的老醫生搶救垂死的美少年。這一篇的重點與其說是它單薄的情節,不如說是它絕美的情境。青春跟「紅顏薄命」「紅顏已老」等意涵是切割不開的,都成為同性戀這份禮物的包裝紙。在《孽子》中,離開原生家庭(親生父母的家庭)的少年同性戀者走到新公園尋找另一種家的感覺。他們這些少年被稱為「青春鳥」(這個稱號的性暗示昭然若揭);老攝影師還「古道熱腸」邀少年到他的攝影棚留影紀念,並將他的收集的照片稱為「青春鳥集」。老攝影師自稱只是要留下每個男孩的青春模樣,但是他的視線究竟成全了他本人的青春崇拜,還是同性戀意淫?我看,應該又是以青春崇拜之名行同性戀意淫之實。這種意淫的快樂,可能尤勝真槍實彈跟少年們上床過夜。
假青春崇拜之名行同性戀之實,就是經典名片《魂斷威尼斯》讓人津津樂道的主因。其實《魂斷威尼斯》並沒有呈現我們今日熟知的同志情慾行動,但片中老年藝術家對於美少年的癡情凝視,一方面明示了青春崇拜,另一方面暗示了同性情愫。我在OKAPI提過,在楊牧提及同性戀的散文中,詩人特別討論了《魂》中藝術家對於美的追戀──因為崇拜青春美在藝術的國度中是理直氣壯的,所以青春美挾帶的同性戀眼神也就可以得到諒解。〈童女之舞〉也提及了《魂斷威尼斯》;按我的詮釋,《魂斷威尼斯》的青春崇拜邏輯「代替〈童女〉說出〈童女〉沒有明言的訊息」:小說中主人翁童姓少女坦承她仰慕鍾姓少女活蹦亂跳的青春模樣,卻不必明說童「剛好」愛慕了同性。
青春崇拜可以偷渡同性戀慾望,所以在同志文學中特別重要。許多並沒有明顯提及同性戀的文學作品也因為展現了青春崇拜,因而讓人聯想同性戀。但我要說明,青春崇拜並不是萬能醬油,把醬油撒在任何食物上就可以讓任何食物變出醬油味──我的意思是,青春崇拜並不會讓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一概變成「同志文學」。硬要把多種文學作品都拉進同志文學的國度,只是徒然自我感覺良好的苦功,未必值得。比較平實的讀法,是承認青春崇拜為文學作品披上的神祕面紗──我們永遠不確知某些文學作品是否屬於同志文學,但它們的青春崇拜讓人聯想同志。曖昧的聯想總是比確切的分類貼標籤來得有情趣,來得貼近慾望。戀愛和讀同志文學都是這樣一回事。
行文至此,我都在強調青春與美(易逝的美)的聯結。追求同性戀的人可以託稱是在追求青春,也就是在追求美。但我想指出,青春的意義是多元的,並非僅止於美。青春的另一個重要意涵是它標示出了一群年少輕狂者。他們跟芸芸眾生不同;他們可以冒險。著眼於青春的這種意涵,青春美就不是重點,他們不必長得美,長得醜也沒關係。因為年輕,所以他們有燃燒青春嘗試各種戀的冒險(含同性戀)。在〈童女之舞〉中的鍾姓女孩像男孩一樣帥氣,像是女同志中的T,但她偏要跟男人上床還懷了孕。所以鍾的青春至少有兩種意涵:一方面,因為她青春「所以美」,貪看她的女同學在眼神中埋藏了同性愛;另一方面,因為她青春「所以可以大膽越界」,也玩過異性戀的遊戲。
青春的孩子享有芸芸眾生所無法企及的曖昧空間:眼看身陷慾望洪流的他們就要漂向同性戀了,他們卻又好像可以若無其事地漂走。朱天心膾炙人口的「女同志小說」《擊壤歌》和〈浪淘沙〉(收錄在《在方舟上的日子》)就是經典範例:要說文本中的女女情誼是女同性戀,只是讓有心的同志讀者覺得搔不到癢處;要說她們不是女同性戀,卻又讓有心人覺得不捨。與其說讀這兩種文本的感覺「很雞肋」,不如說這兩種文本展現了青春少女的曖昧空間:說她們「一定是」或「一定不是」同性戀,就等於簡化了她們和她們所處的文本;承認她們的曖昧,並且認清同性戀就是在曖昧空間中得以斡旋(maneuver),才是培養同性戀「菌種」的長久之計。
因為青春男女通常被認為是不成熟的、還未發育完全的、還沒確定傾向的,可能還拒絕長大,於是他們早就成為各界成年人士所要攻占的市場。有些人說要保護青少年而不讓他們接觸任何情色資訊,有些人則特別指明要讓青少年跟「同志的」情慾教育保持距離;但也有人鼓吹讓青少年早日接觸各種性知識(含同志的),也有人希望同性戀青少年「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這些立場是針鋒相對的,但它們卻也有共通之處:將青少年視為可貴的資產,所以要保護,或要教導,或不能輸。但,青少年在社會現況中的價值和他們在文學中的價值是完全兩回事:在社會,每個青少年都是個寶;在文學中,青少年的可貴卻在於他們的輕賤。
青春而美卻死,青春而任性而死,在文學中範例多,都顯示他們輕賤易死。如果不死,他們也是輕賤可以褻弄,不怕他們虧了腎水。在朱天文的〈肉身菩薩〉中,故事主線是兩名輕熟男同志(小佟與鍾霖)的互動,副線是小佟在少年時期與鄰家大哥的性啟蒙。在少年時期,主人翁和鄰家大哥與其說互相珍惜,不如說輕賤了彼此的青春。但我更想提出這篇小說在主線副線之外的另一條年少輕狂軼事:小佟曾在電影午夜場之後被兩個16、17歲的少男勾搭,唱了卡拉OK之後小佟帶兩少年回家鬼混了24小時以上(睡覺之外做了很多無聊事)。小佟在戶外猛吻了17歲,並在家裡跟16歲做愛。「十六歲拉他壓倒,跟他要,他就給,清清醒醒給,也愉樂,也寂寞。」這三人一起浪費了兩種世代的生命,正因為青春如此廉價,浪費也不心痛,而這種廉價感正是青春讓人崇拜之處。
朱天文似乎愛寫青春同志的可貴暨可賤。在《荒人手記》第八章,主人翁熟男小韶也被一個「底迪」勾搭上了,他叫對方「費多」(Fido Dido,1990年代初的流行動畫人物),對方叫他「PAPA」(爸爸)。PAPA去費多家,看費多做一堆無聊事,而他本人聯想起《魂斷威尼斯》:費多是美少年,而他自己是老藝術家。這一回,熟男不做愛。
這篇文章稱為「青春崇拜」而非「青春」,是因為我並非只想點出青春的一方展現了哪些特質,而是要指出「被看的青春者」和「觀看者」之間的關係。在〈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少男們代表青春(而非青春崇拜),教主才是青春崇拜者。在《魂斷威尼斯》中,美少年代表青春(而非青春崇拜),而青春崇拜發生在老藝術家看美少年的視線之中。同性戀並非伺存在美少年或老藝術家身上,而是依附在崇拜青春的視線上。在崇拜青春的觀者眼中,青春是美的,是易死的,是任性的,是四處漂流的,是金錢得以租借但難以買下來的,是輕賤無聊的。青春的意涵多元,方便文本在青春的名號之下偷雞摸狗,進行慾望大風吹。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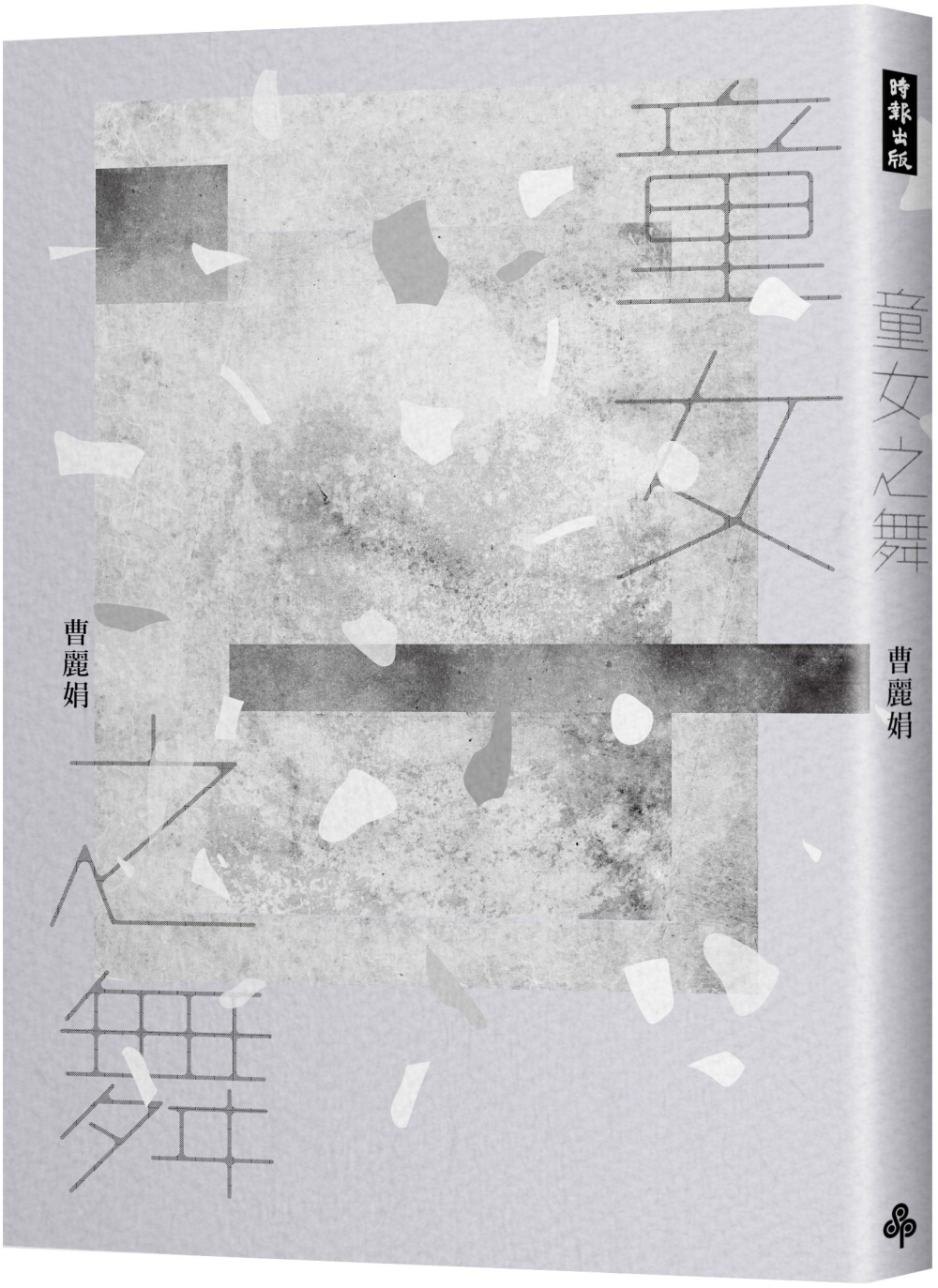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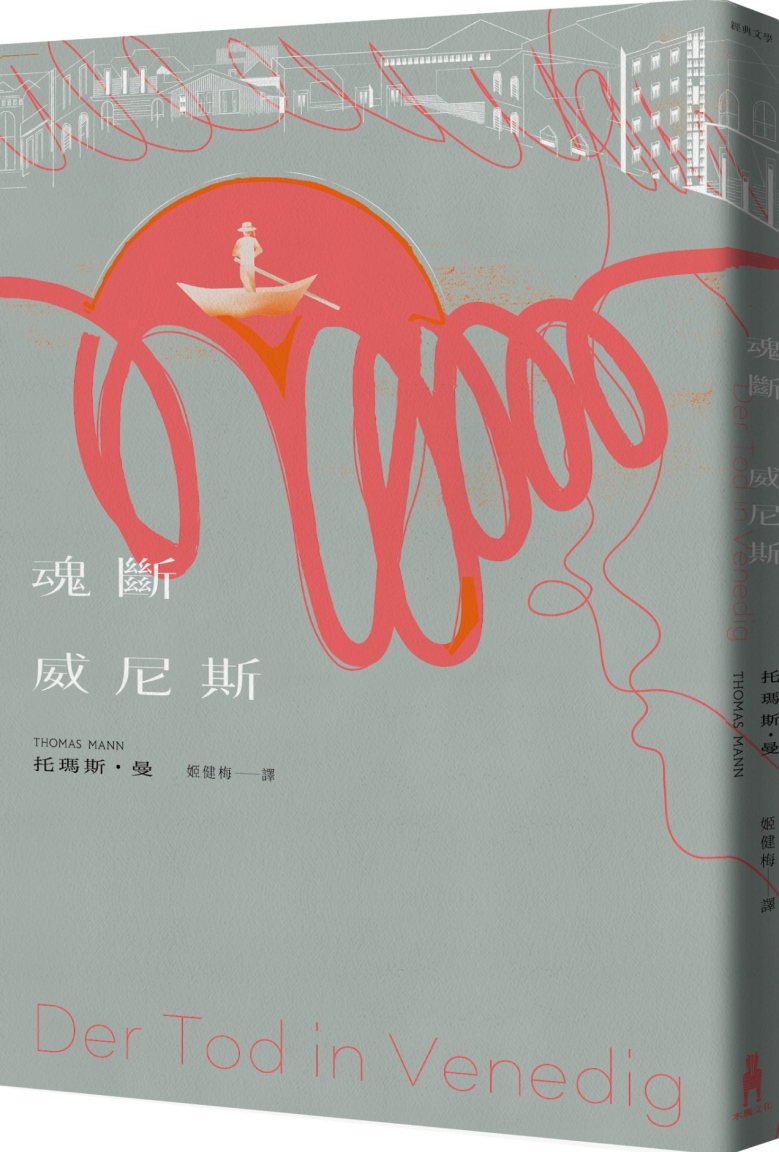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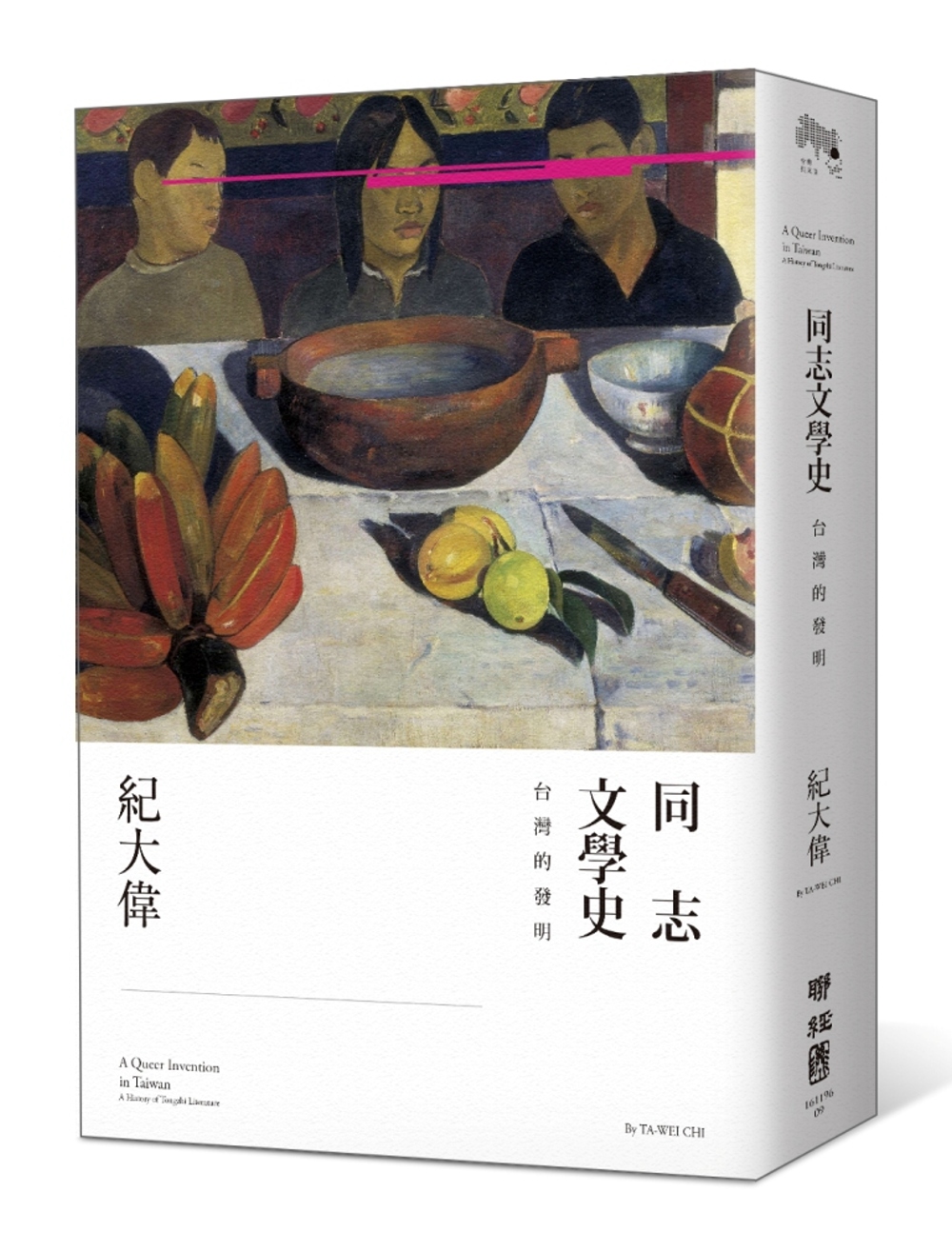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