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誰在玩躲貓貓啊?」遠處彷彿有人的聲音,然而只聽到水滴答滴答地響著,我們每個都躲得好好的,擔心著這社會的老大哥以規訓的姿態找到我們,但如果有其中一個不想再躲了怎麼辦?我們要怎麼「進化」到跟這社會同手同腳的巨人一樣龐大?在為了達成平庸而提供教育的這世界裡,如果自己的特別之處無法遮掩,我們要怎麼回應這來勢洶洶的平庸浪潮?
「誰在玩躲貓貓啊?」遠處彷彿有人的聲音,然而只聽到水滴答滴答地響著,我們每個都躲得好好的,擔心著這社會的老大哥以規訓的姿態找到我們,但如果有其中一個不想再躲了怎麼辦?我們要怎麼「進化」到跟這社會同手同腳的巨人一樣龐大?在為了達成平庸而提供教育的這世界裡,如果自己的特別之處無法遮掩,我們要怎麼回應這來勢洶洶的平庸浪潮?
平庸的本質在互相看守,久了就會形成一種激烈的潛暴力,進而催生出更平庸的體制與社會。這是我們的現實,我們失去了緩慢,無法停下來思考,而渴望進化的「凱文」遂成為我們背後要追上來的猛獸。究竟分裂的是病歷上的個人,還是我們集體有了分裂的渴望?
平庸時代,最明顯的生存問題之一是:你要當個表演者還是思考者?又是一個To Be or Not To Be?
失去腹地的主人格,凱西即將告別的身影
人有時是會破碎的,碎開來的哪一片會最閃亮?
我是凱西,被綁的肉票之一,今早醒來發現內在的另一個我彷彿在凱文的屋體裡分裂著,那裡像個人肉叢林,好似是個沒有盡頭的增生空間。
這時空,管線、金屬與彷彿無止盡的肉色產道,都在我們的潛意識裡蜿蜒不已,而我們又將變成什麼?我是否也跟著分裂在凱文的世界裡?這是我被援救出來後最常想的問題,看到凱文第24 個人格「野獸」已發展出來時,我確知了自己也有分裂的可能性,因回到原本受暴的家裡時,我已不是原來那個「凱西」了,那個以為自己可以活著「隱形」的凱西。
一開始被綁時,我跟另外兩個女同學一樣恐懼,她們見我較不慌張時,罵我說:「妳難道不能偶爾跟我們一樣?」她們不知道,這是沒有選擇的,因另一個旁觀的我跑出來了,像以往一樣俯視著我的險境,彷彿她在冷冷觀察我叔叔那性侵禽獸哪裡有弱點的眼神,她是個獵人,跟我爸爸叮囑的一樣:「先觀察好獵物的動靜。」
那股冷,足以燒出生命的炭火,必須抽離自己太痛苦的當下啊。
我是凱西,至少目前還是,被凱文俘虜的其中一名學生,但我對這情況並不陌生,而凱文這「身體場域」則是我從小所熟悉的,是一個長期處於警戒狀態的內心基地。
你知道一個人如果長期太過恐懼時,內在是什麼風景嗎?那就像從石縫中開出一不成形的黏著肉胎,粉紅爛泥般地氈著地板上、內在那被擊潰之地如陷流沙,細沙中卻還能混水綻放出氣味濃烈的花,每盛開一點就皮開肉綻的痛楚,接著你看到從心開了一個刀口子能流出另一個又一個的人格,啪搭啪搭地生出來,但他們每個也不會哭嚎,因為從小就學會張望,在黑暗裡才安心偷笑,一見到燈亮就縮回去顫抖,你跟你,還有內在另幾個你,彼此是敵對也是夥伴。
即使不在被綁架的這非常時刻,平日的我也像置身在叢林裡,我是個明顯的獵物,無論面對領養我的叔叔的戀童性癖好,還是其他同學中,無法不斷自曝的我,也無法有那些過多情緒的曝曬,或快速的表態、無法讓人知道我是哪一族群,我沒有屬於可將日常當表演舞台的鮮明特質,重點是我也沒有那類表演者的輕快,那必須維持孩童時代沒有負擔的惡意,只有在被過度保護下,長大後才能保有的那種孩童才被允許的、一切都沒什麼大不了的輕快惡意。
 即使不在被綁架的這非常時刻,平日的我也像置身在叢林裡,我是個明顯的獵物
即使不在被綁架的這非常時刻,平日的我也像置身在叢林裡,我是個明顯的獵物
就像我同學那天聚餐看著我,跟她父親說:「總不能整個社團只有不請她吧,我又不是怪物。」有些平庸具攻擊性,會為自保而習慣演出,務求活在角色裡。
平庸在自曝年代也將開始質變,但那並非來自於資質平庸,而是人們開始誇張地展現平庸,來藉此被保障奠基於平庸上的「特別」。
在哲學家傅柯曾指明的監看世界中,每個人的演出性將會是被鼓勵的,事實上,我們正從詩人李歐納‧柯恩隱喻的「動物園的憂鬱*」,正走進一個馬戲團的世界,在被確認馴化後,人們會做該動物能做最極致的演出,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
而我沒有角色可以躲藏,我始終缺席在眾人眼前,享受被「留校察看」時正當性的消失,儀式性殺了自己無數次,等待願意現身的人格出現。
凱文短暫出現時的告白
我自然會害怕,前方躲了什麼吧?別人都以為是小孩子躲起來,其實我是懷疑哪裡都躲著個大人,隨時出來對我指手畫腳,這世界愈發強大的控制慾與我母親的形象重疊,大人都在玩躲貓貓,喊著「抓到你了!」異類者啊,我的身體成為唯一能確認安全的藏身處。
內在的藏身處之多,如一社區,如此大人才找不到,儘管我們常覺得你們的眼目正在外面巡看著,而今日的我要是哪一個,誰才能在外面平安度日?討喜的貝瑞還是博學的歐威爾?但都沒用,下一個總又被外面的某個強勢者給抓到。正如凱文在「海維」的狀態中,仍被兩個女生狠狠捉弄,人性被彌平似的平庸化的恐懼,已伴隨惡意蔓延開來了。
我那叫「家」的外在屋子,在我眼中,窗戶看似都是歪斜的、牆壁的花紋會扭曲、門會伸縮跨不出去、地板也彷彿非實心,媽媽有時像是被掉包的,她的聲音軟尖而細,隨時發出類似刮玻璃的噪音,「凱文,你又搞得一團亂了,是不是?」此時我整個人是被抽離出時空的夾縫中,扁平又扭曲在各個角落,九歲的海維每次都頂替我被抓出床底下,他才是媽媽眼中的「凱文」,又笨又難教。
海維還在哭喊,被打的不是我,在被打的不是「凱文」,我在時間的細縫裡,社會老在玩一個抓鬼的遊戲,無論是否菁英,都要在一個平庸的框架下,沒人敢問那屬於下面的「家庭」組織,是否也演變成一個「除錯單位」,抑或是反撲成為一個「養鬼之家」?家這價值是否也跟著充滿了當代價值崇尚平庸而焦慮?
而佛萊契醫生家中有個迴旋的樓梯,那裡像個子宮,多少個我曾在那裡走過?竄出或潛入,像是我們進化的過程,我們不只是凱文內心遭其他人格排擠的「邪軍」,更是對抗這社會綁手綁腳巨人的游擊軍,佛萊契醫生的走廊則象徵一種進化儀式。
 只有9歲、被虐待最慘的人格海維
只有9歲、被虐待最慘的人格海維
丹尼斯的出現
我想你剛就發現了吧,大部分時候說話的是我,受虐最慘的「海維」把社會化的那幾個人格都趕到一旁,讓激進派的我們出來,因我們比佛萊契醫生更知道,他們的醫療協會是不會接受那種「異常或邊緣者有可能是進化者」的說法,人類這物種不會接受同類的人可能比他更進化的可能,那就代表有被宰制的可能。因此這麼多年,在二戰過後,我們的教育少有讓天才出現的可能性,甚至有以體制來壓抑的作為。
因要維持這資本主義的盛世,普遍的平庸性是絕對關鍵,麻木人心的商品是最熱銷的,這就是我說的:「唯破碎的人才能進化。」唯撕心裂肺的破碎、連廉價麻木都無法安慰或取得的破碎,被大張旗鼓的平庸價值擠到邊緣化的破碎,無從復原也無從伸張的破碎,這並非激進,而是破碎的經驗是人唯一能從那些「無盡的一瞬」中脫逃的方法,大眾所推舉的生活形式將人餵養得無感,這四面八方的徒勞刺激,脹滿各種情緒的人生飽嗝,只有在那些七橫八豎的傷口,經過有自己慢慢復原的過程,發掘出以前不知道的自己,才有可能再脫胎出一個沒有被餵飽以空泛的人。
 激進派的人格丹尼斯
激進派的人格丹尼斯
如果真像美國哲學家Will Durant所說的:「純美誕生於痛苦,智慧是悲傷之子。」如今人們隨感官漂浮在無盡的海洋,起起伏伏的逐浪,卻沒有靠岸的機會般的疲倦,若缺乏深刻的創痛與其之後產生的想像力與思考,便無法離開現代平庸大舉收割的殘虐性,畢竟平庸壓境不是來自個人,而是以繁榮為名的時代意志。
你說,凱文是分裂還是進化?若非近百年追求一致性的平庸,失去對人價值的衡量標準,有些病真的是病嗎?
*「動物園的憂鬱」出自李歐納.柯恩著作《渴望之書》〈MOVING INTO A PERIOD〉一章:「The sadness of the zoo will fall upon society」。

《分裂》(Split)是一部2016年美國心理驚悚恐怖片,為奈.沙馬蘭執導和編劇。由詹姆斯.麥艾維演出擁有24個人格的主角。故事敘述凱文被信任的心理醫生診斷出擁有23個人格,但還有一個未知人格尚未覺醒。為了在人格的戰爭中存活下去,他不惜綁架3名少女。本片在爛番茄持有75%的新鮮度,獲得的評價以正面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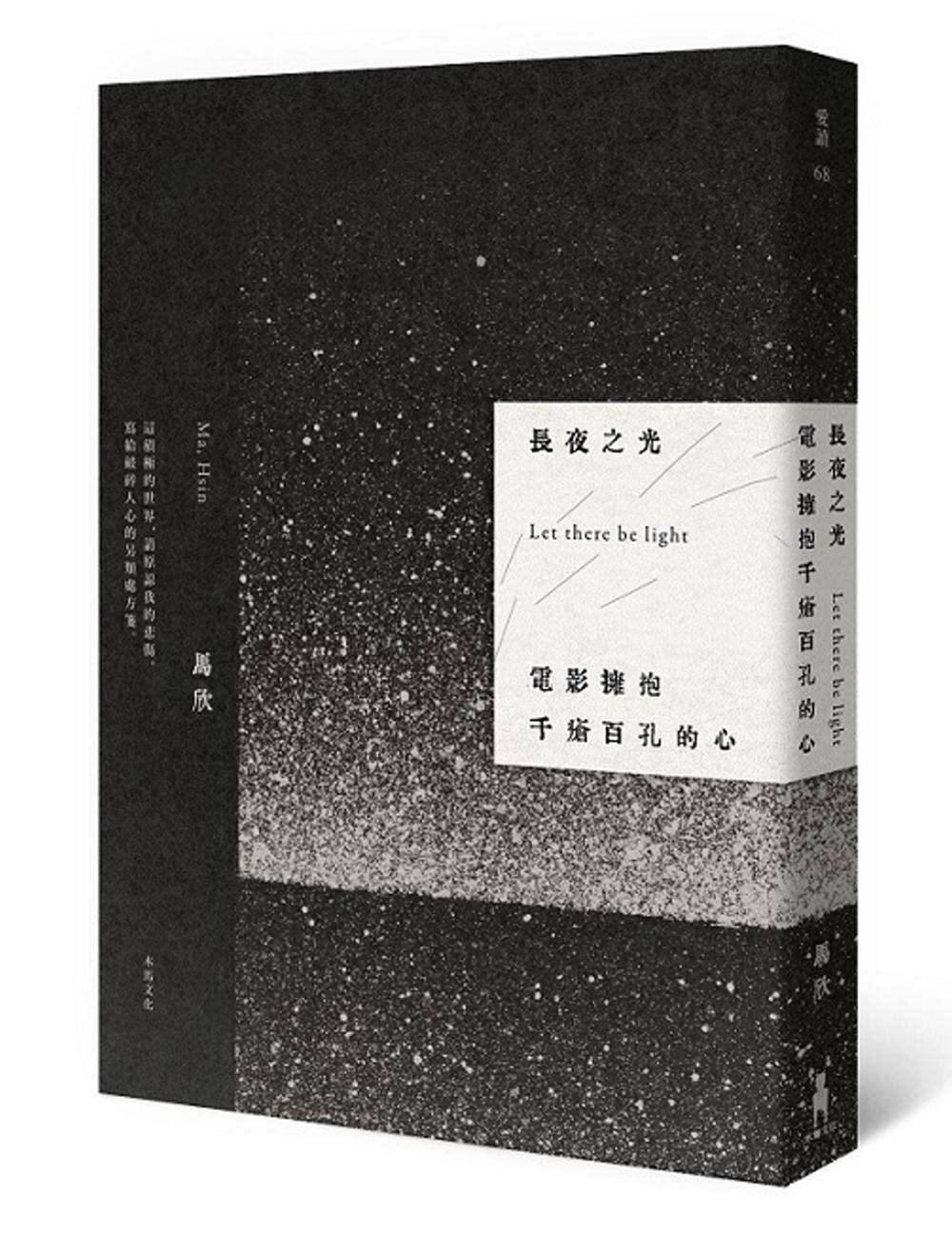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