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是20世紀後半業至今重要的歷史問題,深刻形塑了30多年來許多國家與人們的處境,使人深思現代國家的形式與內涵。轉型正義最簡要的定義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自1980年代開始,大約有80個國家陸續脫離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臺灣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民主化標示了歷史進程的轉向與「斷裂」,那麼轉型正義就是在提醒,歷史並沒有消失,對很多國家來說,也許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時間比處在威權的狀態要更久。人類要付出更多耐性與時間,去面對人與人之間在政體的狀態下造成的傷害與壓迫。這些創傷往往也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於是裂痕與傷口,透過文學反而成了文化的根脈。
11月13、19日將舉行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本屆模憲法庭正是以轉型正義為題,以李媽兜與杜孝生兩案為辯論對象,並邀請4位來自南非、波蘭、智利與澳洲的學者成為國外鑑定人。11月11、12日兩天,中研院法律所也有國際研討會,將針對韓國、南非、哈薩克、波蘭、匈牙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等國家的轉型正義問題進行討論。
為提供讀者另一種理解轉型正義的方式,衛城與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文學與各國轉型正義」專題,從6個文學家的作品理解該國的歷史。此系列中,蔡慶樺寫葛拉斯與德國,林蔚昀寫辛波絲卡與波蘭,林建興寫波拉紐與智利,黃崇凱寫金英夏與韓國,童偉格寫柯慈與南非,紀大偉寫納道詩與匈牙利。要謝謝6位作家參與這個並不容易的寫作計畫。
# 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活動網頁
# 模擬憲法法庭官方網頁
#「比較憲法視野下的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

1999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
文╱蔡慶樺
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在17歲時加入了武裝親衛隊(Waffen-SS),此事在他晚年自我揭露後,引起全歐洲震撼。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每一次共和國重大爭議上都勇於提出諫言,憑著文學的力量在德國戰後與他國和解的進程上做出難以衡量的貢獻,這樣一位被稱為「國家的良知」的文學巨人,卻曾是一位擁護希特勒的青年軍?
我們必須認真地看待這個事件,從葛拉斯身上思考威權時代的渺小個人的失足與責任。
我讓我自己被誘惑了
 心理學家馬爾貝的遺稿終於在2016年問世
心理學家馬爾貝的遺稿終於在2016年問世
先從一本書談起。2013年,德國符茲堡大學心理學史教授阿敏.斯托克(Armin Stock)在學校研究室的地下室裡,找到了一份珍貴的手稿,這份打字機打成的168頁手稿,封面寫著《對於文明世界的合時合眾的觀察》(Zeitgemäße populäre Betrachtungen für die kultivierte Welt),作者未署名,只寫著「一位德國學者」。斯托克立刻知道自己挖到寶藏,因為這是學界尋找已久的卡爾.馬爾貝(Karl Marbe,1869-1953)未能出版的遺稿。
馬爾貝曾任德國心理學協會主席,是符茲堡及法蘭克福心理學研究所的創始人,也是思考心理學學派(Denkpsychologie)創始人之一。他親身經歷了納粹崛起、全民為希特勒狂熱的過程,將觀察寫成這份手稿,1945年完稿。他知道在納粹時期不可能出版(他在這份自稱為「禁書」的手稿中注明了「只到45頁止能夠通過審查」,他也只署名為「一位德國學者」),轉而在戰後尋求出版,但是在那個大家對過往歷史寧可閉口不談的氛圍下,多家出版社認為馬爾貝的研究殺傷力太強,拒絕出版,馬爾貝只好收起這份手稿,1953年過世後手稿下落不明,學界只知道它曾經存在,不知內容為何,直到2013年斯托克讓手稿重見天日,於2016年出版問世。
本書離完稿已經71年,但是書中對納粹時代的第一手觀察,仍然極有價值。馬爾貝探索當時的「大眾現象」,試圖為德國人不分男女、年紀、宗教如此不理性地為希特勒狂熱的迷惑找到解釋,不同於許多觀察家從國際政治、歷史的角度看待希特勒狂熱,馬爾貝從大眾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納粹黨政高層如何誘惑、煽動、暗示人民進入集體瘋狂狀態等法西斯意識形態運作的機制。他認為像希特勒、納粹宣傳部長戈貝爾是構造出一種煽動與暗示機制,通過各種媒體宣傳手段,指示了盲從的群眾;群眾一來從眾,二來在煽動下不斷狂熱化,失去了理性,甚至自我奴化,也使得人性趨近獸性。當你身邊每一個人都做著不正確的事情,你將失去判斷力,如強迫症患者般,強迫自己做出有違自己意願的行動。
書中提到一個歷史大眾現象做為比較:兒童十字軍(Kinderkreuzzüge)。1212年,在法國一個名為史蒂芬的少年,宣稱他看到了耶穌,要傳達耶穌的訊息。他呼籲追隨者跟他一起到耶路撒冷傳教,從法國走到了德國,跟隨他的少年、兒童愈來愈多,一支幾千人的奇異隊伍就這樣組成,往耶路撒冷走去。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可能都不是信仰虔誠的基督徒,但還是如著魔一樣加入了隊伍,這些孩子以為自己會走到聖地,最後卻在南歐流離失所。這個中世紀的傳說,卻在現代成為真正的歷史,馬爾貝用13世紀的故事來解釋20世紀的悲劇, 那麼荒誕卻又那麼真實。
17歲的葛拉斯,就如同兒童十字軍中的一員,看著身邊的人愈來愈多,都朝向某一個目的地前進;他不知道這個目的地在哪裡,不確定是否走得到,但還是決定讓群眾帶著自己往前走,呼喊一樣的口號唱著一樣的歌,瘋狂著一樣的瘋狂。1944年,他加入了納粹武裝親衛隊——這是在紐倫堡大審中被確認為犯下戰爭罪的部隊。
戰後,除了少數幾個朋友知道這段過去外,整整60年,沒有人討論這段過去,直到2006年《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專訪中,他才說出了這一段「恥辱」,震驚了全世界文壇。[注1] 該報發行人、也是這個專訪的策劃者法蘭克.許爾馬赫(Frank Schirrmacher)在頭版撰寫評論嘆道:「我們在這個事件中學到了,生活並不像好萊塢電影的劇情,你永遠可以信賴正義的一方。」[注2]
同年,他的自傳體作品《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出版,更詳細交代了這一段60年前的往事,他說當時他認為武裝親衛隊是一支菁英部隊,並不介意穿上親衛隊的制服,在書中他坦誠:「並不是別人誘惑了我們,而是我們讓自己,不,是我讓我自己被誘惑了。」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呼籲,葛拉斯的出生地但澤市應該取消他的榮譽市民資格,德國許多文化界人士也認為葛拉斯應該退回諾貝爾獎項——風波之烈甚至使得諾貝爾獎委員會必須出面說明,諾貝爾獎並無退回可能。「葛拉斯醜聞」在媒體上延燒,成為這十年來德國、甚至歐洲重要的文化政治爭議之一。
文學者的反省
葛拉斯說,他加入的武裝親衛隊是補給部隊,並非攻擊部隊,他也從來沒有開過槍。為什麼那個並未真的從戰的少年,在60年後引起全國激辯?因為他正是以做為反省德國納粹歷史的文學者而奠立其作品地位,也因此這個反省邪惡歷史的文學巨人,自己竟然是邪惡的一分子,許多人難以接受。葛拉斯迫使我們在60年後仍然無法輕易放下過去,必須去質問:我們應該如何反省?或者,葛拉斯將如何反省他自己?
其實葛拉斯不曾說過他一直站在正義的一方,他以他的文學為整個國家犯錯的人反省,何嘗又不是為了自己當年的失足寫下懺悔書?這並不是到了《剝洋蔥》才表明的立場,我想從另一本書,說明他多年來始終省思他自己以及那一代人在戰爭中的罪行。
 《昨日,50年前》專書
《昨日,50年前》專書
1995年,二次大戰結束50年,日本《朝日新聞》以及德國《法蘭克福環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請求葛拉斯寫作專文悼念戰爭。葛拉斯提議,與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共同書寫,最後兩位世界文學巨人以通信的方式,分別從自己的經驗與記憶反省了「可疑的國家倫理」,釐清德日兩個戰爭發起國的政治與歷史責任,以及如何面對未來世代,如何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政體。兩人的通信激盪出不可思議的思想光芒,除了在德日報紙刊出,也被轉載到幾乎全歐洲的重要媒體,後以《昨日,50年前》(Gestern, vor 50 Jahren)為名出版為專書。
在其中一封信裡,葛拉斯為二戰時期德國軍隊中的敵前逃亡者(Deserteure)平反。在戰爭時期,青年的他看到街上許多逃兵被迫背著「我是懦夫」告示牌,戰時甚至超過二萬名逃兵被帝國軍事法庭判以死刑。葛拉斯問:「可是戰爭的真正英雄,不正是這些人嗎?他們有勇氣拒絕服從犯罪的行為,他們完成了偉大的事物,也就是知道表現他們的畏懼。他們並不盲目跟隨每一個命令,他們的美德就是不服從。而正是這些頑強的說不的勇者,今日仍然可以做為我們的楷模,我們應該要在50年後,還給他們遲來的正義。」[注3] 葛拉斯對這些逃兵高度讚揚,他所批判的對象,其實正是那些服從命令的共犯者,包括17歲時候加入武裝親衛隊的自己。
另一封信中他寫道:「在我的母語中,陣前逃亡有一個字『逃離軍旗』(Fahnenflucht),這是一個很老式的德國傳統概念。而我也跟隨著這個傳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跟大家一起歌誦『因為軍旗比死亡更重要』,毫不理解罪行的後果,以及對於彩色軍旗及標誌神話化之後的毀滅性荒謬。我的世代中的許多人,都準備好追求死亡,我們都相信最美好的事就是把生命奉獻給『元首、民族及祖國』。軍旗對我來說跟『比死亡更重要』的歌聲連在一起,後來結合軍服,讓我遵從那些對國家許下的諾言。換句話說我們穿著德國制服,也生存在某種絕對的天皇體制下。」 [注4]
 雲格的日記《在鋼鐵的暴風雨中》讓一整代年輕人憧憬戰爭,相信殘酷中藏著美麗
雲格的日記《在鋼鐵的暴風雨中》讓一整代年輕人憧憬戰爭,相信殘酷中藏著美麗
雲格是力道十足的文學者,幾乎以一己之力,讓一整代的年輕人憧憬戰爭,相信在殘酷中深藏著某種美麗的事物、以及必須被挑戰的命運。無數讀者怨嘆自己錯過了一戰,並懷抱著激情投入希特勒發起的另一場「偉大」的戰爭。也只有葛拉斯這種高度的文學者,能夠直接與雲格的思想交鋒,穿透法西斯主義架構出的宏偉,看到在「元首、民族及祖國」的謊言中根深蒂固的邪惡。
可是17歲時的他,也只是那無數被迷惑的「兒童十字軍」中的一人,當年他未能逃離軍旗,反而主動去擁抱戰爭,因此他對大江健三郎坦承自己的愧疚,那是一種罪責(Schuld)與羞恥(Scham)的感覺。而他正是懷著這種罪責及羞恥,在《剝洋蔥》中懺悔,「我那帶著年少歲月的愚蠢驕傲所獲致的東西,我在戰後由於不斷滋長的羞恥而沉默。然後壓迫於我的,不曾消失。無人可卸除我的重擔。」[注5]
罪責
《剝洋蔥》不只懺悔了少年在集體瘋狂中失足的問題。葛拉斯並描述一個作家的世界與自我認同是如何發展而成的,如何從年少時候一步一步走向藝術教育、搬到巴黎、開始寫作《錫鼓》(Die Blechtrommel)、面對德國的歷史責任的那個文學者的路;而葛拉斯的懺悔也不只針對武裝親衛隊的過去,他也承認自己在猶太教師與同學遭受迫害時,別過了頭去。讀了這本書,我們才終於領悟葛拉斯是如何在罪責感之中,以那本《錫鼓》嘲諷德國歷史與政治的崇高,並以等身創作切開德國歷史難以面對的過去傷口,即使與一整個國家為敵都在所不惜。那背後的創作動機,是來自自身曾經做為加害者的罪責。然而我們必須問,不曾開過槍、殺過人的那位少年,他的罪與責何在?
戰後首先開始討論德國人的罪責問題的,是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1946年他在海德堡大學開設了「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課程,並出版同名專書,討論納粹罪行帶來的罪責問題。他區分了四個範疇:刑事罪責(來自客觀上可被證明為犯法的行為,法庭是負責審判者)、政治罪責(來自政治人物的作為,戰勝國是負責審判者)、道德罪責(無法宣稱我只是奉命行事因而不負任何罪責的行動,即使法庭不介入,個人也無法自稱免責。只有受不法或不正義侵害的受害者,才有資格原諒他人)、形上罪責(來自對於世界上一切不法及不正義都負有的共同責任,神是最終審判者)。而一般德國人,未曾親手殺害他人、卻依順成為納粹共犯的德國人,究竟應負什麼罪責?
戰後探討納粹罪責時,極為流行「集體罪責」之說,甚至造出「做為犯罪者的民族」(Tätervolk)一詞——所有德國人都有集體罪責,即使不負刑事或政治罪責,也有道德罪責——然而雅斯培斷然拒絕此說法,他強調我們無法指控一整個民族須擔負道德罪責,追究罪責只能針對每一個單一的個體。把每一個體的絕對性消除在集體中,這正是法西斯主義迫害的技術,「在納粹治下如同不再有人類,而只存在著集體。」 [注6] 如果,我們對於納粹抹除每一張猶太人獨特的臉孔、只剩下「猶太人」這個普遍稱謂感到不安,我們又怎能將「德國人」集體化並對以審判?如果我們想想,在納粹時期甚至也有大量德國人因為疾病或性傾向不符合亞利安優生學標準,而被強迫節育(超出50萬人)或者「安樂死」(超出20萬人),那麼「德國人」這個加害者標籤,就更可疑了。
然而雅斯培強調,即使德國人不負擔集體罪責,也背負著根植於內心深處的「責任」(Verantwortlichkeit),這是一種對於他人的永不超出追訴時效的責任。這也就是形上罪責,是一種這樣的良知負擔:成千上萬的德國人、猶太人與外國人在反抗極權主義中尋求了死亡,「而我們這些存活者避開了死亡,我們不曾上街去吶喊抗議,直到被殺害為止,我們寧可選擇苟活,持著即使是正確、但也難以說服人的理由:我們的死,也改變不了什麼。我們存活了下來,這就是我們的罪。在上帝面前,我們知道,我們內心深處最羞慚的事。」[注7]
雅斯培以彷如康德的口吻如此嚴峻敘述存活者的責任與罪責,那正可對比葛拉斯在面對戰爭逃兵時的慚愧態度:某些人是反抗者,而我卻是服從者。服從,或者放棄反抗而苟活者,都是有罪的,都必須承擔無限期的對他者的責任。負責(verantworten)除了是對某事、某個決斷負起責任外,在德文中以反身動詞形式(sich verantworten)出現時,也意指備詢,也就是必須隨時面對質問,必須應答。不斷去回答(antworten)他人、社會、良知、神對我提出的疑問及指控,永遠不停止自問自己是否面對不法不義時袖手旁觀,這就是存活者的義務以及贖罪的方式,這種罪責思維也決定了德國戰後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永不止歇的態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經超過70年,對於歷史錯誤,德國向來勇敢面對,因而能夠取得受害國家的原諒。可是在面對歷史罪責、表達懺悔時,似乎有怎麼做都不夠的感覺,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真正的克服過往?也許曾犯下的錯誤永遠也無法真正被克服,也因此70年來德國未曾停止複雜龐大的懺悔、記憶歷史錯誤的工作,這是存活者對已逝者的無限的責任。
結語:流著淚剝下我的外皮
葛拉斯一生也在實踐這樣的無限的對他人的責任,他不間斷書寫德國陰暗的戰爭歷史,毫不留情地以文學與整個德國經歷戰爭的一代交鋒,從不顧慮政治正確與否,不害怕得罪文壇,沒有他的粗野固執,德國文化界就沒有真正的「克服過往」,媒體因而稱他為「國家的良知」(Das Gewissen der Nation)——雖然他多次拒絕這個說法。然而到了《剝洋蔥》出版後,我們面對「國家的良知」之崩壞,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思索他的文學政治。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的中文版譯名《剝洋蔥》或英文版譯名「Peeling the Onion」皆難以精準傳達德文版原文意涵。Häuten雖有剝除之意,但是這種剝除,是與我的肉身肌膚(Haut)相連,葛拉斯刻意以剝皮一字,書寫其撕開多年祕密的痛楚,剝洋蔥流下的淚水,並非因為洋蔥辛辣,而是來自身體最深處的痛苦。這是文學者對自身政治失誤的懺悔,也是對極權主義痛澈心扉的反省:每一種看似偉大的事物,每一種國家倫理,每一個集體聲音,每一種誘惑我們著魔的美學,都藏著可疑可鄙之物。正是因為這樣的自責,葛拉斯在《錫鼓》創造出了那個德國現代文學史中最傳奇的人物——那個駝背的侏儒,打著鼓尖叫、以噪音抵抗世界的小男孩奧斯卡。
奧斯卡在3歲時識破了世界的虛偽噁心,決定不再長大。他背著父母送他的鼓,拒絕卸下,以鼓聲以及能震破所有玻璃的高音頻尖叫聲,持續對抗世界,並且在各種場合讓一切看似正經的大人社會顯得荒謬可笑。奧斯卡代表著法西斯政權下的平凡人,如何在歷史、國家、政治、民族等複雜巨大的框架中求生存,或者說以拒絕這些框架的方式生存在自己的世界,進而能夠承受那個殘忍無比的世界。奧斯卡代表「對於存在的不情願」(Unwille zur Existenz),因為除了我這個赤裸裸生命之外的一切存在,都難以忍受;我只能以我自身的生命,我拒絕長大因而得以保存的永恆的單純與年少,來回應這個世界。
奧斯卡不是一般小說中的英雄主角,他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因為他的殘缺,必須努力證明自己對社會「有用」,一位無用的侏儒在納粹的生命政治中只能是被消滅的族群。可是這本小說的主角一定要平凡渺小,甚至一定要不見容於社會,這是葛拉斯對抗納粹雄偉崇高法西斯美學的武器。讀葛拉斯鋪陳出來的這個詭異的世界,讀者不得不問,書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他必然想到了17歲時候的自己,那個多麼崇拜菁英的、偉大的意識形態的少年吧?
《錫鼓》之後,他以文學在道德荒原中持續鑿開道路,帶領了戰後的德國人走向克服歷史罪責(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之目標。1999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把文學獎頒給葛拉斯時,在新聞稿中說:「當葛拉斯的《錫鼓》於1959年問世時,就如同德國文學在幾十年的語言及道德崩壞之後,終於被賦予了一個新的開始。」[注8] 而那個孩子氣、自我、荒謬的侏儒,凸顯政治世界、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可笑,也正是葛拉斯對自己所提出的幽暗的反省之開始,最終,在《剝洋蔥》中發展成了最徹底的自白。
以色列作家歐茲(Amos Oz)在關於葛拉斯的紀錄片中這樣敘述《錫鼓》對他的意義:「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我痛恨德國人。我不願跟任何德國人說話或者往來,在我的家庭中禁用一切德國產品。可是,當《錫鼓》的希伯來文版本在1977年出版後,我如同被電擊一般。我讀了這本書,而從那時開始,我已不可能再去恨所有與德國有關的事物。」[注9]
葛拉斯的文學就是有這樣的力量,能使受害者放下恨意。然而晚年的自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使受害者放下恨意的關鍵也許就在於,加害者從未放下對自己的恨意。葛拉斯以這樣的恨意驅策他一生的文學苦行,告訴我們,做為存活者、或者加害者能夠做的,就是對於自身的軟弱的負罪存在、對威權歷史絕不保留的揭露與批判,並對於那個法西斯幻夢、那面彩色軍旗絕不留情的摧毀。葛拉斯的罪責何在?他已給出了清楚的答案。
作者簡介
〔注釋〕
1. “Günter Grass: Ich war Mitglied der Waffen-SS. Der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bricht sein Schweigen. Gespräch im Feuilleton”, F.A.Z., 12.08.2006, Nr. 186, S.33.
2. Schirrmacher, Frank: "Das Geständnis” F.A.Z., 12.08.2006, Nr. 186, S.1.
3. Grass, Günter. und Ôe, Kenzaburô: Gestern, vor 50 Jahren: ein deutsch-japanischer Briefwechsel. Steidl, Göttingen 1995, S. 45-46.
4. Grass, Günter. und Ôe, Kenzaburô: Gestern, vor 50 Jahren, S. 61.
5. Grass, Günter: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Steidl, Göttingen 2006, S. 216.
6. Jaspers, Karl: Die Schuldfrage. Lambert Schneider, Heidelberg 1946, S. 38f.
7. Jaspers, Karl.: 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 Reden und Aufsätze. Piper, München 1951, S. 162f.
8. Nobel Prize, "Pressemitteilung: Der Nobelpreis in Literatur 1999. Günter Grass" (Abrufdatum: 18.09.2016)
9. Wittmers, D.(2015): Schrieb ich Buch nach Buch - Zum Tod von Günter Grass. Online unter: https://youtu.be/kvq9kIKlHZw (Abrufdatum: 10.08.2016).
【時代的錫鼓響起,誰在清理戰場?】系列專文
02|林蔚昀:猴子輕柔的鐵鍊聲──從辛波絲卡的詩,看波蘭百年來的歷史難題
03|林建興:1973年之後的波拉紐
04|黃崇凱:你的祖國正在呼喚你──讀金英夏《光之帝國》
05|紀大偉:桀驁不馴匈牙利──納道詩的《平行故事》
06|童偉格:就像人不能豁免於政治──成為南非他者的柯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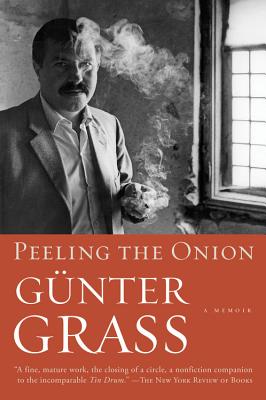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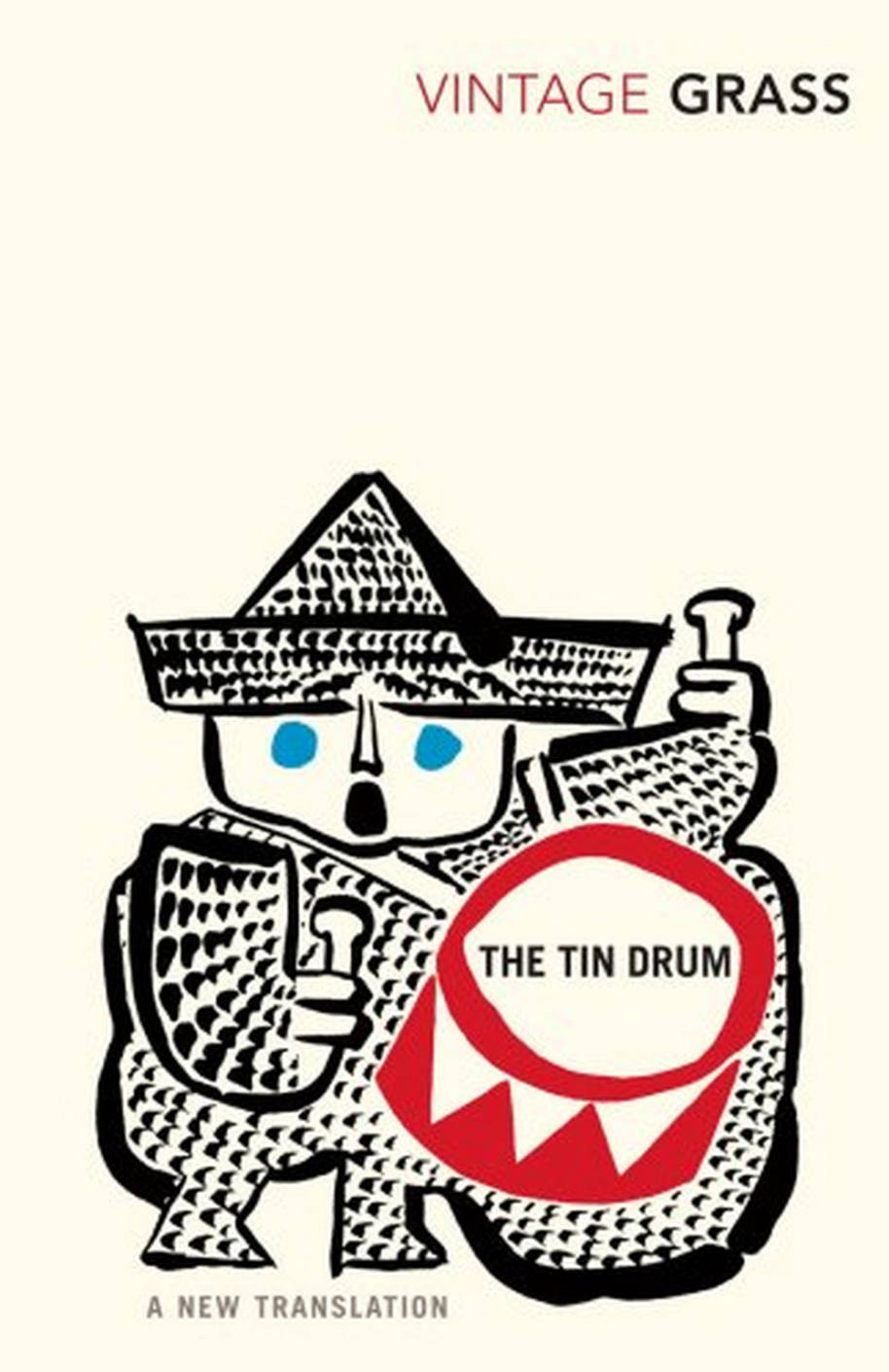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