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把情詩放在很高的位置。愛情之毒與權力之毒,能激發人最大的激情,惟前者可以蛻變為詩,惟對此詩意之嚮往而敢於邁向死。想想《飛狐外傳》裡的程靈素、《天龍八部》裡的阿紫!然而,情詩未必都是這般烈燄,也可能是嗆人的煙、餘紅猶存的灰。因此情詩大宗其實是追憶。
木心情詩即是建立在追憶的廢墟上,比如這首〈JJ〉:
十五年前
陰涼的晨
恍恍惚惚
清晰的訣別
每夜,夢中的你
夢中是你
與枕俱醒
覺得不是你
另一些人
扮演你入我夢中
哪有你,你這樣好
你這樣你
記憶細節雖然模糊,訣別本身卻是清晰的。牽掛以夢呈現,看似常見,然而重點在「的你」、「是你」、「不是你」三個層次。第一層,「你」尚只是「夢」的一部份,第二層次,帶著肯認的熱切,夢中那真是你!你即是夢。然而,「你」之所以恍惚又清晰,正是因為已經訣別了——重逢真被實現,夢就不是夢了,因為過去,所以值得念想。「你」早已被留在十五年前,夢中不是你。既然不是你,為什麼又見到你的形影彷彿徘徊?夢如劇場,回憶即是演出,托你之名,之貌,來夢裡慰藉我吧?無論如何,夢再真切,也不過是模仿,模仿不到你的萬分之一好。「你」為什麼「好」?因為凡屬於「你」,沒有不好的。朝霞當然美,然而一百個詩人寫過,也會變得陳腐;頌讚愛人最好的方式,不是拿已被承認的美去比喻,而是使他本身變成美的最高級,僅就在你們的關係裡有效,獨一無二。
在我看來,極簡的詩不是找一個好懂但是創意不高、老被模仿的比喻,而是像〈JJ〉這樣,清澈,執迷。再看木心另一首詩〈肉體是一部聖經〉,開頭說情人是稀貴的金琴,當青春正到好處,才可能正確而淋漓地彈奏,使「生活是一種飛行/四季是愛的襯景/肉體是一部聖經」——飛行,採夏卡爾定義,他畫中飛行的男人,女,花束與牛羊,最強的喜悅是變輕;肉體如聖經,被教徒一再翻閱、深入、探索其奧義……。第二段詩,過了二十年重逢,金琴變成家常桌椅,塵膩取代了光輝,然而,曾彈奏過金琴的人何嘗不知道底下的真質?
久等你再度光臨
這是你從前愛喝的酒
愛吃的魚,愛對的燈
這是波斯的鞋,希臘的枕
這是你貪得無厭的姿式
靈魂的雪崩,樂極的吞聲
聖經雖已蔫黃
隨處有我的鈐印
切齒痛恨而
切膚痛惜的才是情人
佈置往昔舞台,熟稔一切細節,「聖經雖已蔫黃」,然而也還是曾經屬於我的聖經,肉體上隨處都有舊情的鈐印。波斯的鞋,希臘的枕,這異地風情的提醒似乎暗示了某種消逝的情欲氛圍與開闊文化;全詩雖未明示時間地點,卻不免使人聯想到許多大震盪後的夢痕。
夢裡的人,像一種酸苦入髓的滋味種在齒間,牽引肌膚的顫慄。「切」與「痛」相應,最親密,最痛,所以能崩,能吞,務在多得。貪得而無厭在愛情裡是正向功德。
楊佳嫻
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台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金烏》,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最新作品為《小火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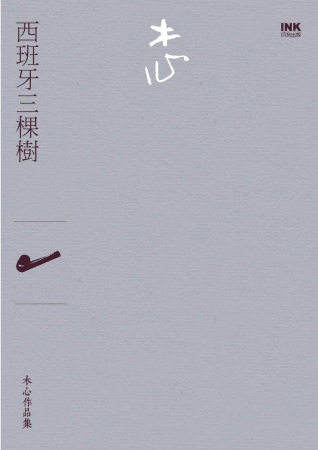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