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前,有一棵樹,她很愛一個小男孩
男孩也很愛這棵樹。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男孩長大了,
樹卻常常很孤單……
你是那棵一生無私付出的愛心樹,
還是那個深深被愛的小男孩?
親自翻譯完日文版《愛心樹》的村上春樹說:這本書你一定要反覆的讀,你如何解釋這個故事是你的自由,不一定要訴諸語言,故事就是為此而存在的。從《失落的一角》到《愛心樹》,謝爾.希爾弗斯坦的繪本作品充滿寓意的故事,簡單中耐人尋味。我們邀請幾位喜愛本書的作家,從教育、愛情、文學和生命經驗各種角度分享《愛心樹》的幾種讀法。
文╱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在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知名繪本《愛心樹》中,愛心樹和小男孩之間一個付出所有、一個予取予求的關係,常被解讀為人際間情感的無私奉獻與犧牲,或是不對等的守候與期盼,但是愛心樹與男孩的故事,其實也提供了思考人與自然互動關係的線索。
在樹與男孩的關係中,樹始終扮演著「給予」的角色,而且看起來,它因為給予而感到快樂;然而當老去的男孩把樹幹砍掉,坐船離開之後,作者卻說:「樹很快樂。但是,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快樂顯然饒富意味,那是在愛之中的寂寞與失落,也暗示了人們主觀認知的投射與想像。男孩愛樹,但他的愛是建立在樹支撐了他每一次的生活所需之上,而在一次次把樹僅存的所有帶走之後,他始終相信「樹是快樂的」。
樹很快樂。它因為愛、因為給予、因為犧牲而快樂。自然萬物因為對人類的付出而有價值,因此值得我們的愛與感恩。這樣的說法並不陌生。日本曾有一家串燒店的廣告海報引起注意與討論,內容是一隻背著蔥的母雞,歷經長途跋涉與重重難關,只為了趕去串燒店當烤雞串。此種「犧牲信念」下的商品邏輯,讓人們身邊總是不乏「自願被吃」的經濟動物,因為我們(想要)相信,牠們是快樂的。
此種擬人化的想像與投射,說穿了只是合理化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利用甚至剝削,但一廂情願的想像總有盲點,故事中的男孩看不見樹的衰老,也看不見它表達愛的形式——例如在樹上刻愛心——其實是對愛的傷害。觀諸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許多有關生態保育的爭議不也如此?我們就像任性的男孩,認為自己對待自然的方式理所當然,沒有修正與調整的必要。

但是,我們其實活在一個萬物正逐漸走向愛心樹結局的世界。沒有任何一種生物,承擔得起這永恆而單向的「給予」,「愛心樹」們正在凋零。如果我們堅持那愛的模式必然是正確的,終將陷入一個困局,那就是,這些「愛心樹」甚至來不及長大。這是何以有「生物多樣性之父」之稱的威爾遜(E.O.Wilson)在《半個地球:我們為生命而戰》中,捨棄了婉轉的道德勸說,斷然宣布:留半個地球給其他物種吧,否則第六次大滅絕肯定要發生了。(參見黃怡〈「留下半個地球」—生物多樣性之父的最後籲求〉)
威爾遜的呼籲,是對男孩們的召喚。讓一棵樹用它原本的樣貌活著,讓蘋果留下,讓葉子留下。這看似不切實際卻無比沉重的呼喚,是要我們留住感受的能力,留住愛的能力。就像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在《愛之旅》中引用的那首三千多年前情詩的女主角,她放開了捕捉的鳥,只為了讓遠方的所愛可以「傾聽鳥的歌聲,充滿沒藥的芳香。」
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現當代文學、動物文學、家族書寫等,長期關心動物倫理相關議題,近年主要之研究方向則為城市中人與動物之關係。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以台灣當代文學為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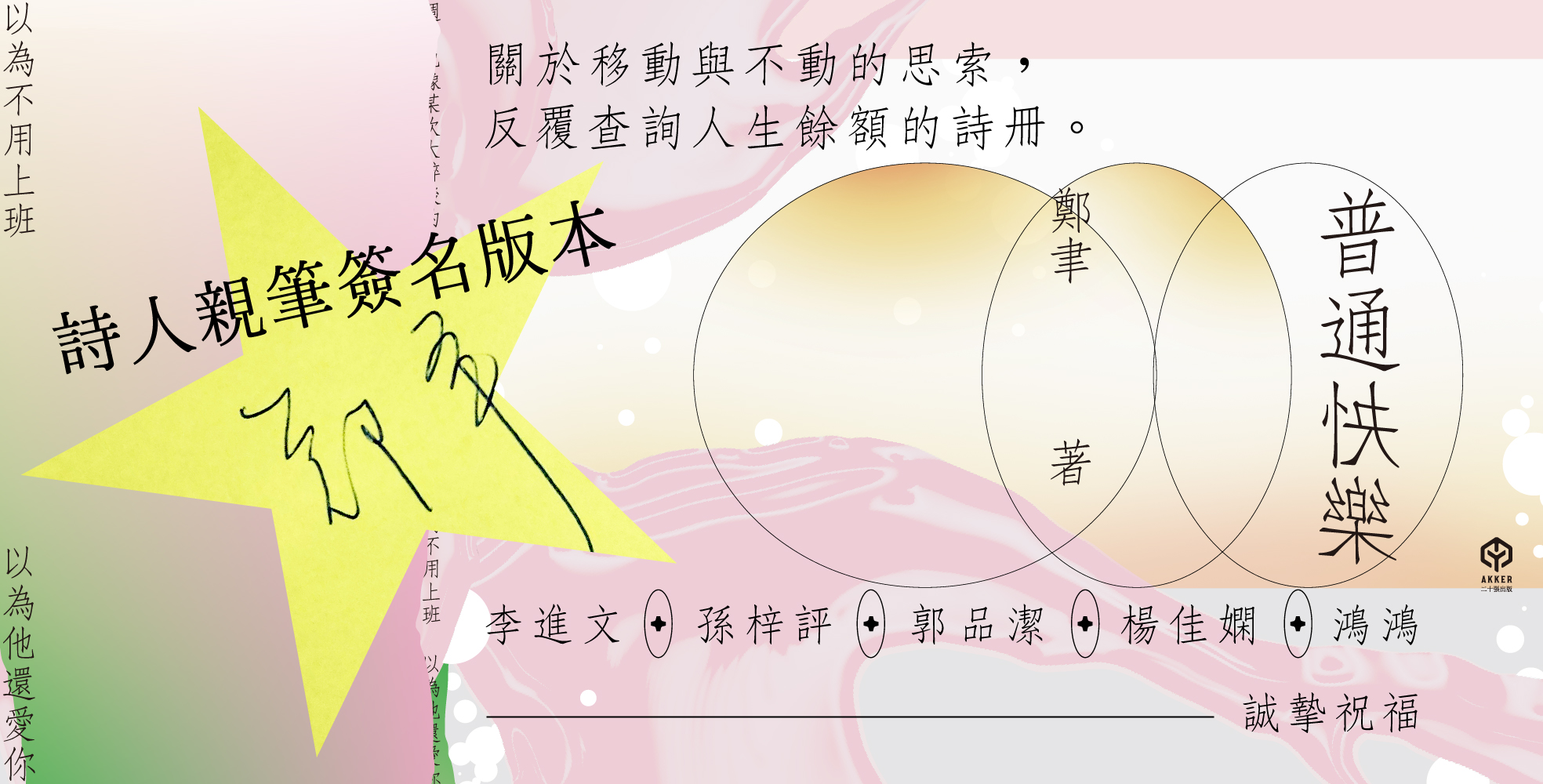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