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翻起以前坐在歷史課堂上的記憶,幾乎都是從中國上古先秦時期為起點,一路細數: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隋唐五、宋元明清華。一個接一個的朝代,一位接一位的皇帝,盛世衰世,明君昏君。歷史二字始終以政治為中心,旁及社會經濟,偶有文化藝術穿插。若非走到北宋來了幅《清明上河圖》,幾乎看不見平民百姓的身影,與日常生活的樣貌。歷史,彷彿等同政治史,除了帝王將相還是帝王將相,是一種由王位俯瞰的角度。
不只國民教育階段如此,大學甚而研究所,也多數不脫此一狀況。蔣竹山憶起他的求學時期,「老師講宋朝,一個學期結束了,陳橋兵變還沒講完。」傳統歷史教學訓練著眼於政治,「整個學期下來,很容易讓學生以為歷史只有這些。你就不會知道像《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這方面的歷史。」傳統歷史無法滿足蔣竹山,對歷史浮現愈來愈多疑慮的他,便開始自己「向外發展」。
無巧不巧,彼時台灣史學研究正面臨從社會經濟史轉到新社會史的階段,於台大講授社會史課程的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便為重要推手之一。蔣竹山每個禮拜風塵僕僕地從政大到台大聽課,汲取杜正勝認為歷史研究應該「由主幹轉為枝葉」的主張,得到了嶄新的視野與指引。
從碩士到博士,一直到現在於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他所關注的不是傳統歷史所聚焦的政治領域,而是社會文化與物質文化。當近代台灣的明清史研究走向被學者們形容為「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之時,蔣竹山無非列屬其中一員。其《島嶼浮世繪》與《裸體抗砲》二書,在在呈現出「聲色犬馬」的生動與繽紛。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裸體抗砲》的副書名是「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說到「暗黑」二字,溫文的蔣竹山笑了起來。「其實只是借用現代年輕人常用的流行語。」書中集結了他十幾年來的論文與心得,「我之所以會寫這些,部分是因為我很喜歡閱讀明清筆記小說。」那些一般人或有窺探、獵奇之心的項目──陰門陣、過癩習俗、五通神、纏足等等,都不是正史會以坦蕩正面態度記述的內容。明清文人喜歡藉著書寫留下這些記錄,多少也帶有一點獵奇感,「但可見我們現在做的這些所謂『微不足道』的歷史,明清文人也在關注,否則不會寫下來。」
不過,對歷史研究者來說,並沒有所謂暗黑不暗黑,那都是當代社會生活型態的一部分。即使寫出來的文字,會讓現代讀者感覺過去這些事物帶有奇詭、神祕的成分,但蔣竹山的觀看方式並不如此。「我們若想試著還原歷史,就要站在過去的角度再寫歷史,也就是『回到過去寫當下』。」若用現代眼光看歷史,不免會出現「以今批古」的問題,「例如五四時期的文人在寫纏足史時,在當時『強國保種』的概念之下,將過去的封建視為負面,進而加以批判──一種『五四時期男性文人的主觀想法』。」蔣竹山認為,那才是真正的獵奇。
「無論文化史或敘事史,都要回到文本本身。語言在產生的過程裡是怎麼書寫出來的,要先去瞭解那個語境。」蔣竹山提及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神入」(empathy),「回到過去寫當下」為的是要以歷史的同理心,讓自己處在千百年前的時空景況,甚至假想:如果我活在那時,我是哪個階層的人,我怎麼過日子?當我遇到戰爭、疾病,或逢上節慶祭典,我會看見什麼、有哪些事要做?如此一來,纏足、陰門陣、痲瘋病、五通神,會是我的習以為常,還是與我無關的茶餘飯後?它們之於彼時的我而言,縱有特異之處,但仍是「暗黑、荒謬、失控、物件堆疊、人聲雜沓」的嗎?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歷史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關懷重點,重點在於如何呈現出歷史意義。」蔣竹山認為,文化史、生活史、物質史或身體史,不可能寫成如全球史或國家史那樣龐大的線性史觀,卻能拉近我們對某些議題的瞭解。
「若只看政治史、外交史或制度史,很多東西是斷裂的。但生活史或文化史是可以有延續性存在的。」政治可能因為改朝換代而一夕變天,民眾的生活卻不會一覺醒來就完全與昨日切割。「你看半世紀前的日治時代,還是有很多層面和我們現在息息相關。」再久一點的明清,甚或更早之前的諸多不可考,並不因時空遞嬗全數消滅,依舊留下些許殘影,待後人一一挖掘、連結。「歷史有趣之處也就在這裡。」微觀的切入,為歷史長出了血肉,同理心的存在,也讓《裸體抗砲》中的「暗黑」元素,擺脫如寰宇搜奇般的小道之議。
〔蔣竹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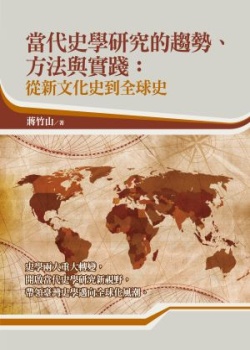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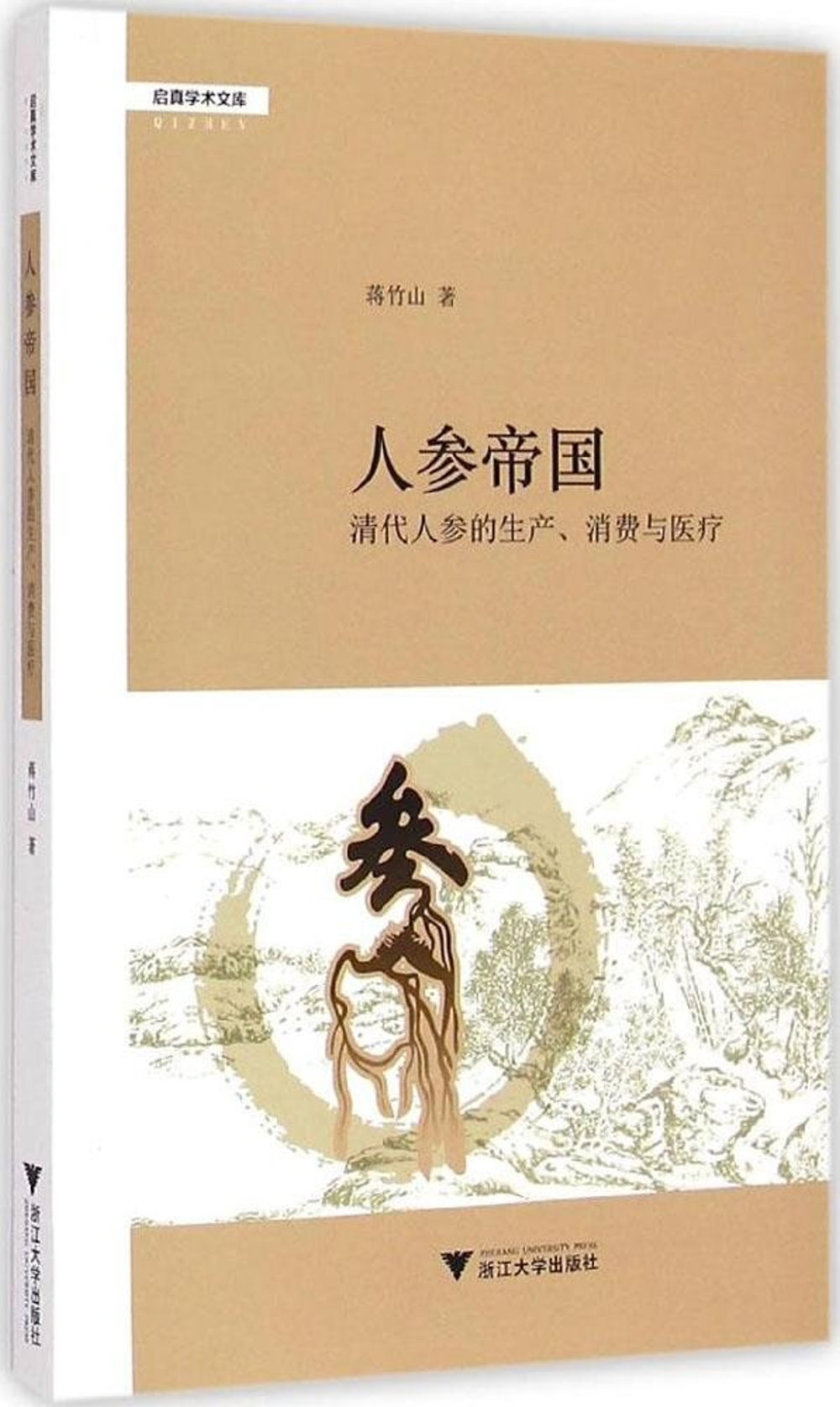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