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祢在嗎?沒在也沒差吧,我剛殺了一個人,她叫王佳梅,她說她要去祢那裡,我不知道她去到了沒,什麼「天堂」之類的,我沒讀過什麼書,也不知道那裡有什麼好,我只知道這裡不好。請原諒我殺了她,一個被當成祭品養大的人,殺了另一個祭品。這城市膜拜富裕教,而我們都犯了貧窮的原罪。
神?祢在嗎?沒在也沒差吧,我剛殺了一個人,她叫王佳梅,她說她要去祢那裡,我不知道她去到了沒,什麼「天堂」之類的,我沒讀過什麼書,也不知道那裡有什麼好,我只知道這裡不好。請原諒我殺了她,一個被當成祭品養大的人,殺了另一個祭品。這城市膜拜富裕教,而我們都犯了貧窮的原罪。 
這世界都出油似的,滴著流洩出飽滿金黃的油脂來,人們雖然貪得無饜但沒餓過地猛舔著,肥丁照樣開始他一天的勞工生活,有一搭沒一搭的賺著蠅頭小利,餓了吃著速食罐頭填腹,這城市飽得滿生嗝氣,有些瘦得只剩紙片樣的女孩依偎著這城市的油膩,半夜上演一如平常的生存遊戲,肥丁沒吃多少但滿口垃圾食物,嚼著如牲畜吃著食糧。另一頭有人夾著人體壽司配美酒,這年頭,人體到底被當成什麼樣的商品?直到她被攪碎了送到餐廳市場,人們才發現不住嚼動的嘴,吞嚥了什麼,自己從來不知道,比較確定的是貪心,人肉鹹鹹的市場,餐桌怎可能乾淨?
香港,2008年的案子被拍成電影,一個邊緣女被殺了,之後迅速結案,幾年之後,有人想去尋找這些邊緣人走去什麼樣的邊緣?如果有錢人已成一個法制外的國度,窮人是否也已另成了一個國家?
以下是肥丁的晚禱,如果導演踏血推演出兇手肥丁的遭遇,我是否也能循著血跡,去另一個底層的國度看著另一個「肥丁」?
神?祢在嗎?沒在也沒差吧,我剛殺了一個人,她叫王佳梅,她說她要去祢那裡,我不知道她去了沒,什麼「天堂」之類的,我沒讀過什麼書,也不知道那裡有什麼好,我只知道這裡並不好。
王佳梅死前,唸聖經上說的:「凡神造的都是好的,只要謝著領受,都是不可棄的。」至於有什麼棄或不可棄的,以我這人是說不上來的,我能被再撿起來什麼?無法明確的知道,我應該什麼都沒剩了,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跟祢說什麼,我不習慣跟別人說話,但非常習慣沒人聽我講話,所以祢在或不在聽其實都沒關係的。
我只是要交貨(王佳梅)給祢,可以簽單嗎?那她以後可以比較幸福點了嗎?
我是不知道祢的那所謂天國是什麼樣子?但我活的世界,祢還有在管嗎?我不知道,從母親死後,我被安置在一個個陌生的地方,但無論到哪裡,都是自己一個人的迴音世界,其實很煩的,這世界有滿滿的人,卻沒有人真的在,沒人鳥我,很好,我不要他們。但我仍被自己煩死了,那些雨的聲音、陽光的刺眼、媽媽照片裡總有深淺不同的微笑,這些都擾嚷著。
雖然自己也是人,但對於人這生物,我是極陌生的,他們總是吃很多、用很多、要很多、到處都是他們的開發地,有他們就沒別的生物,除非可以取悅他們的寵物,而像我這種像豬一樣的,是會被排除的。
我看到的女人都可愛,包括我媽媽、孤單的房東太太、慕容跟佳梅,但為什麼,那些人都把她們想成貨品一樣。把活人當成已死的,就像對待我一樣無情,我知道佳梅為何想死,我想,那就讓她死吧。
 我知道佳梅為何想死,我想,那就讓她死吧。
我知道佳梅為何想死,我想,那就讓她死吧。
王佳梅第一次跟我見面,就說她想死,但有什麼差呢?我對我們這「地方」也是非常陌生的,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留住她的,我們這島上花花綠綠的,有好多好買的東西,但如果都不想買,或買不起,那我們算什麼呢?對我來講,沒有什麼留或不留的問題,哪裡比較好?我暗戀的慕容嚮往的美國?佳梅說的天堂?我都沒差,我也沒存在在這裡過,我不懂她們想什麼,去哪裡有差嗎?去監獄有差嗎?哪裡都沒差的,哪裡都很孤單。
對,神,我有名字的,我叫丁子聰,人們叫我肥丁,或「喂」,沒人看到我、沒人注意過我,我只是個搬貨的,我模樣醜怪又窮,人看我就像蟲子一樣,「搬了就快走吧。」跟我搬的東西一樣,去哪裡?能安身嗎?
是隻蟲子的話,連禱告都不用了吧。因為蟲子沒有什麼「希望」這種東西,別人一踩就稀爛,「希望」就類似這樣的不堪,過了期就好腥臭啊。上帝,祢有窮過嗎?在這地方,貧窮是罪。我原來就犯了這樣的罪,而且是無期刑,我身邊都是犯了窮罪的人,我們有的只是想「越獄」,祢說說,我們犯了什麼罪?
男盜女娼嗎?笑貧不笑娼?在我們自己的「監獄」裡?不要開玩笑了,上帝,我們原來就被他人看守得好好的,窮人住窮地、新移民搬來住我隔壁,他們把這區都蓋成一個牢,我們不用判罪送刑,本來就在服刑。我知道我生來是個奴隸,王佳梅也是,所以我跟臧警官講:「我討厭人。」他們是集體把某些人看管在個地方做工與做雞的,上帝,祢有看過養雞場嗎?那些雞連腳都來不及長出來,就灌食到要被殺了,我感到傷心啊,不是因為我,是因為王佳梅還想要有希望,我不希望她跟慕容都被希望搞得一身殘。祢有來看過我們嗎?我們每天醒來都好像沒真醒來,我們是共同在做同一場噩夢,醒來才發現昨天還沒過,前天也沒有醒,神,祢有過這滋味嗎?窮到一生如一日。
臧警官,是祢派來的吧!我討厭他了,不要叫他再來了,我本來是沒有心的,把它寄放在我媽那裡,就不會太痛,只要維持呼吸就好,「心」這東西,就像佳梅說的,會痛會累,會讓你巴望想過更好的生活,但我的心看到比我還窮的孩子會痛、看到佳梅跟慕容這樣作賤自己會痛,對我自己的事大致不痛了,像微生物般運作就好,但不要看到跟我一樣處境的人,如果人活在地獄,心就像鐵鎚一樣重。
少年時,我曾被安置的一個地方,有個老師跟我們唸過一本幼兒版的《變形記》,講有一天某個人醒來變成一隻蟲的事情。我問老師:「但他不是本來就活得像條蟲,有差嗎?」老師沒回答我,原來,以人的形貌被當隻蟲子使,是正常的事情,像我這樣不吵不鬧的待在供應鏈裡,一旦發現自己是個「人」,就可能是個災難,這個故事讓人想哭,臧警官,其實我曾經偷看一點書,因為我發現多半都是心痛的人在寫書,那個《變形記》的作者很痛吧,是跟我一樣嗎?
有人說我殺人、碎屍很殘忍,其實我也不知道人們說的殘不殘忍是什麼意思?我沒見過什麼不殘忍的,從小就打工,看人殺豬畜,我沒有像你們在超市買已經切好的豬肉,我不知看不到屠殺是否就代表很仁慈?我們這種從小就在市場穿梭的小孩,常看到滿地的骨渣與血泥,我們負責清理,中午吃飯就給我們有碎肉的大骨吃,大家吱吱滋的吃,我沒看過人所謂的「仁慈」,我生來就看到屠戮,只是不是你們負責那塊,有錢,有時是保障你們活得像是「好人」。
神,我說臧警官想太多了,其實我沒有像他講的戀母或恨女人,那是有時間的人在想的事,我跟佳梅是朝生夕死的,至於寂寞,那發明給有點餘裕的人想的事,我們講它太奢侈。如同愛一樣,沒被愛過的寂寞,是從頭徹尾的我們。屬於貧困階級的寂寞,就是人生,除非死去,不然沒有停止的一天,被問會不會寂寞,就像問自己有沒有呼吸一樣多餘,我們這種人的寂寞因為沒法換算成商業利益,多了就會漫延成河吧,成一道護城河,保住市中心人們寂寞的獨特,哪裡都流不走,又深又黑地守護著階級性的優雅,至於那些暴虐的寂寞,就吃掉我們,一口口的,如城中獻祭的小孩,太窮的就丟給牆外無邊的寂寞,吃掉了,屍骨無存,總有下一個孩子,世襲在更貧窮的家庭裡,就丟給城外的狼吧,圍著火光的人們總這麼說。
本就沒有人會找阿梅啊,神,臧警官只是我幻想出的一個美夢,夢想著遲早有一天,有一人會來找我們,然後問我為何要做這樣的事?我真希望有人為我想這麼多。
 總有下一個孩子,世襲在更貧窮的家庭裡,就丟給城外的狼吧,圍著火光的人們總這麼說。
總有下一個孩子,世襲在更貧窮的家庭裡,就丟給城外的狼吧,圍著火光的人們總這麼說。
人們信仰著富裕,然這個信仰歷來是有排他性與獻祭儀式的,我不知道祢還是不是他們的神?而走不出貧窮社區的我們則是這群人的祭品,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在城市的角落,貧窮差距還沒到門口前,人們就會當成沒發生,只要我們這群孩子仍足夠為這城市獻祭。被當成祭品養大的人,殺了另外一個祭品,神,祢說有罪嗎?我們都犯了貧窮這該死的原罪,金錢成暴力,狼就要來了,有人要把別人家的窮孩子推出去了,這城市再度靜悄悄的,沒人踏血尋梅,我們無人聞問,孩子們在麥田裡,一排排地筆直往懸崖走去,神,我不認識祢,但請祢認識他們。
 《踏血尋梅》的丁子聰
《踏血尋梅》的丁子聰
作者簡介
多年寫樂評也寫電影,曾當過金曲、金音獎評審,但嗜好是用專欄文偷渡點觀察,有個部落格【我的Live House】,文章看似是憤青寫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說的),但自認是個內心溫暖的少女前輩(咦?)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當代寂寞考》與《長夜之光:電影擁抱千瘡百孔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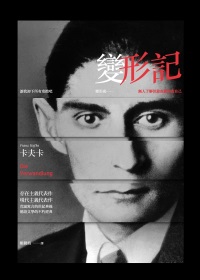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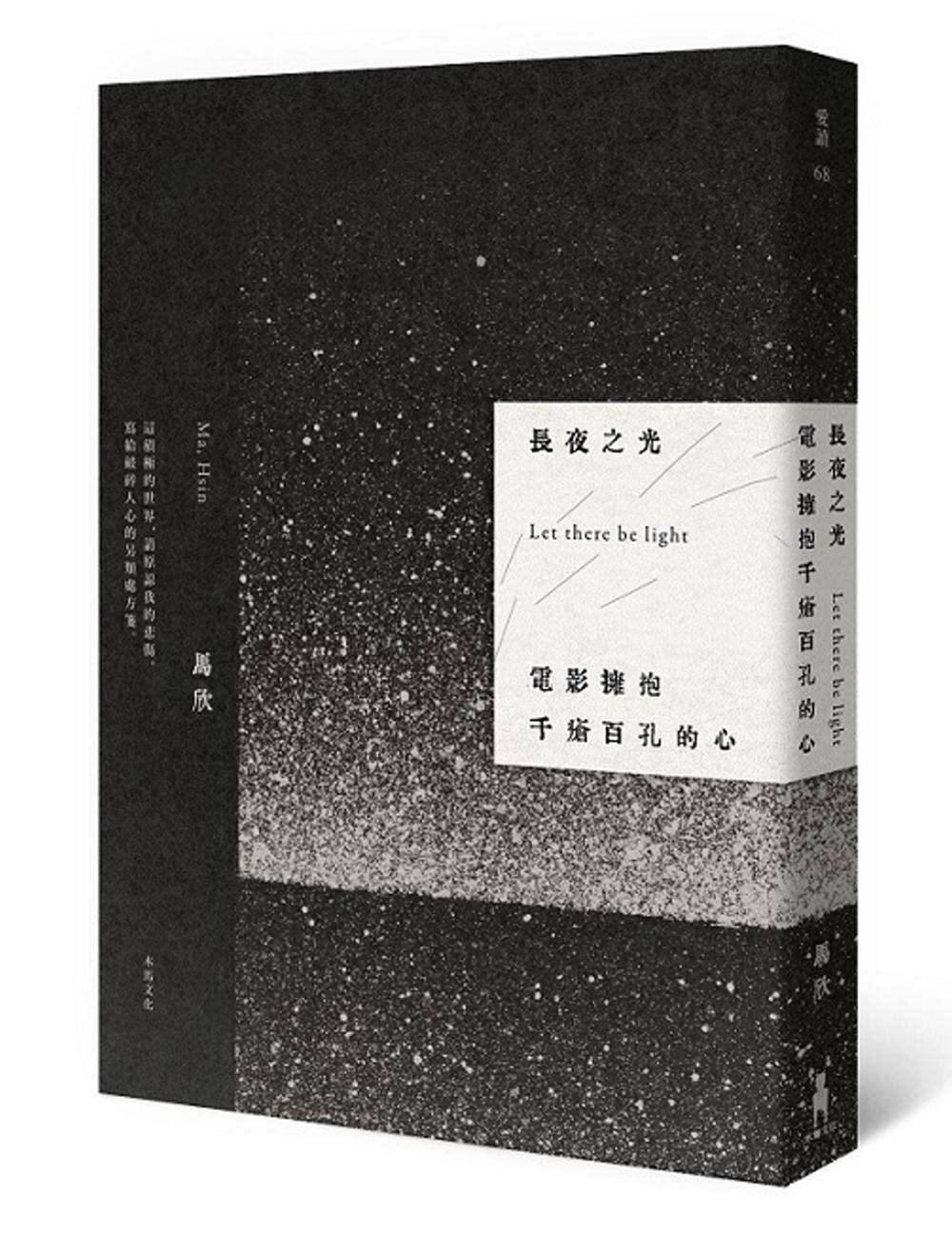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