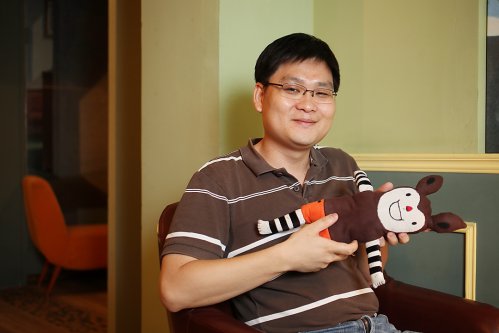
(攝影/但以理)
「那時的台灣就是個大工地,煙塵、泥濘,滿是臨時搭建的違章,生長在那樣凌亂不堪的環境,我人也是好好的,沒缺手缺腳啊,」說起童年,鄭順聰臉上漾著笑意,從小在嘉義民雄鄉下長大的他,從成長經驗出發,甫出版的小說《家工廠》寫的就是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裡,勞動階級和街坊鄰舍的故事,而開麵包烤箱工廠的爸媽、身旁的工人、以及家附近的精神異常者,都在這本新書裡。
2008年,鄭順聰應《幼獅文藝》之邀,寫了一篇兒時幫鄰居拔雞毛賺零用錢的散文〈那些雞毛小事〉,這一寫,勾起了許多兒時回憶,於是有了《家工廠》的寫作計畫,他便以家裡的工廠為核心,故事不斷向周圍拓展出去。2010年,這篇文章也收錄在《晨讀10分鐘:幽默散文集》。
1976年生的他,說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小時候總稱自己家為「阮工廠」、「阮叨工廠」,新書取名《家工廠》,除了含括家的概念,亦帶出當年家庭即工廠的時代氛圍。他表示,文中夾雜的閩南語對白,是寫作時最需要克服的部分,考量的是:如何讓讀者看懂?他沒有意識型態,只用最直接的口語呈現昔日與父母對話的情境。「文學創作是與人溝通,所以我沒有使用拼音文字,那可能會造成更大的距離。」
電鑽是冷面殺手,每一次動作,都要無懈可擊,不能重來。
單單焊燒時那道刺眼的光,即吸引廣大注意,而孔雀開屏式的火花,更是華麗,讓焊槍沾沾自喜。
鉗子總是挑三揀四、小裡小氣的,拔完這個打歪的釘子,又戳入那個孔洞掏出鐵絲……它很熱心,更愛八卦,解決許多危機,也趁機打聽工具的動靜。——〈工具〉,《家工廠》
在他筆下,鐵工廠裡的物件都有了鮮明的性格,「小時候工廠就是遊樂園啊,扳手就是玩具,輪胎內胎可以划船,還可以跳下水抓大肚魚。」物質條件不足的環境,正好激發兒童找尋樂趣的天生本能,自己發揮創意填補空白,「這應該是我與文學產生聯繫的源頭,後來做編輯工作也是如此,都是在空白之中填上東西。」
鄭順聰說,小時後非常渴望閱讀,可是書架上除了課本,沒有其他讀物,鄰居的《小王子》也被他看得快爛掉了,「直到上高中後有了自主能力,我開始大量閱讀,可能是小時候物質匱乏產生的反作用力吧,」那時的他,曾打電動被記大過、喜歡女孩遭遇挫折,憂鬱少年於是喜歡上文學,從洛夫、鄭愁予、徐志摩、白先勇,到普魯斯特、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統統來者不拒。
因為熱愛文學,對機器毫無興趣,他退伍後即進入出版圈,並在《聯合文學》雜誌擔任了五六年的編輯,家裡的工廠則由弟弟接手經營。讀過許多作品的他發現,現在的文學作品不是歌詠農村,就是消費主義的現代書寫,鮮少以工廠為主元素,但是台灣從農業轉變成工業社會的階段,正是由許多工人撐起來的,「這些勞動者的性格多半木訥壓抑、不善表達,很容易被社會忽略,我希望透過文字,讓大家看看這群辛苦的人。」
對小時候的我來說,工廠太忙,爸媽加班都來不及了,更別說旅遊渡假,只有在外出維修時,我才能離開沉悶的工廠,到遠方去,爸爸小貨車能到達的最遠處,就是世界的邊境。——〈貨車〉,《家工廠》
那時,只要父親開著貨車到各處的麵包店修理機器,他就是小跟班,好運的話,還吃得到麵包師傅請的麵包、調味乳,這種「因公」帶來的附加收穫,可以讓他樂很久。「我爸從小的志願就是開一家工廠,自己當老闆。他們的世界很簡單,就是努力賺錢改善貧窮的生活,」他的印象中,一直工作的爸媽賺了錢總是用在長輩、孩子身上,很少自己享受,「我爸一直以為我不認同這個行業,但《家工廠》真的是獻給爸媽的書,也是要向這群工廠裡的師傅、工人們致意。」
現在,他在寫一部辭了職的37歲男子的半自傳小說,並釐清自己20年前的高中生活,預計年底前完成。「高中那段時間是一面鏡子,可以看見自己現在的問題,17歲時總是不斷質疑這個世界,現在則是庸俗地接納所有的東西。」他笑說,「我的中年危機,就是覺得回不去了,尤其是發現自己得靠運動,體重才不會增加之後……」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