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我的書房是
我的秘密聖堂
在此看見幻象
得到安息與力量
──羅智成,《夢中書房》
《夢中書房》上次發表已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如今再出版,詩人羅智成說,「沒想到時間過那麼快,這本書的寫作時間超過10年,現在回顧世紀之交的時候,寫作都帶有道別的感覺,好像那個巨大的時期已經過去。離開這個時間點後,每件事都加速離去,我曾經密切注意的21世紀,現在居然已經離去15年。時間消逝之感一直是我寫作焦慮的來源,但也是動力。」
這種對「時間」的感傷不僅是從個人生命出發,更是因整個以現代主義為代表的世界已成過去而興起的惆悵之情。羅智成提到一個獨特的現象,「華人世界對現代主義很少懷舊,因為我們並沒有整體的經驗,而是跳接過來的,所以也不會有整體經驗逝去的傷感;而日本接受的現代主義就比較完整,所他們有現代主義的懷舊,比如動畫家今敏的城市想像,是對於『現代』都市的懷舊,其中也有紐約、巴黎的城市意象,那並非古代也並非最現代的城市,而是現代城市初始形成之時的面貌,帶有典雅浪漫的氛圍。又如大友克洋的《蒸氣男孩》,工業與器械的意象充斥於動畫中,我稱之為素樸式的機械主義,這也是現代主義很重要的一環,是工業文明中一種機械式的世界觀,它形成龐大華麗的景致與心智狀態。」
《夢中書房》則以比動畫更能展現想像力的詩句,營造了一個華麗而惆悵的世界,引領讀者穿梭於世紀末的慶典、充滿文藝復興氣息的城市,與不斷變化的夢幻書房。「《夢中書房》對現代主義有懷舊的心情,很少人會在20世紀帶著世紀末的感受,因為那時有很多事情發生,譬如網路與數位的發展,讓人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但我卻對於一個現代主義時代的消失感到惆悵,我藉由憑弔自己的20世紀,去憑弔人類的20世紀。不過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後來才有的體會。」
但《夢中書房》在傷逝感懷的惆悵中,仍予人一種樂觀奮進之感,這就像羅智成給人的感覺。這不禁令人好奇,我們所熟悉的現代主義作品與作家,經常是晦澀抑鬱、充滿苦悶,為何他能在哀悼一個時代的消逝之餘,卻仍保持樂觀?「雖然現在有『後現代』,好像現代主義已經陳舊了,但我覺得現代主義的很多面向還是沒有被體驗,特別是在台灣,雖然生活與科技上我們看似與西方同步,但在心智狀態的現代化體驗卻還匱乏,或者說,沒有學習到很完全。」這種文化上的「後進」狀態並非徒留遺憾,它意味著還有許多精緻的文化內涵有待我們去經驗,而這是令人興奮的。羅智成說,「在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發展得比較早,但受現代主義影響的領域不只是文學,還包括科學、美學、建築等。對於西方現代文明在文學之外的表現,我總有一種很豐盛的感覺,它展現出人類巨大的心智轉變,這是在人類世界從來沒有過的。所以面對現代主義,我總會感到昂揚、振奮。」
羅智成也認為,現代主義並非真的結束,其中許多元素已被保留下來,只是轉換成新的表現型態。詩人看似專注於回顧過往,其實也藉此瞻望未來,「很多人說現在是後現代主義的天下,但我不認為現代主義已被拋棄,我傾向說狹義的現代主義被折衷了。早期的現代主義,如存在主義,是一整套的意識形態,選擇了它好像就代表選擇了某一種美學、哲學乃至於生活上的看法;到了後現代卻並非如此,現代主義已經沒那麼激烈,也沒有包裹式的思維,而是出現碎片化的現象,這意味很多看似不同的觀點都可以共存。」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與羅智成過去的作品相較,《夢中書房》也帶有一種折衷的氣氛。它仍保有知性的內涵與曲折的意象,同時也散發出一種親切甚或日常的情調,讀者彷彿是在住家附近的走巷弄口,注視即將在轉角消逝的舊世紀,這與我們印象中現代主義晦澀緊迫的基調有所差距。「這一方面是我這本書的寫作策略,從某個角度看,《夢中書房》好像與之前的筆調有所不同,不再那麼疏離,不像《夢中書房》對現代主義在知性上做一總結;《夢中邊陲》與《夢中書房》則對時間比較敏感,有一種濃厚的懷舊之情。」
另一方面,對羅智成而言,不論知性或生活,晦澀抑或親切,本來就互不衝突。「在台灣,現代主義被理解成疏離,但在西方並不如此。現代主義的確比較接近根源與本質的討論,我曾講過現代主義的四大基因──重視原創的實驗精神、重視潛意識的發掘、對於存在困境的了解,與象徵主義的使用。它們有一共同特色:看似遠離日常的表達與體驗方式,但事實上,現代主義並非不討論現實也並非遠離生活,而是不想停留在表面上。它根本的出發點是對於日常更加的敏感,帶有探索與批判。」這種抽象、宏觀的俯瞰,與日常的親切感並存的狀態,是閱讀《夢中書房》莫大的趣味。
而將文明的視野與個人生命的細微感受連結在一起的,並非主題,而是形式。羅智成藉由語法形式觸碰更深處的真實,當讀者在《夢中書房》中看到那些曲折卻又精確,親切卻又富有哲思的語句時,它們本身即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所有的文字都是表達思想,我們在思想的過程中尋找語言,在尋找語言的過程中表達思想。對我而言,語法最能真實反映一個人的思想細節與實際狀況,是最有臨場感的表達方式。我們必須尋找一個最能反映自我的語言,我無法接受範本式的現代詩表達方式,所以我在1979年時就說:要為我自己的性格寫我的現代詩。」羅智成說。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也許現代主義最根本的精神,即是對於人類的內在自我有更複雜的估計,這迫使藝術家運用更複雜的方式去掌握它。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曾歸納現代主義的兩大特徵:關注形式與趨向內心,並論述二者如何互相影響。羅智成的詩也有這兩種表現,對語法形式的講究,與內在幽微真實的探求不可分割,他說,「我一直希望藉由語言對於情感、記憶、乃至抽象思維的固定化,來對抗時間,因為時間最大的惡意就是忘記,若能透過語言回到那個當下的狀態,就會覺得很過癮,好像隨時隨地都帶著更完整的自己,出現在生命中的每一刻;但因過去的情緒被攪動起來,也會覺得感傷。」譬如在〈夢中厝〉中,羅智成所描寫並非完全真實的場景,但是它卻可能更為真實,牽動著深層的記憶。他形容這狀態像夢,《夢中書房》正是依照夢的法則來捕捉真實。「我們常夢到以前的事,竟然會像當時一樣快樂或哭泣,所以夢不見得是假的,夢也可能更真實。我在發掘夢在本體論上的合法地位。」
在這個意義上,「夢中書房」正是此一「夢的法則」最具象化的展現,羅智成甚至計劃在未來實際蓋出這間書房。他興奮地說,「書房會有很多書,充滿各種奇想與收藏,還有複雜多層的結構。」讀者或許會期待進入那個地方,但羅智成更想邀請每一位讀者,開始建立自己的夢中書房。人雖是孤獨的個體,但我們能分享彼此的心靈,甚至宏觀的觀察與探索一個文明,乃至建立自己的本體,這是現代主義最美麗的信念,也是《夢中書房》帶給讀者最珍貴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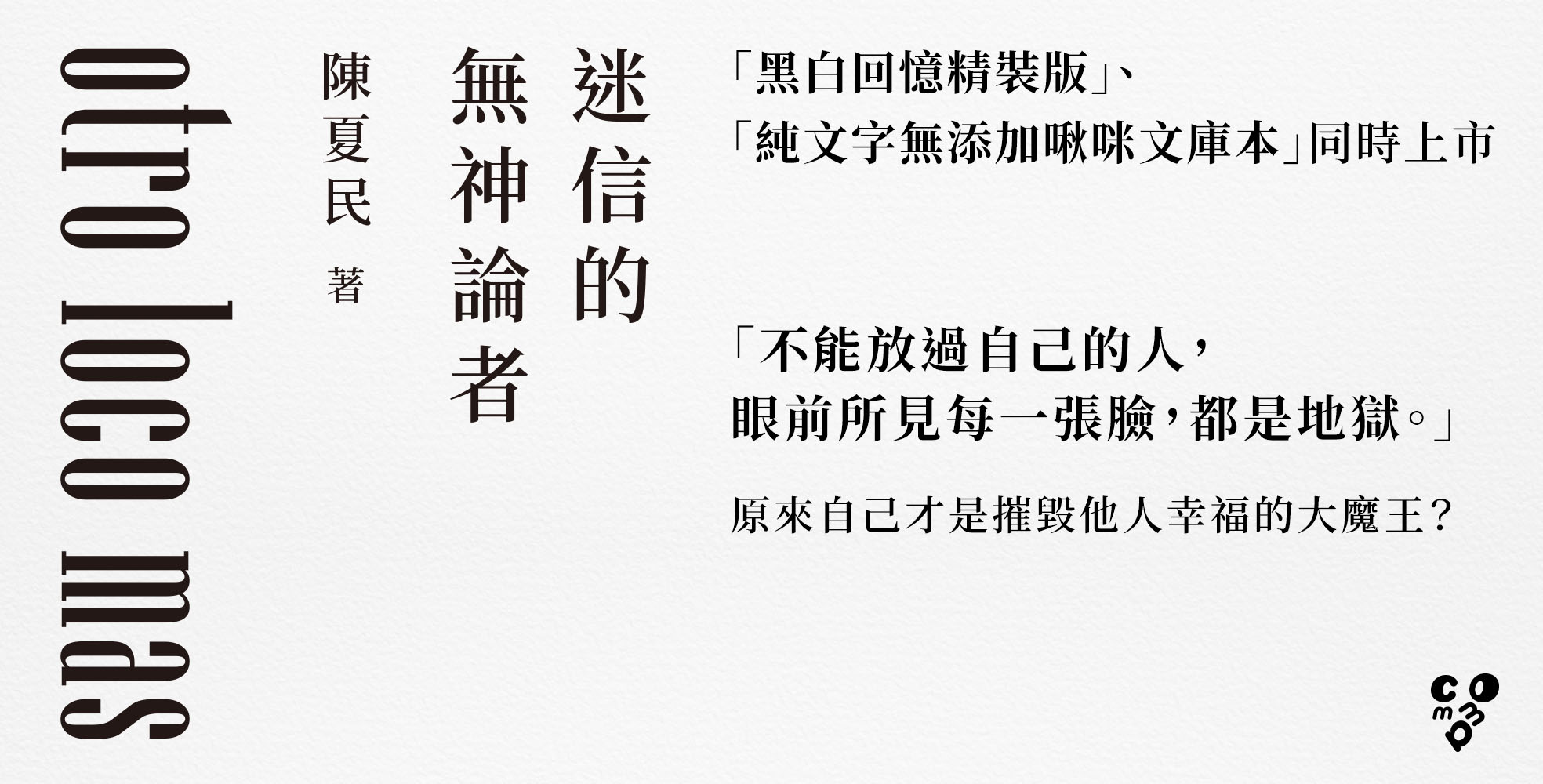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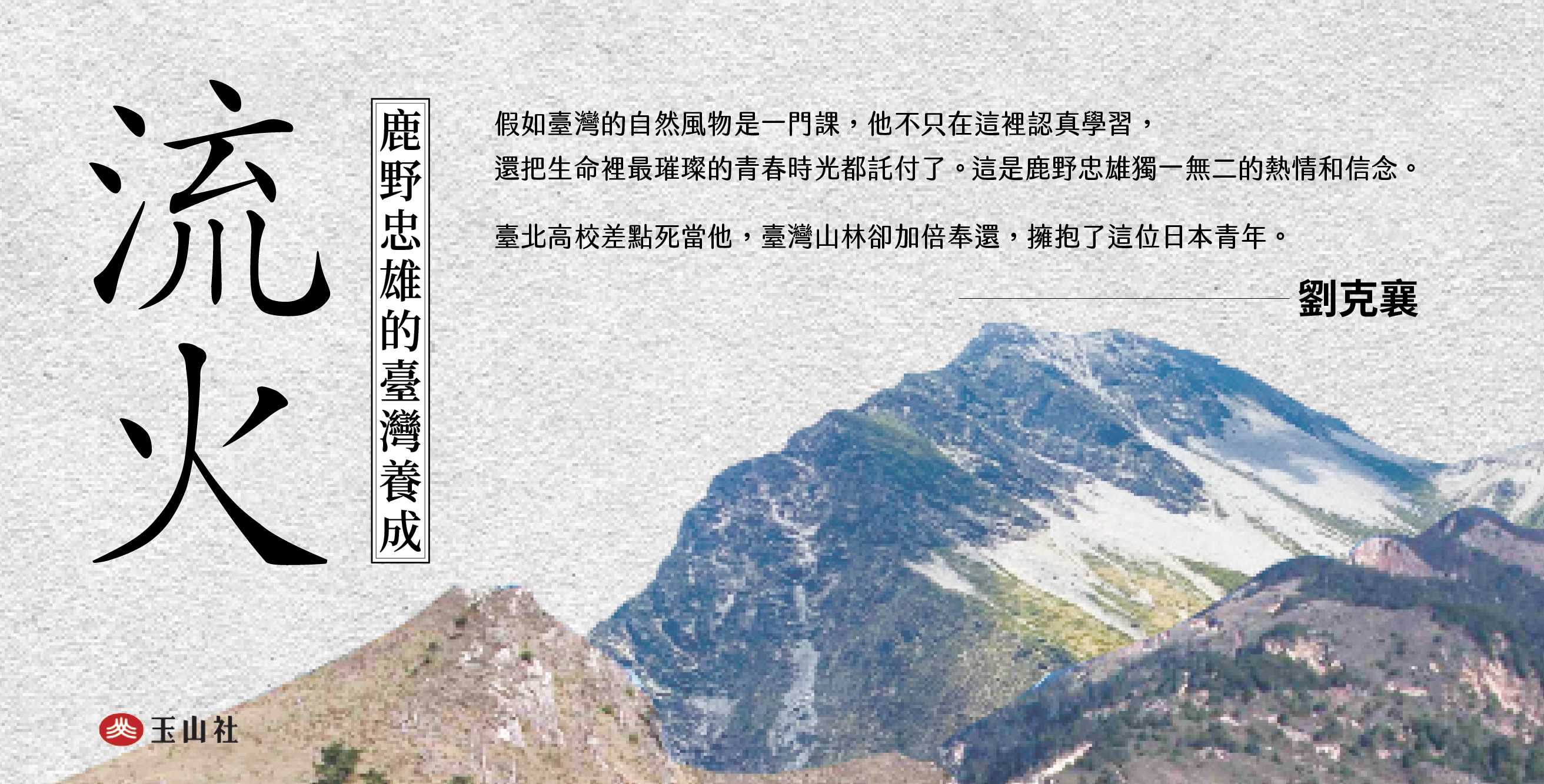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