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參加一個環保團體的志工培訓課程。在一切開始之前,我們被要求給自己起一個自然名。穿山甲、石龍子、桫羅、葎草……人人唱出一個物種的名字,彷彿同時把自己嵌進一個群體、一片棲地。儘管仍穿戴人類的形體,名字領我們跨出城市的人際,共謀一種新的生態關係。
我的自然名不是任何物種。我叫自己「森林」。納入前面所有的名字,我想成為一個收容萬有生命的集合體。這是一個貪心的自許,當下也絕對不可能自問:森林起於何時?邊際何處?要收容多少種生命才足以成為森林?
閱讀《魔法森林》時,我再次想起自己曾叫做森林。離開環保團體後,無人再喚我的自然名,但我依然用它標記網站頁面,執著於當個沒用的森林。許多人問我:森林怎麼可能沒用?我每每給出不同說法,但沒有一個逼近內心真正想說的所有。讀完《魔法森林》後,發現有人已道盡一切可能的答案。
*
《魔法森林》是美國作家博利亞.薩克斯(Boria Sax)甫於2023年12月出版的作品,也是他在台灣發行的第二本譯作。年輕時主修知識史和德語的他,長年浸淫在世界神話和民間傳說的研究領域,並以人類與動物關係的寫作聞名,稍早翻譯出版的《神獸、怪物與人類:想像的極致,反映人心與社會價值的幻想動物》,則是書寫對象從存在於現實的動物探向想像動物的代表作。
延續他鎔學術與抒情於一爐的寫作風格,《魔法森林》把視野拓展到過去被視為動物棲息背景的植物與森林,卻不拘於薩克斯原本擅長的文學、思想史、民俗學等視角,而是更廣泛地從哲學、宗教、政治、生物學、植物學、環境科學等面向,鋪天蓋地探進森林之中,展開一趟宏大博覽的森林文化史巡遊,也因此在近年國內的自然主題出版品中,形成一道卓然特出的風景——若用薩克斯自己的話比擬,就是標記迪士尼樂園城堡的那座高聳拔尖的塔樓。
*
坦白說,《魔法森林》並不好讀,至少一開始並不容易上手。就像前往一座網路上毫無GPX紀錄的山林祕境,你只能老老實實尋索芒草叢生遮蔽的步徑,耐心揮刀砍草,一邊祈禱自己不要在此迷失個把鐘頭。面對以西方世界為主的森林文化史,自言「史詩問題需以史詩規模來思考」且銳意展開今人奢言的「宏大敘事」,薩克斯的策略是從一棵樹和它的葉子談起。
倘若你也嫻熟閱讀近年的自然出版品如《尋找母樹》、《真菌微宇宙》等,或許不會對開篇「一棵樹的個體邊界何在」感到陌生。事實上,森林也揭示同樣對「人類中心主義」式思考的質疑:那些標的我之為一個「個體」的定義,或許無法適用於樹和森林之上。我們如何計算一棵樹的起始?是以人類肉眼可見的樹身為界,還是該把看不見的地下根系算進去?這些根系又如何牽動森林的物種個體生命?
從質疑物種個體和分類展開旅程起點,薩克斯接著從他拿手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裡的林中植物,為讀者揭櫫上古時代存在於人類心靈世界的「物我不分」如何萌芽、棲身於森林之中。舉凡人類從樹而生、與樹成婚、動植物與人類混種變形、或者人樹彼此互為血肉交換的替身,還有居住在森林中的樹精、野人、山怪、幽靈等超自然生物……這些混種雜交、蒙昧難辨的物我關係恆存在於人類集體心靈的幽暗森林中,薩克斯以為,從此關於「森林」的種種概念發明和想像衍生,大抵環繞人們對這闇林的種種投射和反映而來。
那或許是從狩獵本能到征服整座森林的野心滋長;是對森林投以「處女地」等性別化的想像和描述,以及隨之而來的另一種征服和開發慾望;是美國讚揚、發明伐木工人保羅.班楊的荒誕傳說時,悄悄把森林的美感與靈性置換成大量砍伐的驚人業績;是納粹挾持森林的詮釋權,將森林之力挪來與自己的統治權力畫上等號;是為殖民地森林重新命名為「叢林」,並創造一個盪著藤蔓的孔武有力白面孔「泰山」,讓他的野性蠻力覆蓋於森林的萬物生命之上。
「森林披露了我們對大自然的多重看法,從感到驚恐害怕到視為美麗的田野風光,不一而足。我們帶著強烈的恐懼與渴望看待森林,一邊摧毀森林,卻又同時將其奉為神靈。」薩克斯寫出了人類面對重重景深、鬱閉不明、生死交揉的森林時,同樣複雜交錯的感知與行動。森林最終成了祭品,無論是觀念或實質皆然。
*
儘管前面所引述的例子,多是薩克斯穿梭不同年代的歷史、軼事、神話、傳說,以認識論或修辭學解析森林在人類文化中的演化或突變,然而他也並未錯過當前森林環境的嚴峻議題。一方面在書中和德國護林作家彼得.沃雷本、蘇珊.希瑪爾、乃至小說作品《樹冠上》等新近作品對話,薩克斯同時也以自己擁有、管理的家族林地為例,談及國內外皆熱議的林下經濟、碳封存、氣候變遷與森林管護等現象和問題。
事實上,人類的感知經驗難以逼近一座森林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為穩定氣候所做的各種努力。薩克斯描述,我們對森林的這類覺察和想像,事實上也是一種神話。於是,當《魔法森林》最後再度回到人類如何重構對森林的認識和關係時,他的主張是:我們應當放棄線性的時間觀,試著貼近森林的時間敘事。
在森林裡,死生往往交錯相生,看似線性的終點並不意味死亡的永恆靜止。同時,我們或許也當放棄以「原始」、「純淨」的概念看待森林。「原始林」除了引起人類對原初的懷舊嚮往,也會喚醒前往開發征伐的慾望。然而森林並不是一種文化的過去式。它不是折射我們想像的客體,而是會感知、會思考、會孵育夢的有機存在。當人類走進森林,我們或許也成了它的折射,是它發出的一陣自言自語。
當人類試著逼近森林的視角換位思考,他或許不會對砍樹懷有太大的戒懼。薩克斯在書末提及他幾經思量後伐除林地上一棵巨大山毛櫸的經過。光禿禿的樹頭雖然令人神傷,但冬天過去,泥地上重新長出許久不見的青草,伐木留下的坑洞也蓄滿水、孕育不少蝌蚪。這甚至不是一個森林角落的快樂結局,僅是一個小小的逗號,薩克斯給出的提議是:面對森林,人類與其成為一支軍隊(無論出發點是護衛或征戰),我們必須更像一片森林。
以森林呼喚我,也以森林呼喚你自己。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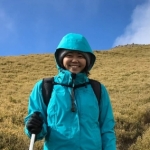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