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個影像源源不絕、不斷衍生,處處叨絮的時代裡,
一張「沒拍到」或「沒能拍下」的照片,
或許不只是一種缺席,
一框空白底片格,
或許更接近一種珍貴的沉默──
而在那沉默之中,或許反而更讓人貼近「攝影」的本質。
我們將邀請五位原本以影像為語言的攝影師,
在這裡以文字留下他們沒拍到/沒能拍下的照片,與那珍貴的沉默瞬間。

〔攝影師|O2〕鐘聖雄 /
1979年生,彰化縣溪州鄉人。曾任莫拉克獨立新聞網、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特約記者,現在游手好閒。
曾以作品《南風》獲2012年卓越新聞獎系列攝影獎,作品《血淚都更》獲2011年城市人權新聞獎。作品《舟曲報告》亦入圍2011年卓越新聞獎國際報導獎。
有時,用「心」紀錄是更重要的事
初學攝影時正值樂生保留運動高峰,要說我大部分攝影技巧都是在街頭抗爭磨練出來,亦不為過。初學者總迷戀快門聲響,或因轉動對焦環時,各色人事物在對焦屏漸地清晰沉醉,所以我在那時期拍得很勤,相機幾乎沒離過身邊。
在當時,樂生療養院處於隨時會被拆除的狀態,所以即便不上街頭的時刻,我在院區也總抱著「不再相見」的心情,盡可能詳細拍下這座見證台灣漢生病隔離史的病院,期盼自己的照片「見證歷史」。是的,這四個字對攝影人來說,彷彿是種催情藥,在激勵精進攝影技巧的同時,也讓拿著相機的自我膨脹許多,過度放大自己的重要性,也捨不得任何可以放下相機的時刻。
私下拍攝樂生院民時,我以為自己克制得多,尚能掐住分寸,明白那些人與人情感交流的時刻,不該受到快門聲的干擾;或許我也有逾矩的時候,但我相信阿公阿嬤們對我相當寬容。與拍攝院民相對之下,更難拿捏的,其實是上街抗爭時,決定何時要拍攝伙伴,何時又該放下相機,與他們並肩站在一起。
2006年7月11日,樂生院民與聲援者們前往當時的台北縣政府陳情,要求政府承諾不強制驅離院民,卻遭到政府代表斷然拒絕。當天,有人朝縣政府丟了顆雞蛋,引發警察大動作暴力驅離;在我的印象裡,這是樂生抗爭中,第一次遇到真正的肢體暴力衝突,或許也是日後街頭衝突越演越烈的導火線之一。許多人在那次的驅離行動中受了傷,還有十多名聲援者、組織者被警察逮捕上警備車,準備送往警局拘留。最終,樂青有兩名成員一直被拘留到深夜才獲釋,同時還得面對被起訴的命運。
我在當年的樂生抗爭行動中,扮演的多是攝影的角色。只要你有一台看起來像樣,同時又架上機頂閃燈的單眼相機,很容易就被警察視為(職業)記者的身分,我因此免卻非常多皮肉傷,警察也不認為他們應該逮捕我。但,相信我,這一切並不好受。即便我可以將身體躲在觀景窗後,因著相機的掩護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但我的心情卻極度地難受。
透過觀景窗拍攝你所熟悉、關愛的人一個個被警察擒拿、拖行、扭打、逮捕,本身就已是非常痛苦的事,更無奈的是,相機彷彿劃下了一條無形的線,將我與伙伴們區分為不同的群體,切割了關係。於是,當他們聊起受創經驗時,我插不了嘴,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我有和他們「共患難」的經歷。
更有甚者,有朋友會質疑我,為何當他被警察攻擊時,我卻只顧著按快門而不伸出援手,加入他的戰線和他一起抵抗。我聽著這些指責只覺得很無奈,因為我明白在那當下,我出手不只對事情沒有幫助,還會讓我們事後想指責國家暴力時變得困難重重,因為我們沒了控訴暴力的證據和素材。
當天下午,當多數的樂青重要成員遭逮捕拘留時,我和一些倖存的人正著手準備召開記者會,而我所拍攝的現場衝突照片,則成為控訴國家暴力的重要證據。當我拍攝的照片出現在記者會現場時,老實說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成就感,只覺得寂寞。
印象中只覺得那天超級累。身體還沒有從前一天籌備的疲累中回覆,第二天就開始忙著開記者會、忙著被警察推擠、忙著拍攝伙伴被拖上警備車、忙著躲在觀景窗後掉眼淚、忙著不被最親近的人諒解、忙著收拾殘局後又得重新準備召開記者會、忙著和許多有運動傷害的人溝通……就這樣,一直到了深夜,兩名被起訴、拘留的同伴終於要被釋放了。
我和幾名同伴拖著非常疲憊的身子,從台大附近的辦公室一路騎車到板橋地檢署,到現場等沒多久,終於在深夜昏黃的燈光下,等到兩名「久別」的伙伴走了出來。當時去地檢署接人的同伴中,有一位和被捕的同伴是戀人。兩名歷劫重逢的戀人,就這麼背著昏黃的燈光落淚、緊緊相擁,身邊的伙伴們一個個也只能像剪影一樣沉默感傷。
對於一名想要完整紀錄樂生保留運動的人來說,此刻的畫面戲劇性再好不過。拍攝暴力仍不足夠,一個完整的故事,應當記下暴力的後遺症與回復的過程才算數。坦白說,我那一刻仍閃過拍照的念頭,不只是因為畫面的完美,也因為那一刻在整個時間軸中的重要性。
回程尋找豬腳麵線攤的路上,我把自己那一刻所感受的焦慮,說給另一名同伴聽,因為我覺得他也是攝影愛好者,應該可以明白這樣的感受。當時他告訴我說:「我剛剛也在想那個畫面挺好的,但同時間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如果這時候阿雄把相機掏出來拍照的話,我一定要砸爛那台相機,然後把他的手給剁掉!」
在那之後過了幾年,我成了一名職業的新聞工作者。幾年間我走過天災人禍與不少傷心地,也看著一齣齣悲劇在眼前上演,一個個傷心欲絕的人在鏡頭前倒下。隨著作品累積越來越多,我無法按下快門的時刻其實也越來越多。我經常想起Don McCullin說,每天半夜有幽魂會從他底片櫃跑出來的事情,也經常懷疑Robert Capa、Larry Burrows、James Nachtwey這些傑出的戰地攝影師們,如何有辦法在那麼多痛苦的人面前舉起相機對焦。
樂生的事情,並非我第一次無法按下快門,甚至無法掏出相機的時刻,要說更心碎的時刻,太多了,但那個畫面與那個時刻太重要了,深深地揪在我的心上。那位伙伴的話讓我明白,即便身為一名記錄者,我也不是無時無刻都非得用相機記錄不可。攝影者沒那麼了不起,有些時候用心紀錄是更為重要的事情;而那關乎感受,關乎鏡頭兩端的關係。
隨著「缺席的照片」累積越來越多,我同時也留下更多「後悔的照片」。拍與不拍之間,大多數時候絕不是跟工作、跟新聞交代那麼簡單。如何跟自己交代、跟被攝者交代,才是身為一名攝影者終生的課題。
但這件事情,我相信不管怎麼討論都不會有結果,這本書裡所收錄的故事,包括我方才說的,對正在讀這些文字的你也未必會有多少意義。除非,有一天你能深刻瞭解,自己所拍攝的愛與悲傷,從來也不是別人的、更抽象的、更巨大的、更有意義的愛與悲傷,如同電影《一千次晚安》中,主角最後所領會的那樣。你的攝影作品,從來就是你自己的顯影結果。
Doug Dubois說得很真實。他寫道:「在我們的工作中,把相機放下其實跟舉起相機一樣困難。就算我試著保持道德與誠實來理解攝影究竟意味著什麼,一旦對比照片意味著的意義,我仍曾經有過、且持續可能繼續發生這種在『慎重』與『得體』上的偶然失誤。」
換言之,攝影是一門必須學會處理遺憾的工作。
延伸閱讀|獻給故鄉,獻給邊陲之人──鐘聖雄、許震唐《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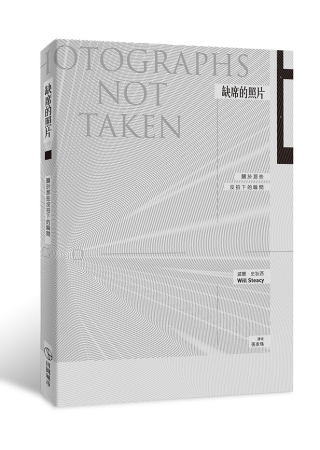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