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世芳的新作《耳朵借我》《歌物件》,集結他近年的專欄文章,寫的是歌,是人,也是嘹亮的時代。
《耳朵借我》是馬世芳第一本聚焦「中文世界」的音樂文集,問及接觸華語音樂及西洋音樂的先後,他沉吟了片刻才笑答,「若要追本溯源,恐怕得回到我娘胎時期。」他的母親陶曉清被譽為「民歌之母」,乃民歌時代的重要推手,當年她挺著大肚子去做廣播,於節目中引介西洋流行音樂,是以馬世芳未出世前應當就聽了不少搖滾樂。據他回憶,能追溯到最早的印象,是聽他母親彈吉他唱蘇州彈詞,唱〈黛玉葬花〉〈雲想衣裳花想容〉〈小小羊兒要回家〉等歌謠,也唱嬉皮時代紅極一時的民謠搖滾四重唱「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的作品。他的搖籃曲中,中英文歌皆有,委實難辨先後。
民歌運動肇始於1975年,兩年後,金韻獎開辦,由陶曉清策劃之《我們的歌》合輯隨之出版。那些年,民歌手、音樂人經常出沒他家中,多半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大學生,彼時正值馬世芳小學階段,他跟所有小朋友一樣,共同度過了由這些歌曲繚繞著的童年。「小時候聽那些歌,感情上是很貼近的,我們都很熟啊,〈恰似你的溫柔〉〈月琴〉誰不會唱?〈龍的傳人〉紅得要命時,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歌。」唯獨比其他人占便宜一點的是,他認識這些唱歌的阿姨叔叔。
聽歸聽,小朋友自然不會費心去想歌如何寫就、音樂概念又是怎麼回事,一心只想著玩。馬世芳記得,有一回他拿著一副撲克牌到李建復跟前,打算變魔術給他看,卻頻出差錯,李建復仍極有耐心地等著。他也曾拉著蘇來,一直跟他講《怪博士與機器娃娃》的故事,他同樣很有耐性地聽他娓娓道來。
馬世芳自認音樂啟蒙很晚,舉凡西洋搖滾名團,常是十三、四歲即立志組團,而他則遲至十五、六歲才開始聽西洋流行樂。此前,他瘋迷的是松本零士《宇宙戰艦大和號》《銀河鐵道999》等日本動漫畫主題曲,不僅租錄影帶來看,還拿錄音機將歌曲錄起來,無怪乎他戲稱自己「其實小時候像個動漫阿宅」。
直到升上國三,他對西洋音樂的興致才高漲起來。起初,跟同學一樣,都看Billboard排行榜、看余光主持的音樂節目《閃亮的節奏》,什麼紅就聽什麼。直到有一回,他偶然從母親那兒拿到一卷The Beatles的卡帶,這一聽,便一頭墜入父母輩的搖滾世界而不可自拔。
反而是在迷上搖滾樂之後,又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逐步對台灣歌謠的創作脈絡有了較全盤的理解。
1988年,去國三年的羅大佑自美返台,發行《愛人同志》,那是馬世芳第一卷自己掏錢買下的國語專輯,「當時那張唱片很轟動,是一個文化事件。」他聽後非常喜歡,又找出羅大佑早先的專輯重聽,「我小時候就聽過羅大佑,也滿熟的,如〈亞細亞的孤兒〉〈未來的主人翁〉〈戀曲1980〉,但當年不知其所以然,事隔三、五年,重新溫習他的錄音帶,我已經從一個兒童變成少年,感覺也不一樣了,非常震撼。」高二那年,他重聽〈亞細亞的孤兒〉,忽地發現原來這首歌並非如副標所稱「致中南半島難民」,而是指涉台灣的國族處境,那震撼力之大,猶如「被雷打到」。
「羅大佑跟我們的感情,跟你聽西洋搖滾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也聽羅大佑的情歌,還癡迷地把歌詞抄寫在隨身攜帶的本子上。如此一路往前回溯,溫習李壽全《八又二分之一》、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等專輯,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他們幹的事如此勇猛轟烈。
高中至大學期間,馬世芳一邊瘋狂地追老搖滾,一邊又回頭去聽這些長他五、六歲的世代才熟稔的台灣原生創作,繼而再重溫校園民歌。「聽過Bob Dylan、The Beatles、Neil Young、Judy Collins,再去聽楊弦的第一張專輯及金韻獎早期的那些錄音,感覺會完全不一樣。」原來,楊弦的〈江湖上〉,是向Bob Dylan〈Blowin' in the Wind〉致敬的歌,「原來我們的長輩在1970年代是這樣跟影響他們的創作者對話,他們希望能夠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在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找出屬於自己的線條、自己的語言。」

那幾年,也恰是台灣「後解嚴時代」,壓抑經年的欲力破土而出,社會上瀰漫一片兇猛而富創造性的聲音。「我們好像有一種站在時代的轉折點上,見證一些幾十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的感覺。」抱著這樣的心緒,再去聽前一、兩代的人在面對時代所做出來的作品,自然別有滋味。「每一代的創作人會面對他們各自的焦慮,197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有一種大時代的自覺,那是一個台灣國際處境不斷邊緣化的時代,那是一個國族主義還是主旋律、但鄉土意識愈來愈萌芽的時代,年輕人在思考如何在外來和本土、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東方之間找出自己的定位,他們用各自的創作設法提出解答,有人編雜誌、有人辦劇團、有人創舞團、有人寫小說、有人做音樂、有人拍電影,民歌運動也是在這脈絡底下。」
為之動容的馬世芳,慢慢將過往的圖像拼湊出來,始知小時聽的歌蘊藏何等魅力。作為一個阿宅型樂迷,他也從早先只聽歌手和旋律,進化到聽樂手、錄音、編曲和製作,如此再回去聽自己文化脈絡底下的東西,便有很多新發現。而這些新發現正好又跟他所身處的年代有一些可呼應之處,「後解嚴時代,我們一樣在面對類似的問題,本土文化被壓抑了那麼多年,新台語歌爆炸性地發展起來,原本被認為俗的、庶民的,一夕之間變成最潮的東西、最時尚的設計元素,變成了某種新的政治正確。」
近年,台灣、中國、香港社會抗爭不斷,年輕人倍感焦慮,社會上持續湧動著一股不安、躁動、壓抑的氛圍,這些也都反映在馬世芳的文章裡。
2013年3月9日,日本福島核災兩年後,台灣民間發起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核遊行,高達二十餘萬人走上街頭,馬世芳也在隊伍之中。在他大學時代,人們上街,唱的無非是戰歌型、團結鬥陣型的曲子,但那次上街,他看到兩個二十出頭、清湯掛麵的小清新女生站在宣傳車上,彈著不甚流利的吉他,用不是很好的合聲、努力地唱著吳志寧的〈全心全意愛你〉,稚嫩的聲音透過破爛的喇叭放送出來,他頓時覺得:「哇!時代不一樣了,小清新也可以上街,也許這是他們覺得對的氣味,亦無不可。」
今年,太陽花學運退場後,核四試運轉爭議再起,他在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碰到一群年輕人,儘管不大有人搭理,他們仍擎著親手做的看板,以顯然有練過的二部合聲,彈唱929的〈貢寮你好嗎?〉,那句「我們不要核電廠」襯著悠柔的旋律,聽來無比清新。當時馬世芳趕著辦事,無瑕停下,走至電扶梯時,不知何故,忽然一陣鼻酸,萬分感慨,「每一代有每一代自己的嗓子、自己的口氣,好面對這個時代滾滾而來的各種你受不了的事。」
他至今仍無從知曉何以當下鼻頭一酸。過了片刻,他再一次試圖釐清彼時心中閃現的念頭──「我們如何用抒情的方式去對抗這個國家機器、對抗這個大人世界?」難道,他是憂心以抒情的方式無法真正撼動什麼?馬世芳連忙澄清,「抒情的方式OK,只是那樣的抒情在那個時刻聽來無比悲涼。抒情有抒情的力量,悲歌有悲歌的力量。應該說,那個歌其實滿美的,然而,這種清新的、抒情的、美的聲音,要去對抗的竟是那麼糟糕醜陋的東西,所以特別感覺到彷彿漫漫長夜,看不到路的盡頭,我們好像還是得唱唱歌給自己打氣吧。」
言及至此,那個醉心於搖滾樂的少年,彷彿一夕之間老了,成了惆悵的中年,幸而歌終究還是這樣慢慢唱著。馬世芳自認從不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而,「回歸我自己的角色,我除了是一個公民和鍵盤嘴炮手之外,還可以是一個DJ、一個寫專欄的人,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做一點符合我擅長的事、同時試著把我心裡想的東西再說得清楚一點。」
〔馬世芳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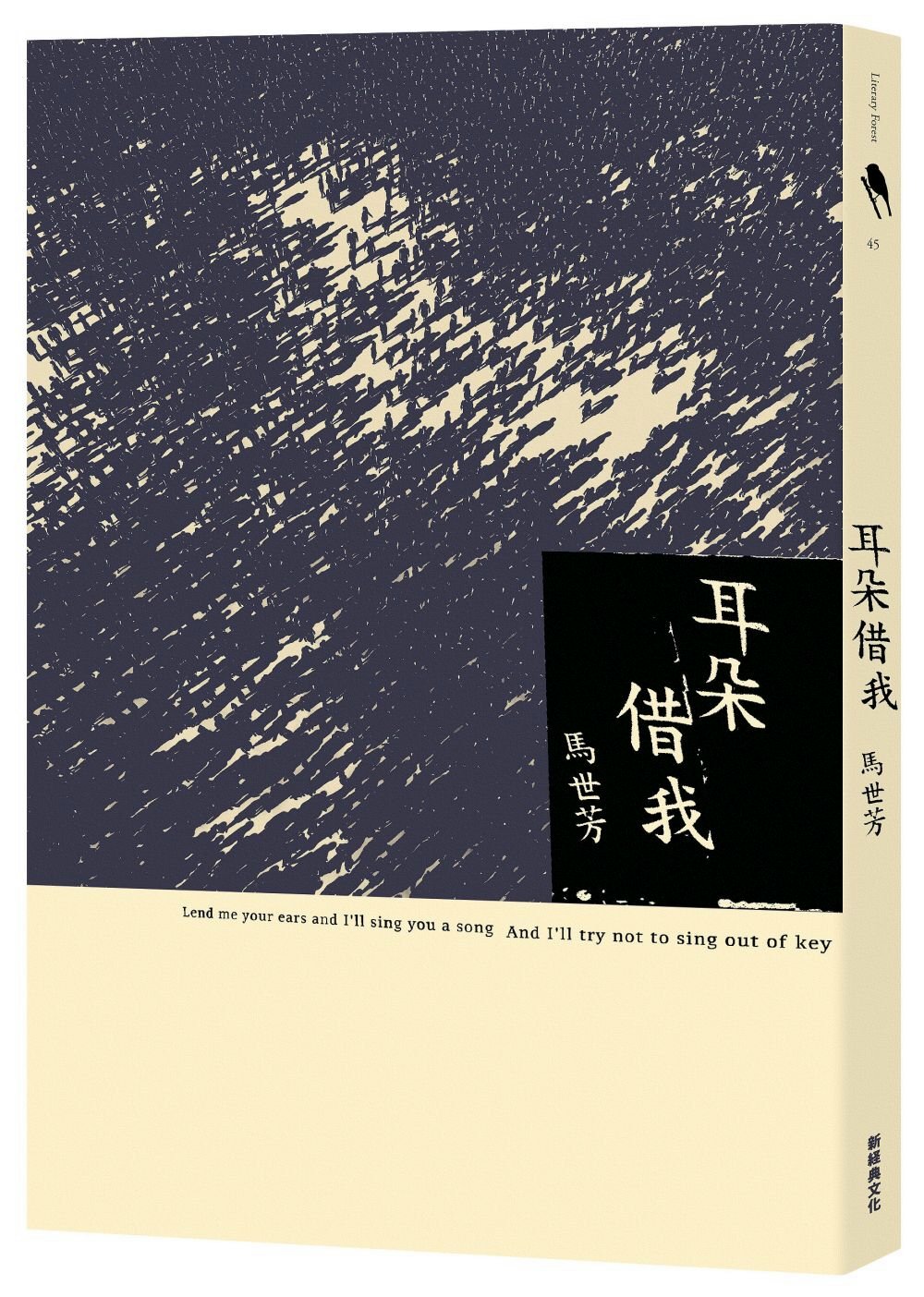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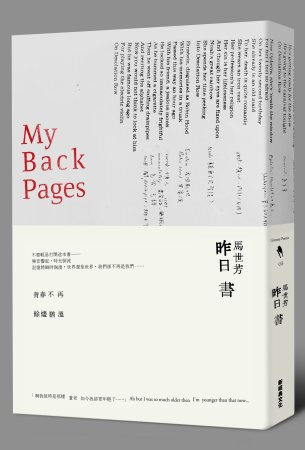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