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算,吉田修一說,他到台灣的次數,已經將近四十次了。
十多年來,平均每年三到四次,才有辦法累積到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旅遊數字。既非公務差旅,也非視親探友,純粹只是喜歡這塊土地,因而一訪再訪。「只要工作有三、四天的空檔,我就會想:『嗯,那去台灣一下好了。』」
面對「你為什麼這麼喜愛台灣」這個總被一問再問的疑惑,吉田修一始終說不上什麼具體的理由。回想自己第一次抵達台灣、步出機場,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受油然而生,至今絲毫未變。「就是莫名有種『這個地方跟我好合喔』的感覺吧。」
如是深刻的契合感,讓這位擅長以寫實細膩的貼切文字,描述都會孤寂生活與尋找自我歸屬的日本作家,在數部叫好叫座的文學作品《同棲生活》、《公園生活》、《惡人》、《再見溪谷》、《橫道世之介》之後,專心致志地寫下一部設定台灣為故事舞台、以興築高鐵為時空背景,串連起台日三個世代情感糾葛的長篇小說《路》。這是他寫給台灣的情書。
若說《路》這部小說與吉田修一以往作品最明顯的差異,該是書中流露出的氣氛較為和緩多情,不若其他的淡漠疏離。
「我想是因為《路》中大部分的角色,都是用溫暖的眼光在看事情。像是來到台灣的安西誠,在遇到Yuki之後,他的想法和看法便出現了變化,與他在日本時不一樣。」其他如對台灣有一定的熟悉與好感的多田春香,或是有著矛盾鄉愁的灣生葉山勝一郎,因著角色們與這塊土地或深或淺的眷戀和懷念,讓《路》顯得人情濃厚許多。以往作品的角色,不是深感寂寞的人,就是多以冷眼看待世界,給人的感覺便相對冷淡。
「而且畢竟是情書嘛,當然要寫得熱情一點。」吉田修一半開玩笑地說。「當然,如果沒有台灣,我也寫不出《路》這本書。」
如同岔路的抉擇導致兩個相異的平行宇宙,吉田修一坦言,有遇見台灣的自己,與沒有遇見台灣的自己,人生必定大相逕庭,不只是有沒有《路》這部作品而已。「如果我沒有遇見台灣,我不會是現在的模樣,在我身邊的也一定不是這些人,對事物的看法也會有所不同。」總是感動於台灣人的親切體貼,吉田修一覺得自己似乎也慢慢受到這樣的潛移默化,變得比過去更加溫和柔軟。「雖然我不是個陰沉悲觀的人,但偶爾還是會有不開心的時候,台灣就是能替我消除這些不愉快,讓我感到自己受到了療癒。」

人們總在故鄉與異鄉之間擺盪,「路」,是「離」與「返」有形無形的串連。吉田修一過往的書寫,著眼於走在尋覓之路上的人們,時而空虛,時而脆弱,如今他以《路》展開一道沉靜堅實的途徑,隱隱呈現出他對「故鄉」定義的轉變。「以前認為,當父母與兄弟姊妹都在的時候,自然就有『故鄉』的感覺;然而一旦家人都不在了,『故鄉』又是什麼呢——」吉田修一沉吟了半晌,「在我寫《路》的時候,我想到的是,雖然我不是書中的葉山勝一郎,但如果在某個地方,有個人對我說:『你可以留在這裡直到死去』,那麼那個地方,就可以算是故鄉了吧。」
「我雖然本來就很熱愛旅行,但從未想過自己會如此喜歡、並經常前往一個日本以外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台灣對我的意義,或許可以說是賺到了吧。」長崎、東京、台灣三地,吉田修一說,那不只是讓他又多了一個能經常往返的地方,還多了一個「在這裡死掉也無所謂」的地方。
「《路》這本書,就是我喜歡台灣的理由。如果要我親口說一次我喜歡台灣的理由,我的答案會是將這本書,從頭到尾朗讀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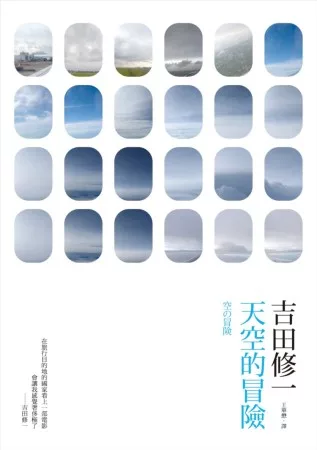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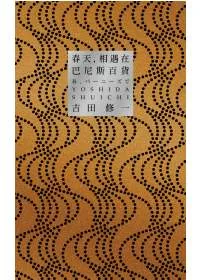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