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臺灣讀者而言,伊朗顯得遙遠,但書中觸及的議題並非與我們無關。我們或許已經習慣與不安共存,但警戒心也悄悄磨損了。《解放之焰》提醒我們,權力如何滲入生活、恐懼又如何被內化,這些我們都該謹記在心。
在以下訪談中,我們會聊他的寫作起點、文學所承擔的倫理與責任,也談他在伊朗相遇的那些人。希望這些對話,能讓讀者帶著更銳利、也更溫柔的目光,重新看待這個世界。
Q:《解放之焰》是你在臺灣的第一本書,相信很多讀者會先從你的人生履歷開始認識你。你曾是職業冰球選手,這個經驗有影響你的寫作嗎?你在法國先以小說作品出道,後來的多部小說都獲得重要獎項的肯定,是什麼原因讓你想寫一部非虛構作品,而且還是旅遊文學?
德澤哈布:是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一開始其實是打冰球的。這項運動在臺灣並不算流行,據我所知,你們好像只有一座冰球場?我並不是因為當過冰球選手才成為作家,也不是為了當作家才放棄冰球。那是兩段同時存在過、後來各自分開的人生,但彼此都留下了痕跡。
冰球場沒有教我怎麼寫句子,但它教會我怎麼忍受沉默、付出努力、面對自我懷疑。當運動員,你會反覆練習,學到紀律、耐心,也學會與疼痛和挫折共處;失敗永遠比成功多,但你還是得繼續下去。老實說,寫作也差不多是這樣。
 圖片來源/作者Instagram
圖片來源/作者Instagram
至於從小說轉向非虛構寫作,我不太覺得那是「轉行」,比較像是把視野放得更大。到某個階段,我開始想拿掉最後一層虛構,直接面對這個世界,不再躲在故事後面。旅遊文學正好滿足了這個需求。它是一種很有交會感的寫作形式:你走路、觀察、閱讀、思考、回憶;你既置身其中,又稍微站在旁邊看著自己。
《解放之焰》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寫成的。我想用世界原本的樣子來考驗自己,而不是寫出一個我想像中的世界。
就像旅行作家尼可拉.布維耶說過的:「人會想啟程遠行,往往是因為在十歲到十三歲之間,趴在地毯上,靜靜翻看著地圖集的那些時刻。」
Q:本書一開頭提到,法國外交部打電話勸你不要去伊朗,因為那裡已經被列為警戒區,但你已經在飛機上了,正準備起飛。為何選擇伊朗?是什麼動力讓你不顧危險仍要啟程?
德澤哈布:我很年輕時就讀了尼可拉.布維耶的《世界之用》,那本書對我影響非常深。它不是那種你會一字一句模仿的作品,而更像是一條地平線,指出一個方向。很多年來,我一直有個念頭:想重新走一段他走過的路。不是出於懷舊,而是想看看時間、歷史和政治,究竟把那些風景、那些社會變成了什麼模樣。重返文學走過的地方,測量時間留下的距離。
伊朗本身,其實就是人類最偉大的文明之一。那是一種延續數千年的文化,歷史層層疊疊,有帝國、詩歌、科學,也有革命。把這樣一個國家簡化成一個政權,或只是當下的外交衝突,對我來說一直是一種思想與道德上的怠惰。我想看的不是一個抽象的「伊朗」,而是一個真實被人們生活著的地方。
另外,還有那個「當下的時刻」。我在伊朗旅行時,剛好遇上當地人民開始起身行動的時期,某些東西正在移動、鬆動、震盪。我想看到一個正在變動中的人民,不是從遠處,不是透過螢幕或官方聲明,而是真正站在現場。對我來說,旅行正是這件事:走進那些不確定、尚未完成、還沒有答案的地方。不是為了扮演英雄,而是去承認——如果文學想對這個世界說出一些真實的話,就不應該永遠待在安全的地方。
Q:你在書中多次提到尼可拉.布維耶的《世界之用》,甚至去日內瓦見了布維耶的么子曼努埃爾(Manuel)。臺灣直到2023年才正式引進《世界之用》,宣傳文案寫著:「歐洲人人必讀的經典遊記」。你在人生不同階段讀《世界之用》,各有什麼體會?《解放之焰》與《世界之用》之間有什麼共同的精神?
德澤哈布:大約在25歲左右讀到布維耶,對我來說幾乎是一場爆炸;是我作為一個讀者,人生中少數幾次的強烈震動。一方面真正看清世界有多大,一方面也感受到世界的脈動。你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有多麼廣闊、多麼壯麗,也多麼殘酷——而你其實只看過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從那一刻開始,沒有任何一個字比「旅行」更美、更讓人著迷。你腦中只剩下一個念頭:上路吧。但很快,反而是那條路抓住了你、帶走了你。三個月、六個月、十個月之後,它又把你丟回一種定居的生活,而你必須學著與那樣的生活共處。時間飛快流逝,青春慢慢退場,你的背包在櫃子深處積滿灰塵。直到某一天,你再次出發。也正是在路上,你為自己定下了一條此後不再偏離的人生原則:把一半的日子用來觀看這個世界,另一半則用來書寫它。
作為一名作家,多次重讀《世界之用》,最打動我的其實是它的倫理觀。那本書不是在談征服什麼地方,也不是在蒐集經驗,而是在談專注、節制,以及把自己從中心位置移開。布維耶從不把自己放在高於他所描述的事物之上;相反地,他試著讓自己稍微消失一點,好讓世界自己說話。這或許是最困難的一課。
如果說《世界之用》是在談如何「住進」這個世界,那麼《解放之焰》問的則是:當這個世界本身看起來已經疲憊、出現裂痕,被歷史、意識形態與暴力磨損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書並不是一種懷舊式的致敬,而是一場跨越時間的對話。也許是同一條路,但天空已經不同了。
Q:你曾在印度的一個文學節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交流,還稱自己是她的「保鑣」,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安妮・艾諾的作品對你有什麼意義?如果你可以帶安妮・艾諾去旅行,你們會去哪裡?
德澤哈布:有一次我們受邀去印度,參加德里的文學節。那是在她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現場的印度讀者全都蜂擁而上,急著想要她的簽名。有好幾次,我不得不直接站到她和人群中間,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大家,等於臨時充當起「人肉盾牌」,保護我們的國家級文化資產。也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在履歷上多加一行:「安妮・艾諾的貼身保鑣」。
她是法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年輕時也大量閱讀她的作品。說她直接形塑了我的寫作風格並不完全準確,但她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她那種對不正義毫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如果要我帶她去旅行?嗯,為什麼不是臺灣呢?只要你們邀請,我們就會來。
 圖片來源/作者Instagram
圖片來源/作者Instagram
Q:你覺得旅遊文學的作者,對於被書寫的當地人民,是否背負某種責任?你會為你的旅遊書寫設定倫理標準嗎?什麼可以寫,什麼不該寫?在極權國家旅行,這樣的標準會有變化嗎?
德澤哈布:是的,我確實相信寫作是有責任的——但我也很警惕,不想把文學變成一張道德檢查表。對我來說,旅行書寫者最基本的責任,不是替別人說話,而是不要蓋過他們的聲音。你只是短暫走進別人的人生、別人的國家、別人的歷史,光是這一點,就應該讓你保持謙遜。真正的危險,永遠在於把仍然活生生的現實,轉化成風景、象徵,或只為你自己的故事服務。
對我而言,倫理的界線,從「專注」和「精準」開始。你必須非常小心你所描述的事物,而在你試圖解讀、詮釋它們時,更要加倍謹慎。旅行書寫者並沒有獲得任何授權。他不是法官,不是發言人,也不是救世主。他的正當性本來就是脆弱、暫時的,而且應該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每當我寫到我遇見的人時,我都會問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是在幫助讀者更理解這個世界,還是只是拿這些人來裝飾我的文字?
在極權國家裡,這些問題會變得更加尖銳。因為在那裡,寫作從來不只是寫作。文字可能帶來的後果,往往遠超出書頁本身,尤其是對那些無法像你一樣離開的人而言。在這種情況下,作家的自由本身就是不對稱的:你可以出版、可以離開,但你遇見的人,可能要承擔後果。這迫使你必須自我節制——保護身分、避免不必要的曝光,謹慎選擇你的角度,確保你寫下的內容,不會讓那些願意對你開口說話就已經承擔風險的人,陷入更危險的處境。
Q:你在書中紀錄了許多人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誰?你從這個人身上看到什麼?這趟伊朗之行遇到的人,如何更新你對伊朗的想法?
德澤哈布:也許有一個相遇,會蓋過其他所有的相遇。她叫菲如澤(Firouzeh)。我是在伊斯法罕(Isfahan)上方的索菲山(mont Soffeh)遇見她的。一開始,我們只是閒聊日常,然後,她很平靜地對我說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她說,她不害怕死亡,她害怕的是坐牢。而且,她正在為此做準備。
我問她,怎麼準備?
她說:背詩。
一首又一首,幾十首,甚至上百首。她告訴我,如果有一天她被逮捕,他們可以把她關起來,把她塞進一間擠滿人的牢房,或是單獨囚禁,不給她睡、不給她吃,羞辱她、毆打她、強暴她——一切都有可能。但有一樣東西,他們永遠拿不走。那是一樣很小的東西,幾乎微不足道:她藏在身體裡的詩。那些在她心中默誦的詩句,陪她等待死亡,也或許是自由。
當你從一個年輕女子的口中聽到這樣的話(一個比你年輕,卻勇敢無數倍的人),而你又是一名作家時,你很快會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麼。你不美化,也不解釋。你只是作證。你成為那份勇氣的書記官,很單純地把它寫下來,讓它不至於消失。
所謂的「伊朗」,並不只是制度、壓迫,或那些掛在嘴邊的口號。它同時也是這種看不見的內在抵抗——在那樣強烈而私密的空間裡,文化、詩歌與記憶,成了人們得以活下去的工具。
 書中照片,作者攝於伊斯法罕。
書中照片,作者攝於伊斯法罕。
Q:如果有讀者因為你的書,開始關心伊朗的人權問題,你希望他們記住什麼?你認為這個世界需要什麼樣的「下一步」?
德澤哈布:我希望讀者首先記住一件事:人權不是一個抽象的檔案,不是一排數字,也不是外交語言裡的一種公式。人權是被活出來的,是每天在身體裡發生的。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張臉、一個聲音、一具可能被監禁、毆打、噤聲的身體。如果這本書能做到任何一件事,我希望它能阻止讀者只用地緣政治、制裁或口號來理解伊朗。因為一個國家在成為政權之前,首先是由人組成的。
我也希望他們能記住那種勇氣。不是那種看起來很壯烈、很適合出現在演說裡的勇氣,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安靜而固執的勇氣。
至於所謂的「下一步」,這個世界並不需要再多一堂課、再多一種道德姿態,也不需要那種隨著新聞週期來了又走、選擇性的憤怒。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致性,還有記憶。而或許最謙遜、卻也最必要的一步,其實很簡單:實際去聆聽與閱讀。文學無法改變一個政權,但它可以改變我們看待生活在那個政權之下的人們的方式。而有時候,責任正是從這樣一次視角的轉變開始的。
Q:很多人對旅行上癮,旅行快結束時就開始計畫下一次旅行,你也是這樣嗎?旅行結束後,你會感到失落嗎?你如何處理旅行結束後的情緒?
德澤哈布:最美的旅程,永遠是那一趟還沒出發的旅程。不過話說回來,我從來不相信「永遠離開」這件事。我對那種「遠方一定更好、更純粹、更強烈」的想法,其實抱持懷疑,尤其是當你住在法國時——借用我朋友席爾萬.泰松(Sylvain Tesson)的一句話:「身在天堂,卻自認在地獄。」
是的,旅程結束時,往往會伴隨一種失落感。有時只是淡淡的哀傷,有時則更尖銳一些。你離開了那些再也無法重逢的面孔、那些沒有你仍繼續存在的地方,還有那些只在彼時彼地存在過的自己。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稱之為「被中斷的共鳴所帶來的苦澀」,而我更願意叫它「一首未完成之歌的悲傷」。
回到家,常常會讓人感覺世界突然縮小了。一切看起來更小、更慢,也更可預期。但慢慢地,生活又會重新接手。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一趟旅行,沒有讓你帶著更銳利的眼睛、更多一點的專注回到日常生活,那麼這趟旅行其實是失敗的。
 書中照片,作者攝於盧特沙漠。
書中照片,作者攝於盧特沙漠。
Q:你在書中說「用一半的人生看世界,一半的人生書寫它」。目前你有重新調整這兩者的比例嗎?
德澤哈布:以2025 年來看,答案是肯定的。這是十年以來第一次,我幾乎每天都把屁股釘在辦公椅上,趕著完成那本我已經寫了五年的小說。不過到了2026年,我就會再度上路。
Q:你對亞洲與臺灣有什麼印象?你如此熱愛旅行,未來是否計畫來亞洲,並寫一本書?訪問最後,我們誠摯歡迎你來臺灣,相信你會得到很不同的體驗(首先會被餵飽)。
德澤哈布:我得先坦白一件事:我對東亞其實不太熟,而且我從來沒有去過臺灣。不過,是的,我非常想去。至於「一定會被好好招待、吃得很好」這件事,我可是非常認真地看待(笑)。畢竟,食物是最直接的一種待客之道,而一個國家,往往也是從餐桌上開始對你說話。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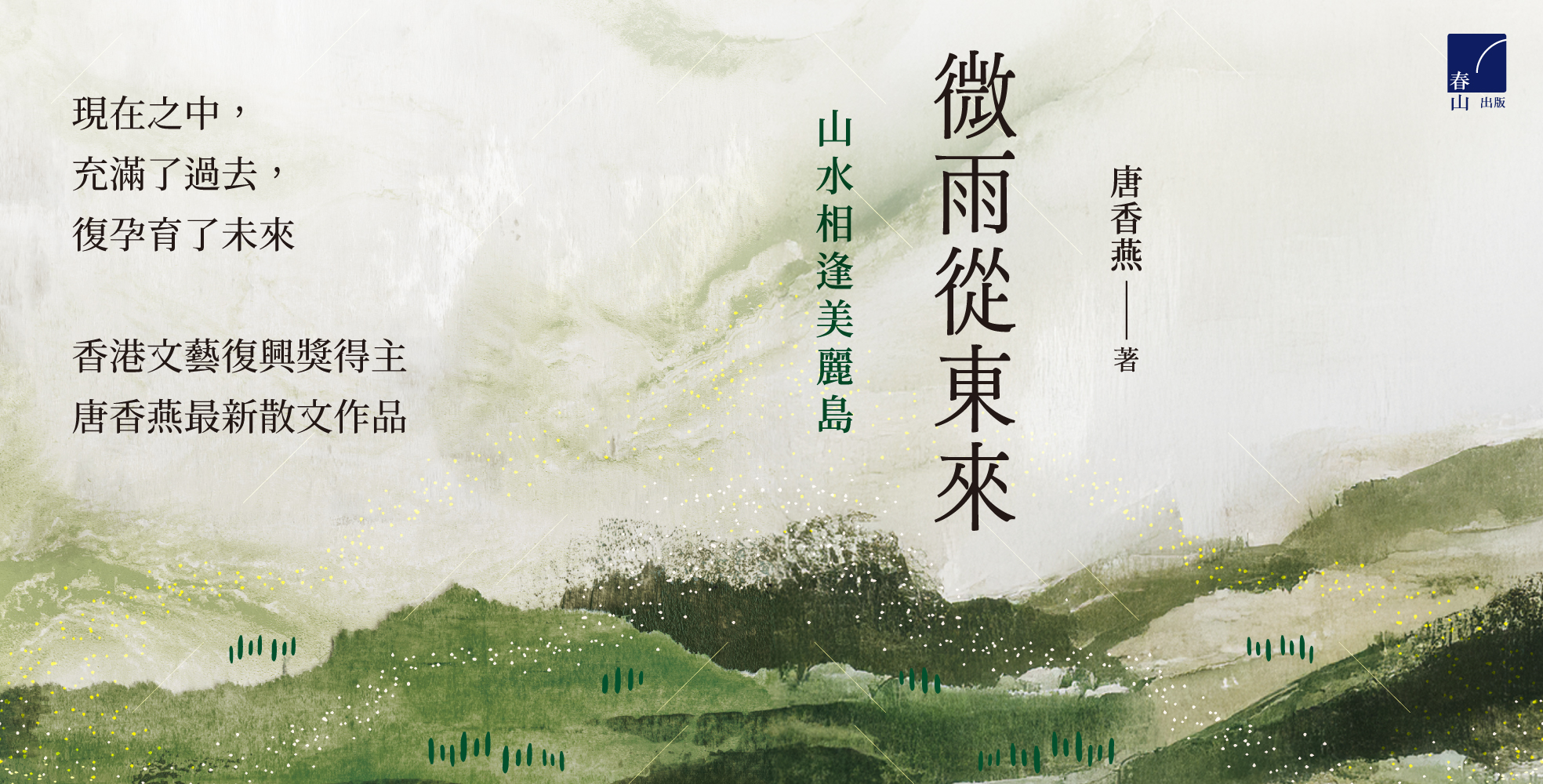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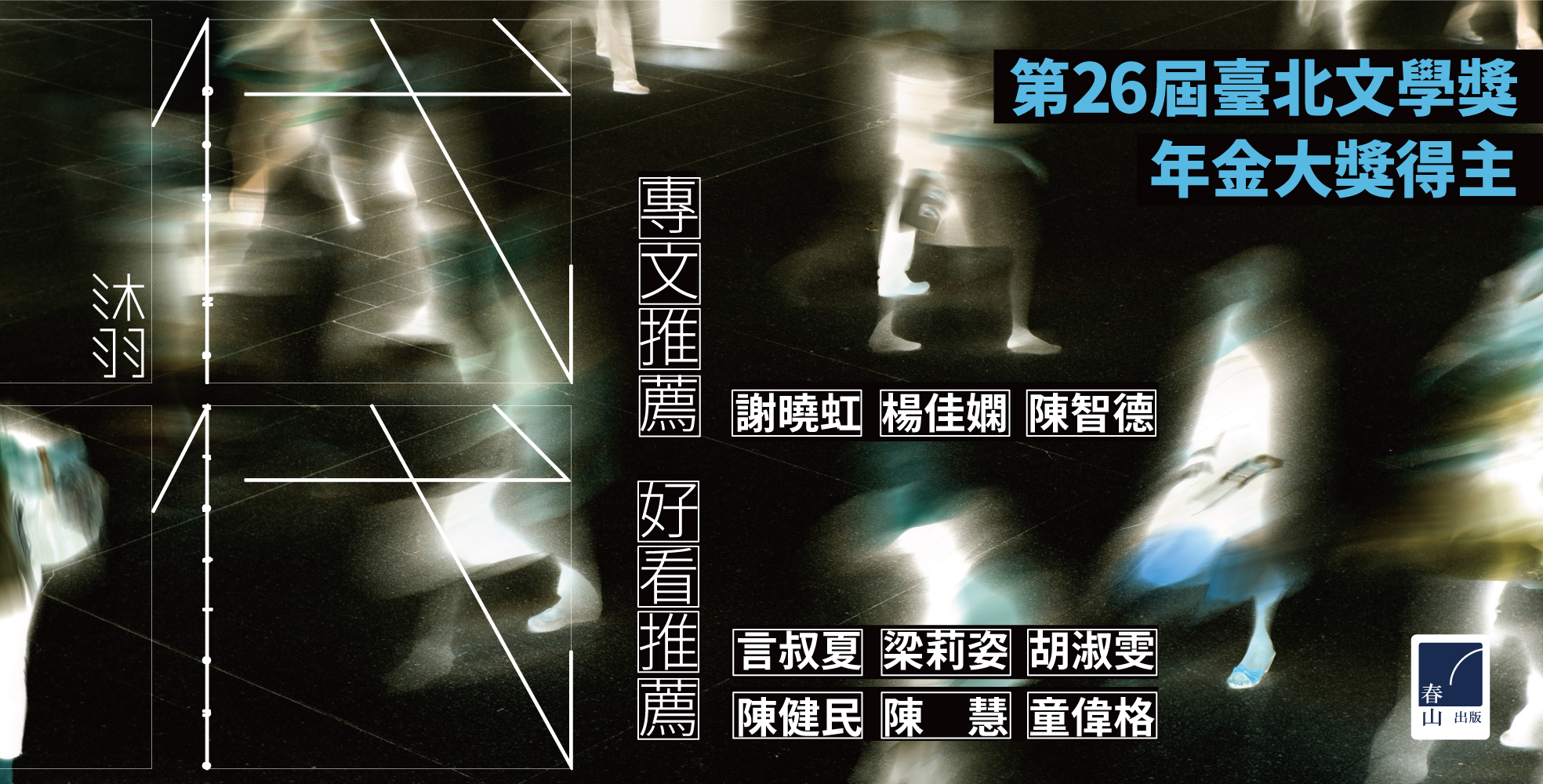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