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頭望明月,低頭……地上有六便士。望月的人想登天,不屑屈膝撿錢,這是本書的主旨。毛姆借用畫家高更的生平,刻畫主人公懷抱著登天的野望,不惜悖德追求理想。問題是,在百年前的英國,六便士值得撿嗎?
二十世紀初,毛姆連續發表幾部小說和劇本,挾著《人性枷鎖》洛陽紙貴之勢,在英國躋身名家之林。當時令他遺憾的或許是這些作品叫座不叫好,評論界普遍將他歸類為通俗文學寫手,他始終與大獎無緣。是繼續低頭寫暢銷書好呢,或者仰天祈求文壇垂愛?

毛姆(1874-1965)是20世紀英國最受歡迎的小說家、劇作家之一。(圖片來源/ wiki)
毛姆用詞平實無華,行文的著眼點在親民,再加上他敘事穩健、人物描摹生動、言語輝映人心等優點,廣獲普羅大眾喜愛。然而,在書寫《月亮與六便士》時,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毛姆筆調急轉彎。若說《臺灣漫遊錄》以翻譯腔戲仿日翻中譯本,《月亮與六便士》用的便是在當時即已老氣橫秋的文學腔,非但不體貼讀者,更以老一輩愛用的雙重否定、夾敘夾議、繁複長句、多重子句,來闡述哲理,還不時引經據典,頻頻離題,以增添權威感和深度。總之,毛姆的忠實讀者捧場之餘,對他這部新作有個煩言──兌換現代說法──炫技。
翻譯本書期間,我感歎《月亮與六便士》比古還古,連敘事者都自問是否太「舞文弄墨」,於是我向三位美國友人訴苦,其中兩人回家從書架翻出舊書重讀,與我有同感,頭兩章讀得辛苦,但後來大呼痛快。另一人根本讀不下去,看了影視版大罵主人公史崔克蘭沒良心,慶幸自己沒浪費時間還傷眼。閱讀毛姆,若以旅程來比喻的話,毛姆的其他小說像順風揚帆徜徉大海,但《月亮與六便士》一啟航就白浪滔滔,晃到有些讀者直想棄船回岸上,殊不知這本屬於先冷後熱型,產科醫師出身的毛姆想接生一個新毛姆。
小說《臺灣漫遊錄》裡,作者楊双子請一名冒牌「灣生」為「新譯本」立序,毛姆則為《月亮與六便士》虛構一位年近半百的無名氏作家,故事的梗概是作家為鬼才立傳的採訪寫作過程,而這作家的背景恰似放下產鉗、擁抱筆墨的毛姆。頭兩章中,毛姆藉無名氏之筆,先界定「卓絕」的內涵,說明藝術家以傑作造福人間之餘,更獻上一份厚禮:藝術家本身。換言之,藝術家不僅彩繪給有緣人欣賞,他們的獸心惡行也值得抽絲剝繭探究。敘事者繼而調侃粉絲造神的心態,譏諷孝子為不肖先父講好話的虛偽,暗批新生代文筆不如前人,並坦承「新舊之爭永無弭平之日」。接下來,毛姆恢復本色,重拾講故事老手的絕活,請讀者戴上獵鹿帽,在敘事者帶領下,踏上偵探的征途,從倫敦追到法國,幾年後在巴黎與史崔克蘭心機對壘,最後再浪跡大溪地,一窺絕情大叔史崔克蘭的隱心跡。
整本小說裡,毛姆不提六便士,約莫是給讀者自行去體悟圓月和這枚硬幣的反差。但在故事結尾,他引述「家叔亨利」倚老賣老的一句話:「想當年一先令買得到十三顆上等蠔」,等於是給未來讀者出一道數學習題,六便士價值呼之欲出。
《月亮與六便士》今譯的價值何在?有一派主張,新譯本若無法超越舊譯本,就不值得推出。但我認為,新舊譯本都是創作,可平行並存,不一定要拚得你死我活。新譯本的挑戰在於,翻譯不僅要忠於原著,更需在語言推陳出新的語境裡保留「時空感」。
既然編輯與讀者多數希望譯本讀來行雲流水,譯者大可昧著良心,不分古今文類和筆調,一律以現代白話文定稿,既省事,又可少死幾個腦細胞,三方皆大歡喜。但便宜行事豈不辜負了毛姆望月求變的苦心?我下筆時為保留原味,在不影響閱讀的前提下,儘量忠於老毛姆,避用本世紀才盛行的「即便」,也盡量以「便」取代「就」。百年前,「家」是尊稱,潦倒的史崔克蘭人品和作品都被鄙視,所以配不上「畫家」,只是區區一個「畫工」,作品能抵債時晉升為「畫匠」,地位還不及藝術名家。毛姆那年代更不會以「老師」稱呼不任教職的人。另外,「土著」(natives)只用在人物對話中,其餘譯成「島民」。
保留時空感之外,我也避免放縱主觀意識喧賓奪主。拋家棄子的史崔克蘭是個古今都痛斥的下三濫,敘事者也好不到哪裡去,兩者對女性的評價固然辛辣,卻禁不起時代考驗,例如:把女人當作洩慾工具,或「女人常誤認感恩即愛情」,或藉船長之口說,「基督教最荒唐的觀念之一是女人也具有靈性」。此外,白人眼中的落後國家女人比家畜更不如,例如:大溪地那環節裡,島上的女老闆認為打老婆的男人才是好丈夫,待嫁的女孩更附和,「不然我怎麼曉得他愛不愛我」。我再無法認同,也盡可能回歸百年前的社會環境,按捺住理智,以歧視女性的語氣轉述作者原意。
書裡引用法國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名言「理智理不清情絲」(Le cœ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oint.),幸好史崔克蘭無情無義,敘事者無須在情事上多加著墨,但他對宗教卻常有意無意提一句,彷彿提醒讀者,狼心怪傑的故事底下另有一道潛主題:「史崔克蘭具有狂熱分子的坦率,具有使徒的赤忱」。極突兀的一點是,史崔克蘭和大溪地嫩妻對話裡的「你」全以古文取代:「汝乃我夫,我乃汝婦。」史崔克蘭之子是牧師,在故事尾聲以仿經文說:「上帝的磨坊精工慢磨,磨工卻極其細膩。」全書畫下句點前,亨利叔叔令人匪夷所思的蠔語也可從宗教角度詮釋(亨利的世界是家鄉假道學的宗教圈和「以蠔代鮑」的俗世,相當於銀幣;毛姆的世界是男男共舞的巴黎同志圈,以月亮象徵。)更明顯的是──某人說史崔克蘭已創造出一個世界,「看著是好的」(出自《舊約》創世紀的說法 saw it was good,主詞是「主」),然後「在驕傲和鄙薄的心態下毀滅世界」。由牧師叔父亨利帶大的毛姆不信神,對宗教存疑,身為小譯者的我在此點到為止,請讀者消化整本書,再深思宗教在故事裡的隱喻。
世界大戰方酣,毛姆為英國政府遠赴南太平洋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因罹患肺結核而回國治療,痊癒後,在男祕書陪同下前往大溪地休養,順便為已起筆的《月亮與六便士》蒐集資料。但在毛姆的隨筆集《作家筆記》和《寫作回憶錄》中,大溪地的見聞總計不到一頁。我讀《月亮與六便士》的目的之一,是重溫我的大溪地蜜月往事,想再神遊地表罕見的環礁夢幻藍潟湖,而毛姆竟然只寫叢林峻嶺。自由撰稿作家威爾蒙.梅納德(Wilmon Menard)多年後專訪毛姆,證實他不僅登陸大溪地,也在島上找到高更的情婦。但情婦不多說什麼,只質疑高更遺族為何不託毛姆帶錢給她。高更在島上的兒子已滿十八歲,正在等徵兵令,臉型和體態都是高更翻版,不識字的他見過父親的畫,但不覺得美。故事末尾,毛姆描寫這男孩在船上熱舞,對男孩的未來有所憧憬,可惜事與願違,成年的他多次因酒醉鬧事妨害風化而坐牢,平日以手工紀念品擺地攤,也用蠟筆在畫紙上簽姓高更,一張賣一美元。熟悉高更生平的讀者最好拋開史實,把高更和史崔克蘭畫上等號恐怕會讀到火大。
在虛虛實實之間,無論潛主題是否存在,女性是否被物化,敘事者是否舞文弄墨,敘事者講的是不是毛姆心聲,無論古書值不值得今譯,毛姆寫的畫家故事頭尾呼應,蘊意深邃,餘韻無窮盡,而俗人如我在完稿之後更有一個疑問耿耿於懷:六便士到底值多少?換算外幣是譯者的基本義務,總不能因為是作者隻字未提的古幣,便望月而視若無睹吧?我埋頭查證之下,總算得知六便士是銀幣,在二十世紀初能請工人清掃煙囪一次,或吃兩頓豐盛的晚餐,或買三、四顆頂級的英國牡蠣。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或許能買一本今譯的古書療心飢。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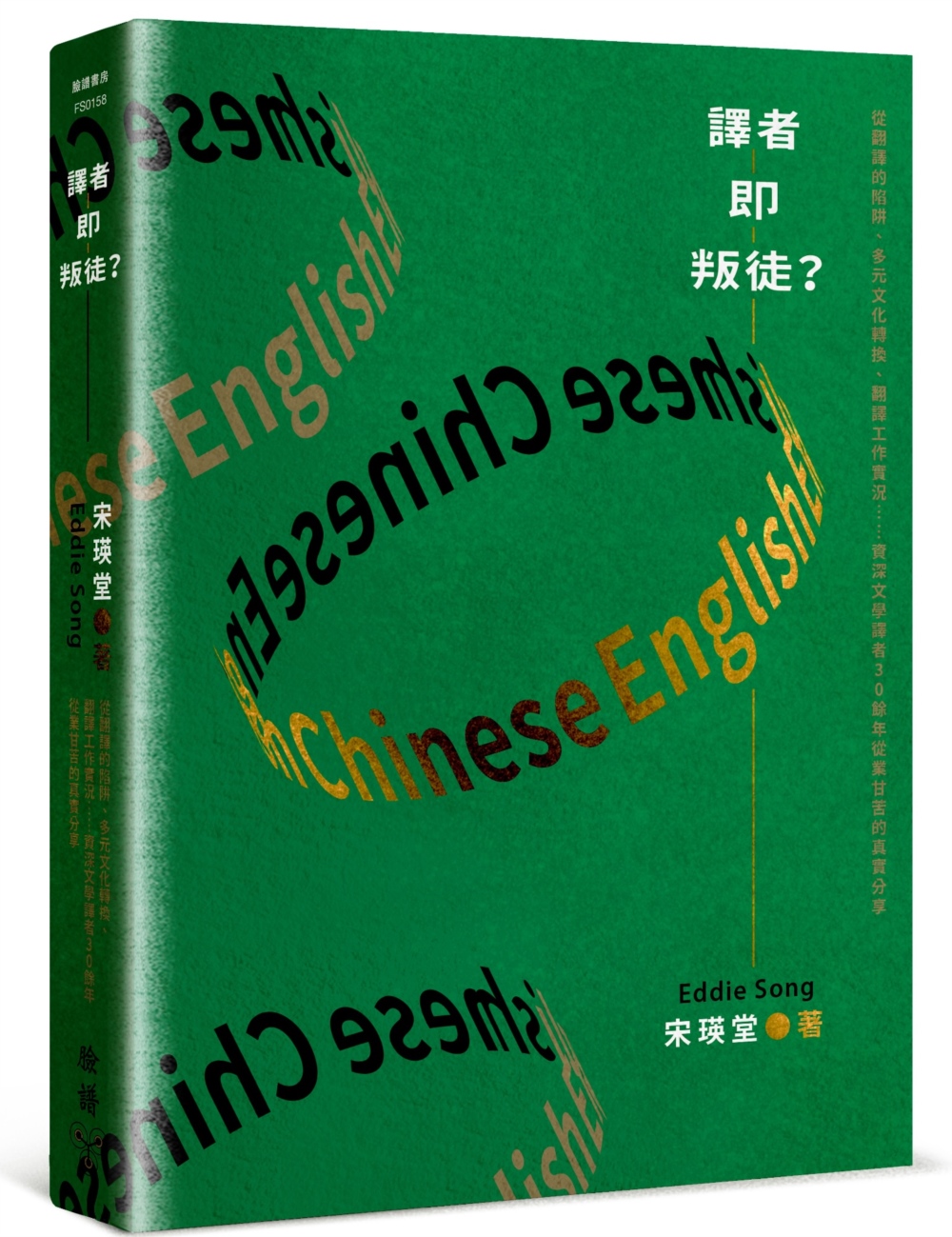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