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有一門必修課叫作「當代人類處境」,課如其名,沒有固定的樣態,在我接手教授之前,已逐漸長出「演講課」的定位,各週邀請不同學者暢談最新的人類學研究議題。我開始授課之後,設計成依據博士生的研究興趣,找尋相對應、高評價、最好獲得過書獎的當代民族誌一本本閱讀討論,我自己也能由此接觸到本來沒有機會認識的人類學家與優秀作品。
這次教課的時候,我幫一位已在菲律賓馬尼拉貧民窟出入過的博士生配對上一本關於巴西曾經最大的垃圾掩埋場「格拉馬喬花園」(Jardim Gramacho)的民族誌《棄品重生:里約垃圾場的生命與勞動》(Reclaiming the Discarded: Life and Labor on Rio's Garbage Dump)。這本書曾獲得2020年美國經濟人類學學會書獎,在課程最後也得到大部分同學的青睞,將其評選為一學期以來的民族誌書單中最喜愛的一本,而我也深有同感。
人類學家米勒(Kathleen Millar)處理的是一個人社領域讀者一定不會陌生的命題:被排除於主流社會韻律之外、過著危殆生活的「垃圾撿拾者」(catadores)。這種主題通常可以找到兩種書寫策略,第一種是見證與控訴,講述那些被邊緣化、汙名化、視為「非人」的生命故事,並直指創造這樣處境的權力與暴力結構。此手法大致符合一種興起於80年代後、回應新自由主義全面破壞的「暗黑人類學」倡議,呼籲人類學家關注在社會不平等、壓迫、剝削之中的受苦主體。
第二種則是翻轉與創造,著重在黑暗深淵之中找尋幽幽不滅的微光,揭示危殆生活中的生存、照護、愛慾、道義等多重關係,甚至希望與夢想等對於未來的想望。此手法大致符合一種「良善人類學」的提醒,期盼人類學能超越受苦主體的描繪,重新找回過往經典民族誌中對於一地、一群體之文化價值與行動的好奇。
《棄品重生》則找到了第三條路,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命」好了,看似籠統,實則深刻。米勒觀察到,儘管垃圾撿拾者在垃圾場的生活中傷痕累累甚至危及性命,也亟欲尋求正當體面的工作、脫離汙穢在主流社會中立足。然而她發現,許多離開的人終究會回來,包括她自己。「為什麼會復返垃圾生活」成為這部民族誌的核心探問。原因不在於此間有不為外人所知的「文化價值」吸引著他們,也並非形塑垃圾掩埋場的「社會不義」不夠強大,而是這已成為一種他們總是能理解但又哭笑不得的「生命形式」,包含了一切醜惡與良善的事物、破壞與創造的力量。

我們曾經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自從殖民者到來後,我們卻成了他們所唾棄的族群。
若不說書名而要讀者猜是哪一本左岸文化的人類學出版品,很有可能會說是關於加拿大因紐特人在殖民處境中自殺與其他醫療問題的《生命之側》。然而,同樣的邊緣主體關懷,克里弗德在80年代末想表達的卻是那首詩的開頭,「純粹的美國產物已然瘋狂」,也就是過往民族誌書寫熟悉的對象(他者、原住民、文化……)早已捲入現代性計畫中而無純粹的原真性,那麼古典人類學研究的初衷:搶救、保存、分類、全貌觀等等,該如何自處?這就是所謂「文化的困境」。
在《文化的困境》中,克里弗德的解決之道在將民族誌(或民族誌物件的收藏)視為某種特殊文類的文學性,並打破人類學家書寫的權威,認可其中多聲共構、拼貼、錯置的基調。往後透過《人類學反思三部曲》,他將從移動、旅行、接觸區、成為等概念繼續思索。克里弗德的這套策略同時也面對了耽溺於文學修辭與再現的批評,某種程度而言,關注「社會不義」的「暗黑人類學」與重返「文化價值」的「良善人類學」都是對此的回應。然而,若從上述引言重新讀起來,克里弗德與近來民族誌「生命轉向」的關懷其實是一致的。沒有錯,是殖民讓原住民失去土地、流落成為白人家庭中的幫傭,重新找回他們的文化創意與尊嚴也是富有意義的行動,但到頭來這就是他們此刻、屬於自己的「生命形式」,如此而已。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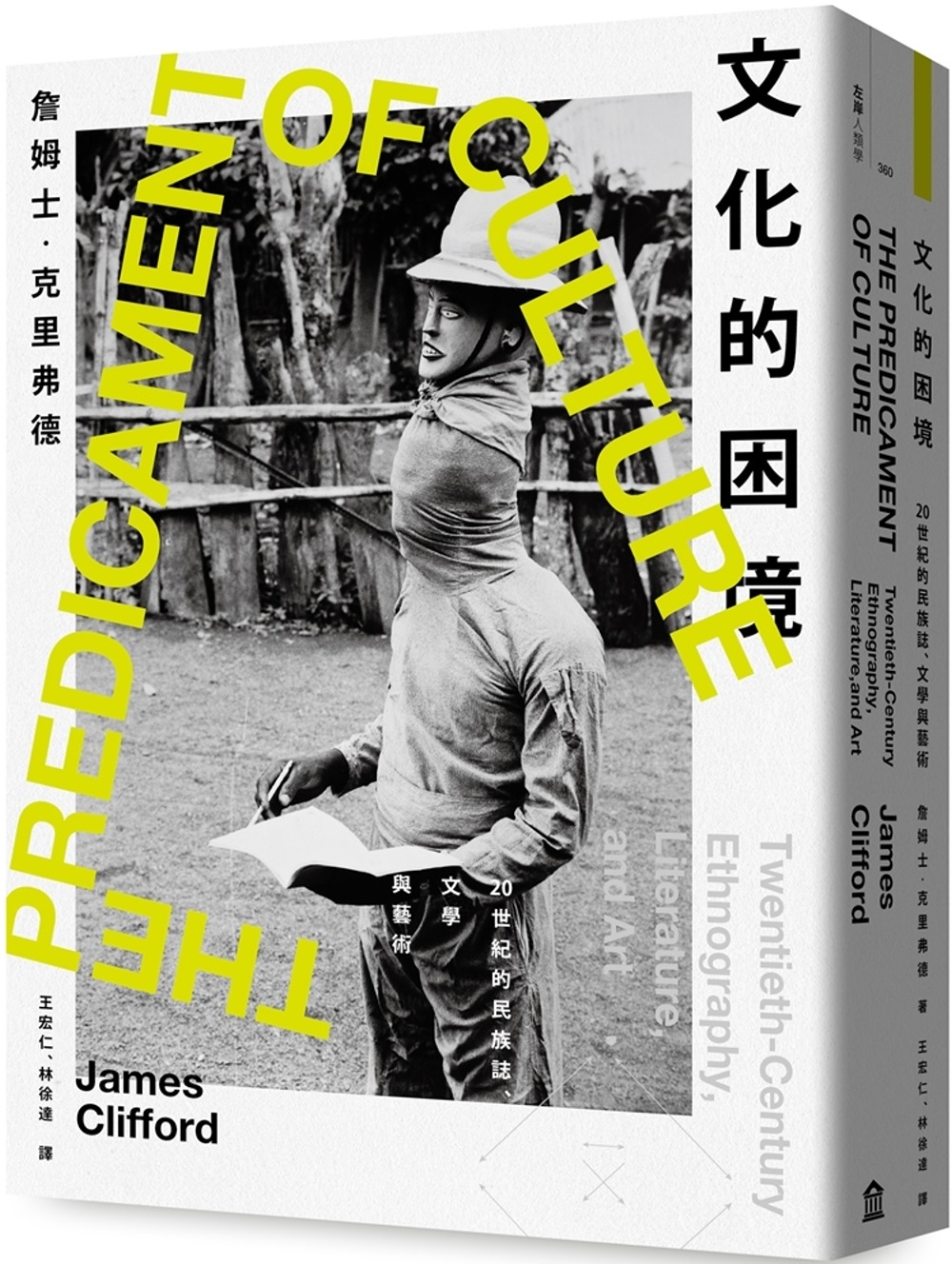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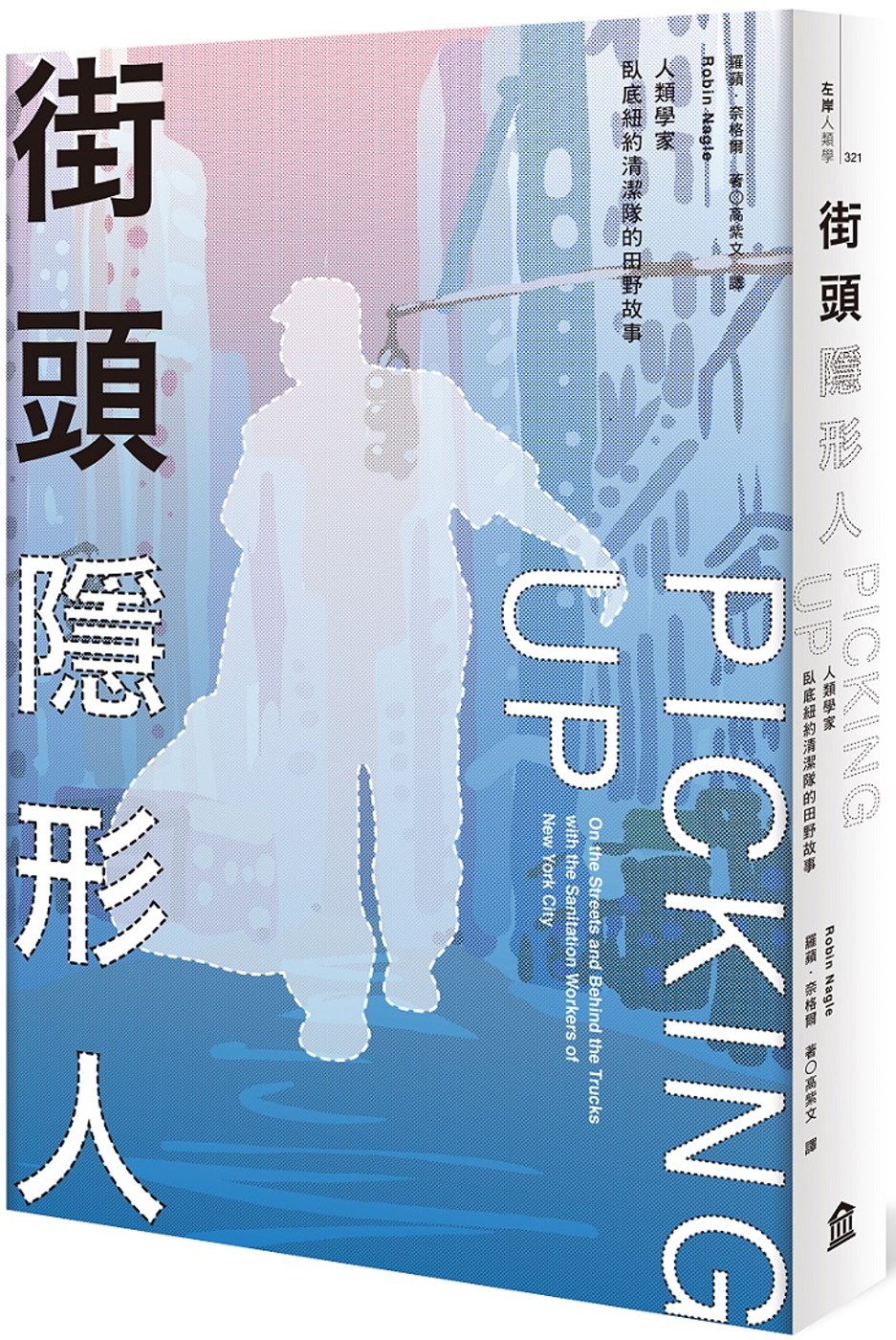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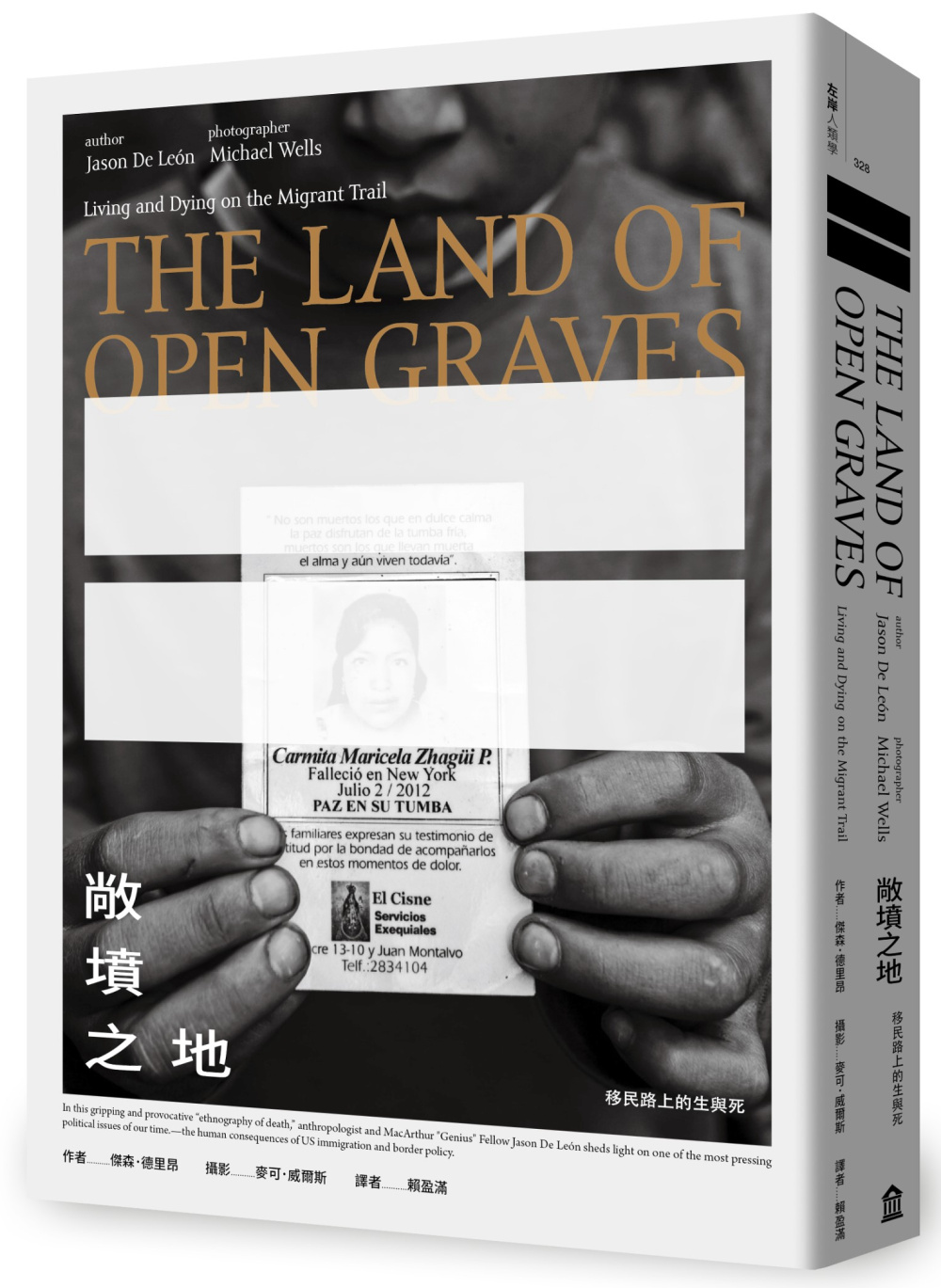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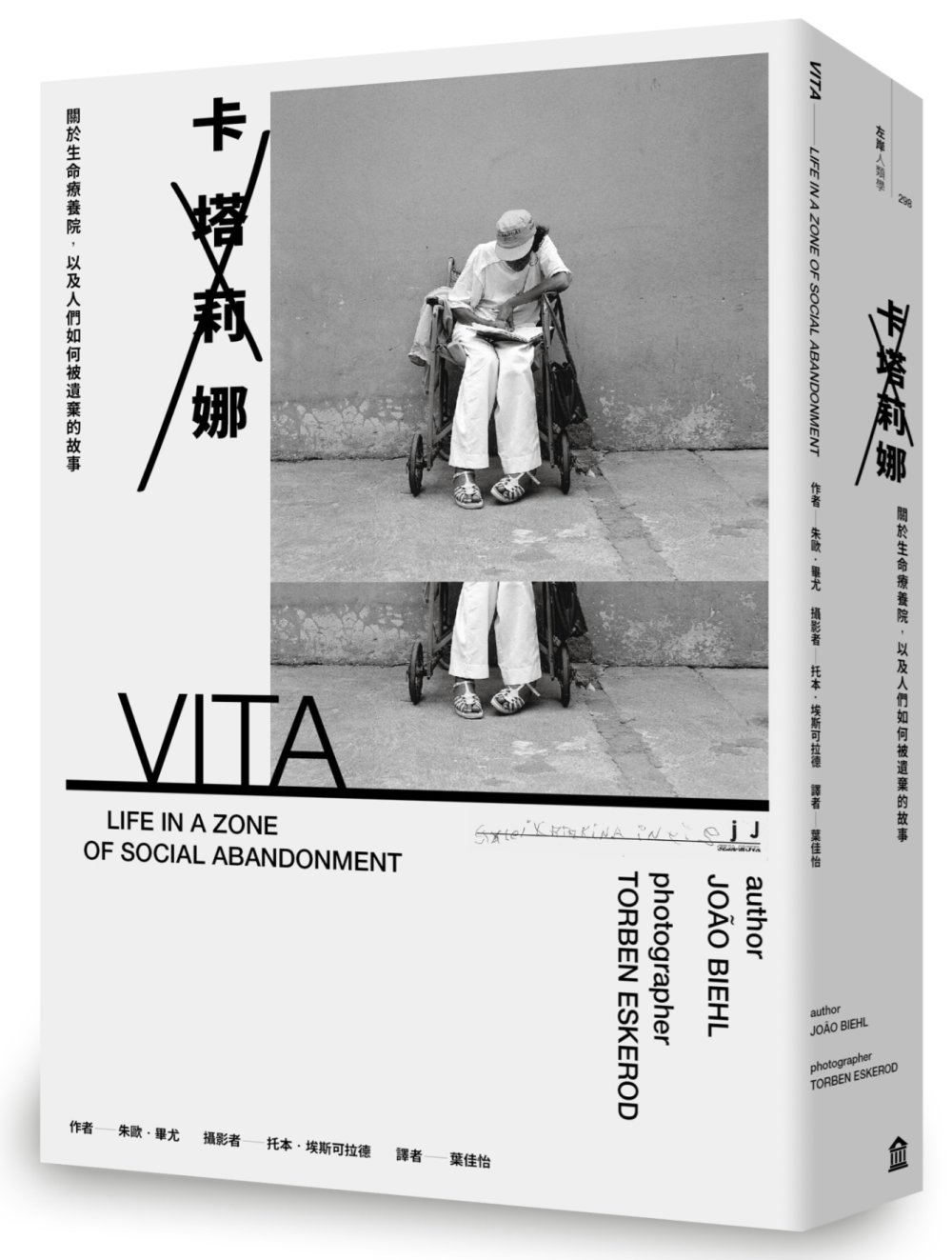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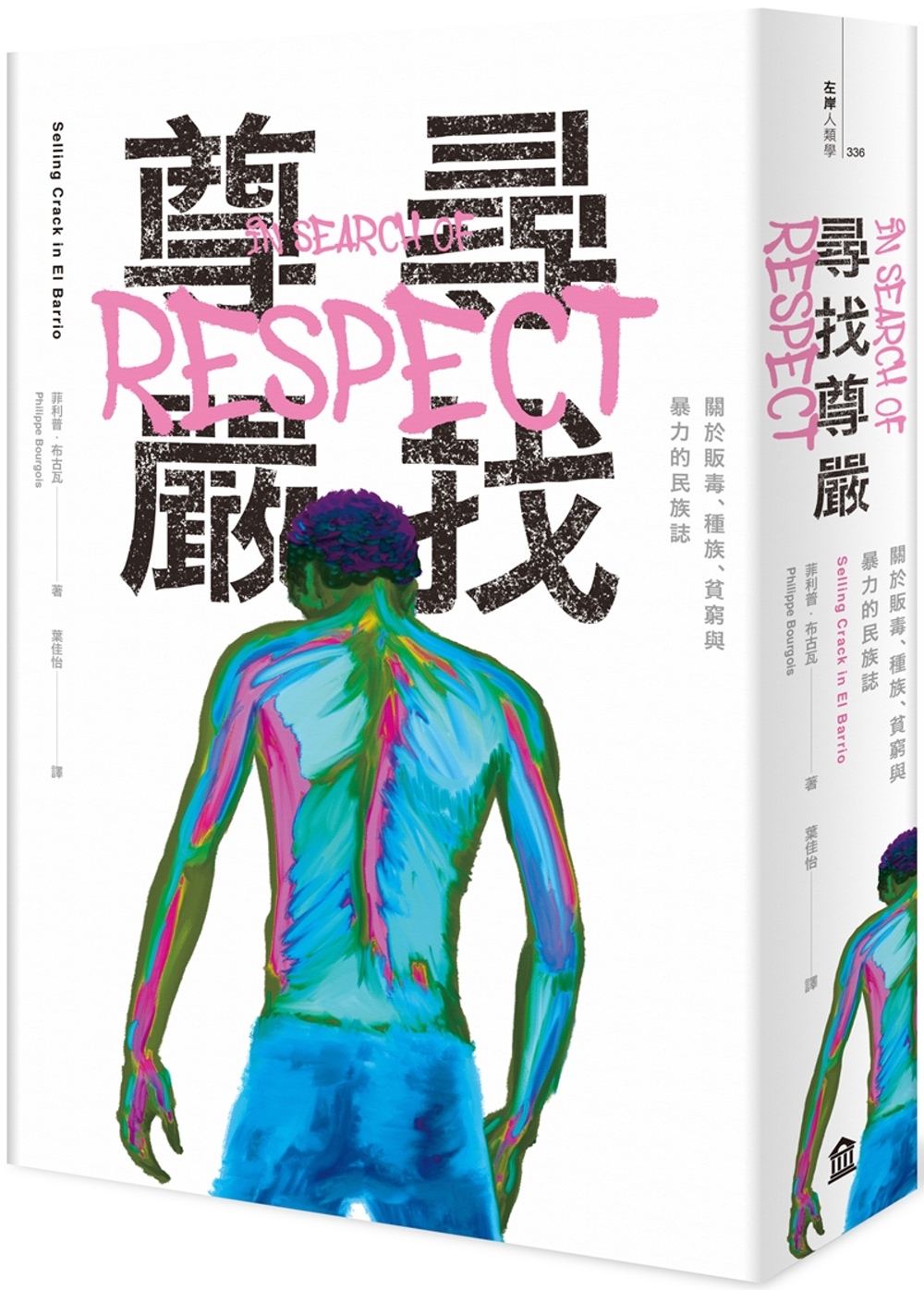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