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瞿筱葳以《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書寫奶奶,14年後出版《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寫學者父親瞿海源。
那些曾經的抗議軍人干政、憲政改革、媒體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社會運動的歷史,或說一本以現年八十多歲社會學家瞿海源為主軸的回憶錄《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真的好看嗎?
還真好看!畢竟是女兒寫父親和自己啊。這本書的作者瞿筱葳一進門,就跟博客來OKAPI的編輯說:「採訪者啟麟是十八歲就認識的同學,我們認識二十幾年了。」然後她再跟《訪父記》的編輯君佩說:「他是我的上一本書《留味行》的編輯。」
其實是三十幾年了,雖然她不想承認。筱葳的頭髮已經半白,看來遺傳了奶奶和父親的基因。她不只遺傳了頭髮。今天我們也知道了,雖然她上大學之前一直不太關心父親的關心──那些社會運動的種種。但是為了寫這本兩代人的回憶錄,她啃了大量的社會學論文和文獻。
人生功課遲早會來。終究是要念社會學的,再往前追溯(或是往後?)也是會被社會系同學帶壞的。
瞿氏父女小檔案
| ▌瞿海源 資深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澄社」的創社社員,曾任總幹事及社長。澄社是臺灣解嚴前後由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在推動民主改革、監督政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積極投入社會運動,如反軍人組閣、推動司法改革、媒體改革等。他也參與了國中「公民與道德」課本的編輯工作,推動教科書內容的民主化與社會化。曾任公共媒體催生行動聯盟的召集人,致力於公共電視的成立。長期擔任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 ▌瞿筱葳 七〇年代中生於臺北。曾任職社運、媒體、紀實影片工作、文化行政法人,為 g0v 臺灣零時政府社群共同發起人。著有: 《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以及奶奶的十一道菜》,獲金鼎獎、開卷好書獎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獲臺北文學獎年金大獎 |
籌備婚禮時,我突發奇想要在先生賃居的坪林山上辦露天婚禮,房東祖宅土角厝前院子,很適合搭個小臺有點音樂……我父親來到山上開心得不得了,也可能他暗嘆女兒的婚禮還算能跟他的私自辦的結婚酒會匹敵。
趙:從妳的上一本書《留味行》中,看見奶奶在二戰時千里尋夫。這本《訪父記》中又看見父母私奔。你們家族有這種不顧一切尋愛的傳統啊!
瞿: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其實我受我奶奶影響比較大,她是這種比較帥的女性。我和先生也是比較怪的人,我們婚禮的其中一場辦在老公自租的山上三合院,父母也當賓客邀請來玩。
趙:《留味行》中看得出妳跟奶奶的感情深厚,為什麼這次會想寫父親?《訪父記》中說妳和父母不親,甚至對他們說「我其實不喜歡你們」。妳經過「半年考慮」才決定寫這本書,能說說妳的思維鏈嗎?
瞿:我一直想像他這種大人物,應該會有大部頭的傳記,那我就逃過了這一題。但是他在《留味行》那篇序,大家都讀得到他很吃味,所以他可能也希望被這樣書寫。我真的想了半年,期間不只一個朋友跟我說,這本書只有我能寫。後來決定寫這本書,也是做我的人生功課。
開始寫之後,他拿了李遠哲和盧修一的傳記給我看。他可能期待的是像磚頭那麼厚的傳記。他還下指令說,妳第一章應該要補什麼什麼。但是我已經長大了,可以不理會他的期待。我就(表情和語氣)很柔~~的說,這是一本從女兒觀點寫的訪談記錄,面對的是年輕讀者,那些不認識他的人。
趙:妳出生才三十四天,父親就去美國留學。剛滿一歲半,母親也去美國幫忙父親。妳一直到了四歲才認識這位父親。以妳現在的年紀,怎麼回頭看父親這個決定?
瞿:我現在當媽了,生了兩個兒子。現在來看,四歲超大欸,可以去念幼兒園中班了。現在想起來,我當時是滿驚嚇的。突然來一個陌生的叔叔阿姨,說我其實是妳的父母,現在我們要搬家。然後我就脫離那個原來認識的奶奶啊,姑姑啊,表姐啊。
我因為寫這本書,重新從各個面向理性去看,看那時國科會的出國計劃,那時國家的風雨飄搖,還有家裡的經濟情況。OK,我可以理解,當時只能那樣。
趙:他也可以選擇不去美國?
瞿:對,他可以選擇不去。但是他如果不選這條路,我們家也許沒有辦法透過考試、念書,然後從底層的軍人家庭,變成知識分子家庭。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等於是把所有事情攤平來看。除了我自己童年的衝擊之外,還有這些社會、文化、歷史、家庭的因素。
所以寫這本書,比較是為了自己,這是我的人生功課。我想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來的過程經歷了什麼。

趙:所以寫作自己的人生功課,不是為父親立傳?
瞿:《訪父記》有點類似一本雙回憶錄,是兩代人的回憶。因為我不僅寫父親,也把我寫進去了,其中也有你的身影欸。
趙:大學的部分我們後面再聊。看這個雙線的回憶錄,會發現妳跟家庭的親緣有點淡薄?除了四歲以前,然後妳國中又住校。雖然是臺北人,大學卻外宿。
瞿:對,的確是親緣淡薄。達人國中和高中的三年級都規定要住校,天主教學校管得很嚴格。當年在臺北的私立高中,生活就是念書,沒有社團,也不會翹課。然後很自然的覺得大學應該要離家嘛,一方面是政大在木柵比較偏遠,同時,知識分子家中那種拘謹的生活方式我已經沒有辦法了。大學不是會跟你們喝酒嗎?抽菸喝酒都會。我回家的時候,也是去奶奶家住,而不是回父母家。

《訪父記》附錄照片。左:奶奶晚年與家人合影,父親的頭髮和奶奶一樣銀白。
右:2014年吳叡人、瞿海源等中研院自由學社學者呼籲總統馬英九「傾聽民意,重建憲政」。
趙:妳說知識分子的家庭……妳是什麼時候意識到父親是一號人物的?
瞿:考完大學之後,考得很累,然後他逼一個高中沒在運動的女兒一起去爬山。去爬七星山,累得半死。下山的人看到他就行注目禮,然後說瞿教授好。一排人都這樣耶。我問,你認識他們嗎?他說沒有啊,大家都認識我。
我爬到山頂已經快要吐了,休息的時候,他開始講跟各個政治人物的一些小事互動。他這樣講,我才,哦,知道他的確是一號人物。他那時還會穿西裝去電視臺錄影,發表選舉的評論,就是現在的政治評論家。
不過澄社的選舉評鑑、野百合學運之類,我頂多都是看報紙,回家也不太想問。我國高中時代比較擔心的是數學考三十幾分。

趙:妳訪談父親時,他對編過國中公民課本這件事只有一語帶過,但妳似乎特別感興趣?
瞿:訪談那時正逢「青鳥行動」。往前看,從野百合學運、野草莓學運、318學運,參與的是哪一種人?我就去比對了年紀,查了各種論文,我發現臺灣的公民教育很特殊。
我們吃什麼就會長什麼。我們吃威權教育,骨子裡面就會有這種影響。可是看年輕一輩的公民課本,我翻開的時候還滿震撼的──我們是公民,那我們要做什麼?社會的組成是什麼?就是這麼簡單、基礎的提問。
但是我們國高中時候讀的《公民與道德》,只有兩個字:「要乖」。

趙:妳是什麼時候有意識的發現自己很關心社會議題的?
瞿:欸......我覺得是因為認識你們這群社會系的耶。嗯。就是十八歲認識一群社會系的朋友,然後你們會去搭帳篷抗議,那時候政大沒有這樣的人啊。還有同學是綠潮社、女研社的,還有修曼尼斯社、國思社。在我們租的那個宿舍,這些人都會來,然後就會在那邊閒扯。
所以現在是受訪者,受到訪問者的影響。我學會抽菸不就是因為被你們影響嗎?還有那些社會議題,那時覺得你們讀左派的書很潮。這真是一個奇怪的訪談,本來是要溯源,結果溯到你身上了。這太奇妙。
上一本書《留味行》我回絕了兩家出版社,因為我說要留給大學同學當出版社的創社作。
趙:然後我們開出版社就得了金鼎獎和開卷好書獎。妳真厲害,一出手就中,隔了十幾年,這次《訪父記》又獲得臺北文學獎年金大獎。不過妳這十幾年,除了生出《訪父記》,也生了兩個兒子,他們幾年級了?
瞿:一個升小三、一個升小五。每天還是會親親抱抱。
趙:這是我們這一代從沒體會過的成長經歷。
瞿:真的,開心。
對比四歲之前不認識父母,對現在的瞿筱葳來說,只有抱小孩才是正經事。寫完一本書,她交出自己的人生功課,療癒自己的童年。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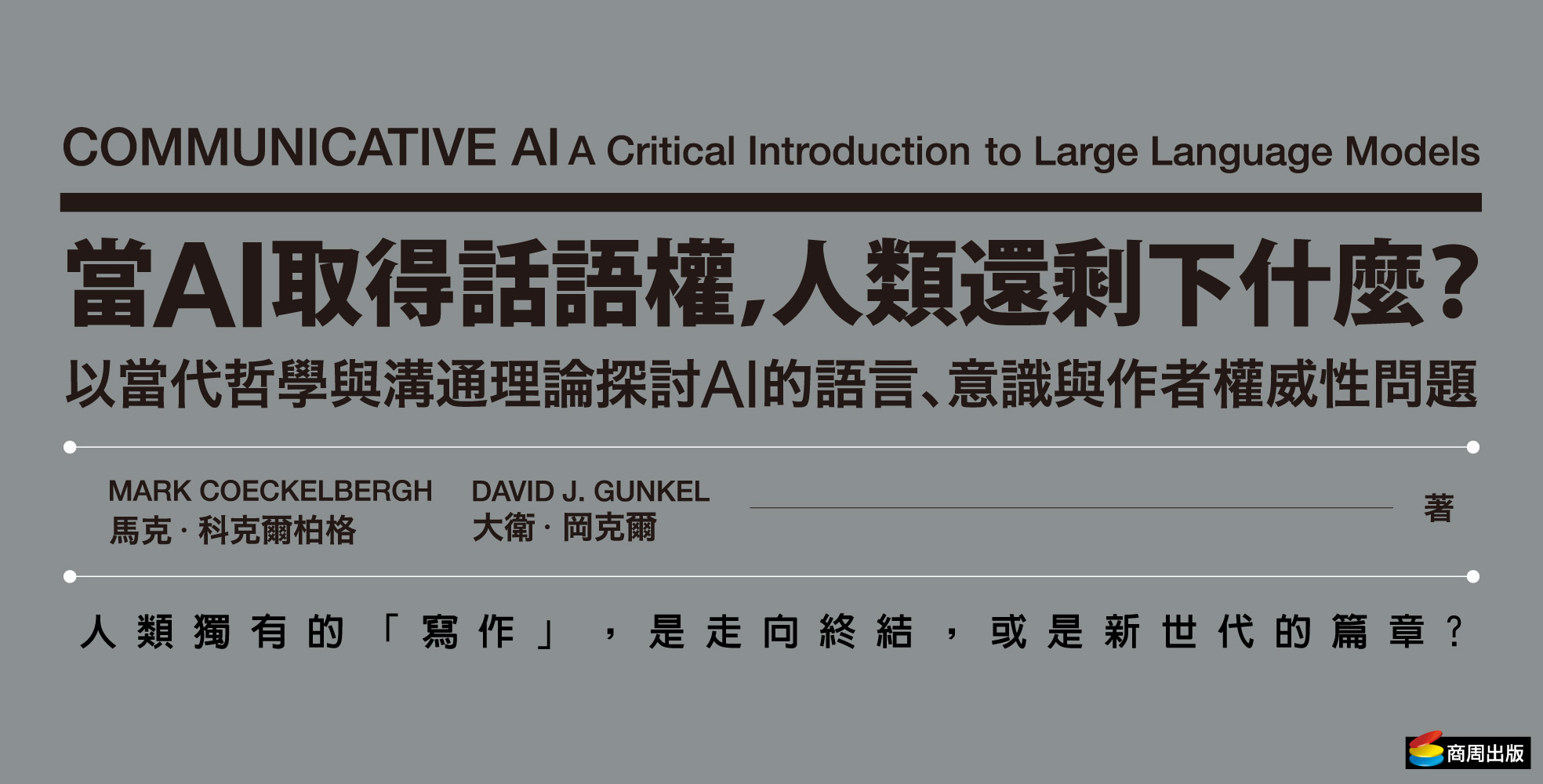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