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外文系畢業、在美國取得博士並在美國任教的桑梓蘭(Tze-lan D. Sang),在2003年出版《浮現的女同志:現代中國的女性同性情慾》(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這本書應該算是第一本綜覽女同志在現代中國的英文專書。這部野心之作,在時間上橫跨整個二十世紀,在空間上將中國和台灣(在此書,指台灣的女同志運動和邱妙津小說)打包在一起。將台灣跟中國打包在一起是美國和其他第一世界國家的學界「習慣」,在此暫不多談。
《浮》分為四個部分:一、現代中國之前(《聊齋》中的女女戀等等);二、民國時期(「同性戀愛」一詞如何從國外傳入中國、五四文學的女女戀);三、毛澤東時代完結之後的中國(林白、陳染的小說);以及,四、解嚴後的台灣(女同志運動、邱妙津的自傳性小說)。在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台灣經驗」被選角擔任儼然壓軸的一個篇章。
《浮》並非專門談論文學的書;它也兼談了論述的翻譯(如「性學」如何把「同性戀愛」的觀念帶入中國)、台灣同運等等。也就是說,與其說《浮》就文學而論文學,還不如說《浮》藉著介紹中國和台灣的種種女女「現象」(含文學,但絕不只限於文學)來讓英語世界的讀者認識「中國人的女同性戀世界」。這種策略性的寫書方式──將文學做為認識社會的教材──在美國的東亞研究界是常態,用英文所寫的日本同志專書也同樣著重介紹日本「社會」而非分析日本「文學」。
文學反映了社會嗎?這種說法,我並不完全否定;但我想提醒,文學雖然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但這種反映必然是扭曲的──寫作者的技藝就在於扭曲社會現實的手法。邱妙津的小說可以作為認識台灣的一種參考資料(但是可不可以作為認識中國的材料呢?),但絕不可能提供可靠的社會顯影。我並不是說邱的小說技藝不可靠,而是她──或許多國內外的小說作者──不大可能把自己的小說技藝貶為「僅僅只是反映社會的可靠鏡子」。
《浮》提及台灣電視節目曾偷拍女同志場所(這是璩美鳳、張雅琴等人在1990年代留下的案底),並且認為邱妙津憤怒地抨擊大眾媒體偷窺女同志。對於這種說法我很存疑。在邱妙津出版小說的1990年代,解嚴後的媒體的確很愛偷拍同志,在歷史留下紀錄;但,我們手上並沒有邱妙津本人批判媒體的具體證據。我們頂多只能說,《鱷魚小說》中的卡通鱷魚跟媒體之間存有互相調侃的關係。
(題外話:《浮》並且指出邱妙津的小說突顯了女同志個體和女同志運動之間的張力、曝露出同志運動論述並不足以捕捉同志個體的苦楚──我也有異見。邱妙津的小說並沒有評議女同志運動,因為作者早於女同志運動興起之前就英年早逝。同志運動做為邱妙津的後來者,評議邱妙津其人其作,才是事實。)
不過,《浮》對於媒體暴力梗梗於懷的態度,卻提醒了我們該正視邱妙津其人其作跟媒體的密切關係:在作品之外,作者和作品的名聲的確都是1990年代媒體的造物,我甚至想說,往前推的1980年代媒體和往後拉的21世紀媒體都不大可能造就出類似邱妙津風潮的現象(2010年代的媒體當然也還在偷窺同志,但這年頭的媒體已經跟同志「文學」「作家」沒什麼利害關係了);在作品之內,《鱷魚小說》中看起來沒有意義的鱷魚章節,其實「很有意義地」討論了同志和媒體的互動。說起來,《鱷魚手紀》可能是極少數對大眾媒體具有高度自覺的台灣小說之一;在《鱷魚手紀》之前流行過的後現代文學(見黃凡、林燿德、張大春等人舊作)固然很在乎大眾媒體(大眾媒體就是後現代的神龕),但也不至於像《鱷魚手紀》展現出對大眾媒體的偏執(paranoia)。
《浮》全書特別在乎的三位作家,除了邱妙津,就是大陸的林白和陳染。她們各以《一個人的戰爭》和《私人生活》為代表作。這兩本書都在台灣出版過,但本地反應很有限。《浮》費心討論《一個人的戰爭》和《私人生活》,是因為(至少在20世紀末)正式出版的中國女同志文學極少,而這兩本書是特例;《浮》也指出,這兩書內的女性是在男女兩性之間周旋沒錯,但是若要看到女同志的「性心理」(sexuality,黃道明譯法)和主體性,就不能只看中國國內,而要看中國國外(即台灣)。在國際學界高度邊緣化的台灣,總是被迫「顧全大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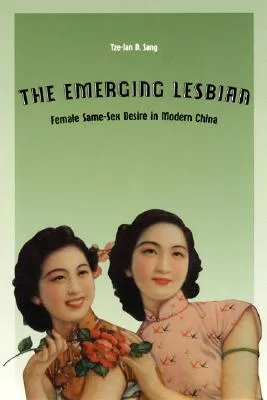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