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昭旨)
「很用力擁抱的時候,我聽見你骨頭碎掉的聲音。」
像吸飽了空氣即將爆裂的肺泡,像情感鼓脹以致於歡聲雷動的心臟,參雜溫柔與暴烈。安靜地愛,安靜地崩壞,安靜地疼痛,吳俞萱帶來首本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愛人」是她對於某些導演、畫家、作者的稱呼。愛的範圍可以很廣,包括電影導演羅伯.布烈松、安東尼奧尼、安哲羅普洛斯、柏格曼、金基德、作家莒哈絲……等,「他們教會我完整的世界觀和對人生的觀察,我覺得他們很誠實地像是交出了肋骨一樣,赤裸地把很多東西交給讀者。」對於這些愛人們、作品們所真誠給予的,可能只是某個鏡頭、某個情緒、某個狀態,吳俞萱說,「我只能寫詩回應。」
以一種難以想像的嚴謹自律,卻又習慣自然,吳俞萱的一天從跑步開始。她連續好幾年清晨五、六點起床,出門跑步一小時,接著回家挑部電影看,類型不限。「我覺得自己比較熟悉精神面,沒有腳踏實地的感覺,也沒辦法書寫出有血有肉的人際互動。」畢竟,精神面和現實有所差距,她也試圖抓回一點真實感,「把自己丟出去一個現場,沒有實際干擾、互動,卻可以不斷觀看。」每個踏出去的腳步,都是踏進現實世界的一步,她穿越晨起運動的人們、經過他人生活的片段,利用抓地力將自己拉回現實,也像是每天的田野調查,鍛鍊觀察能力。
隨著生活階段改變,她陸續待過台北、台東和高雄,「其實外面的世界沒什麼差別,因為我常常只跟自己相處。」除了每週一次的讀書會分享,她沒有出門的必要。不看電視、不玩臉書,只經營部落格,她將眾多雜訊排除在外,與社會上的種種隔絕,「我想像中的生活,是精神的完全自由。」
她嚮往成為莊子所說的「無用」之人,認為賺錢只要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因為無用,想做什麼都能夠照心性去做。對她來說,隔離並非對世界反感,而是因為感覺過多,「我很容易分心,對什麼都好奇,例如什麼東西發出了什麼聲音……」有人在講話、有人在施工,陌生人的走路方式、說話表情,甚至是咖啡店的燈光反射,「不管再日常再微小的事,每個東西對我來說都很新鮮。」帶著孩子般的微笑,她說。
「現在的生活是選擇的結果。」她很早就察覺語言的無用,當人學會將語言當成面具,語言就變得可怕,甚至失去溝通的能力。「我想要發展出更直接、更誠實,不會被扭曲的方式。」她說自己一直想當啞吧,剛上大學時還故意不說話,當然這個選擇很快就失敗,很多時候還是必須開口,「不過這個念頭並沒有被消除,察覺一直存在,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面對自己,於是開始喜歡獨處。」現在的她,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跟自己相處,她說是很普通的生活,看書、看電影、寫作,加上打書摘的習慣,一天就過完了。避免干擾,她也不聽音樂。那會跟自己講話嗎?她仔細的回想,然後笑了,「連自言自語都沒有。」
她引用李歐納.科恩的句子:「如果生活可以過好,詩不過是一層灰。」對於詩,她沒有強求去寫,「懂得溫度、懂得照顧別人,可能是比寫詩更有詩意。」與其寫詩,她更在意讓生活有詩意。即使生活空白、零碎,對她來說屬於同種重量,不特別追求什麼,不帶有目的性。像是劇場導演彼得.布魯克所說的「空的空間」,讓任何東西進入、碰撞,走到另一個地方,又是全新的。
「文字是唯一可以跟世界對話的方式。」寫詩讓她覺得生命被理解、被打開了,「情感濃度很強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不見了,我會變成它,用它的方式去想像,可以變成任何東西,去想像各種感覺。」一邊追求藝術性、一邊追求直覺,紀錄某種生命狀態,紀錄已經過去的濃烈時刻。「不寫也沒關係,我比較在意自己看不看得見。例如觀察有沒有更敏銳、眼睛有沒有更利,關於逝去的時間,有沒有準確地掌握住。」
吳俞萱寫詩,不為了別人寫,也不特別覺得要給別人看,甚至有點排斥出版。出書是希望讓媽媽知道自己的女兒究竟在做些什麼,化成紙本的形式和重量,能讓長輩安心。在生活中寫詩,用詩意過活,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與步調去生活,吳俞萱說,「我每天都很期待新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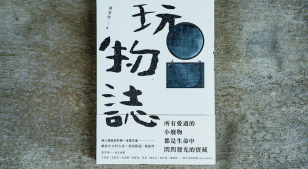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