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聊村上春樹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所謂的「前場」與「後場」。
前場與後場,是布袋戲的用語。戲班中負責在舞台上操演戲偶和口白的人,稱為「前場」。布袋戲尪仔在台上的喜怒哀樂,飛天遁地,都由前場來操持。
而戲班中負責演奏樂器、唱曲的人,統稱「後場」,也稱為「先生」(註)。他們控制節奏與聲音,情緒的轉折與牽引,前奏的預告,轉場,當然還有終結。
以村上先生小說中最愛用的名詞來比擬的話,前場是「意識」,後場是「心」。
▌二元映照的世界觀
優秀的小說家,必須要能把意識與心,也就是前場與後場的分工理解透徹,前場是給讀者的路徑,有說白、有情節,使人能夠理解;而後場則必須處理所有「不能說的」物事。優秀的小說家寫到一個程度,前場與後場的使用越發精熟,它們就不再是固定的表面和裡面了,前場的人可以溜到後場去,後場可以走在前場來。
村上春樹的小說中,向來以虛構和非虛構/真實與想像的世界為探討核心,命題涉及暴力、生死、人的存在意義。早期作品《聽風的歌》、《舞.舞.舞》、《1973年的彈珠玩具》,即可看出村上大量使用空間的隱喻,比如深入地底、比如玩具機台的場域、蒙太奇式的西伯利亞荒原。人物上更是毫不避諱使用雙胞胎的存在、我與我的影子、老鼠和我、烏鴉和卡夫卡來做出映照。村上的世界一直都是雙生的辯證,而雙生辯證便於產生各種投射的可能。例如《海邊的卡夫卡》以虛構世界的弒父來借位了真實世界的弒父,雖然殺戮並不發生在少年的手上,但是血確實染透他身上的衣服。
暴力並不發生在「我」手上,可是血染在我身上。
村上對於人類天生暴力的困惑與反感,形成他特殊的反戰思維。村上作品中一再描寫戰爭,那些歷史久遠的、看似逝去的戰爭,映照著當下正在發生的戰爭;正在發生的暴力複寫已經發生的暴力,無所不在。而恐怖與傷痛都會以其他方式反彈、重新成形,在你暫時看不見的地方作動,然後措手不及地折返回來。村上的二元世界裡沒有高姿態的對錯批判,很可惜的是也沒有正義,這個世界裡真正存在的,只有生與死而已。只有行為與結果,有行為,就會有結果—扣下板機,子彈就會射出;子彈射出,無論飛向何方,終會有一個標的被射中,傷害也一定會發生。這很邏輯,也很簡單。
但,有可能不讓子彈被擊發嗎?不可能。因為傷害早在我們出生之前,在「我」認知這個世界之前就已經發生。人在成長過程中無可迴避傷痛與失落,無可迴避衝突,畢竟,這個世界是眾人共有的,而非為你一人打造的。甚至在《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之中,以這樣的句子直白寫出來:「人類在某些情況下是:只要這個人存在,就足以對某人造成傷害。」
所以怎麼辦呢?那,就打造一個只有我一個人的世界吧,對誰都不會產生傷害,什麼也沒有的世界。那世界裡沒有疫病、沒有入侵的任何變動,只有不變的季節,以及我永遠不想失去的人。
於是,在長篇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1Q84》中,村上則乾脆就建構了兩個世界出來。一個是真實的、主人翁剛開始認知的世界,一個則是主人翁在無意識中創造的心靈世界。在腦海中的黑盒子、意識的暗流之下,有一個冷、以牆構築的城,而那城裡不存在現實世界所有的任何東西(包含時間),卻有你真實人生裡所有已經失去的東西。
天啊,是不是很吸引人?所有的遺憾都在城中被找回,所有的缺憾都在這裡被包容、被原諒,在這裡一切都是合理的。這是人類心理的補償機制,每一個讀者心中,都存在天空高懸兩個月亮的「1Q84」,都有一個飄著冰雪豢養著獨角獸的「城」。在那邊,有一個永遠錯過的人在等著我。那個地方就藏在我們內心深處。非常少年,有點中二,可是你沒辦法否認,自己心裏有那樣一個天真之地。
這樣撫慰人心的世界觀,有沒有被打破的可能?在村上提出《1Q84》、《沒有色彩的多崎作》時,我曾經一度以為,村上此生恐怕沒有機會打破他自己設下的少年魔咒。但是我錯了,他終於交出《城與不確定的牆》。一舉打破他自己的二元世界觀,還讓永不長大的少年成長了。
▌從角色設定看村上如何昇華情感關係,成為大人
村上早期作品另一個特點(且時常被女性讀者詬病)則是少男對於「理想型情人」的投射,這樣的投射是人類認知「愛」的原型。早在柏拉圖的《饗宴》中,就已經提出過極為神妙的比喻—人原本是兩兩成對存在的,男男同體、女女同體、男女同體,後因為太完美驕傲而被神劈分開。於是我們終其一生都在茫茫人海中,找尋自己當初失落的那一半。這種集體潛意識的「自我投射」,是愛的第一個層次,也就是我希望我愛的人「就是我的影子」。這是自戀,人要先學會愛自己,每個人都會走過這一段。台灣作家朱少麟最膾炙人口的小說《傷心咖啡店之歌》,其中的男主角岢海安,就是一個自戀自溺的人。
但,世界上從不存在雙生的我,這只是一種幻覺,是投射,而不是事實(多少身心靈的騙徒打著雙生火焰的口號誘惑人心呀)。事實是:你在構建自己世界的同時,就會與其他人的世界碰撞—受傷、也傷害到人;直到你成為一個成熟的個體。成熟的情感關係則是:「我理解我對你的投射,其實全部都只是我自己的事。而你是一個獨立的、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真正的愛不是讓你成為我的影子,而是因為我愛和我不一樣的你,我願意理解你,與你共同生活、一起成長、一起經歷每個當下。」
於是,有了《城與不確定的牆》。
這部小說既是《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續篇,也是村上過去所有小說的續篇。在這部小說中有各種村上書迷能找到的、似曾相識的舊人物,甚至有死而復生的角色。在這裡,決定要回到真實世界的影子,有了自己的人生,有了新工作和新對象,漸漸轉變為成熟的個體。再也沒有比這一段更為炙熱而誠實的中年愛情告白:「我所求的並不是她的一切。她的一切現在可能無法收進我手頭的小木箱裡。我已經不是十七歲的少年。那時候的我,手上握有全世界的所有時間。但現在不一樣。我手上的時間,那能使用的可能性,變得相當有限。現在的我所求的,是她身上所穿的防禦牆內側存在的安穩的溫暖。還有在那特殊材質圓型罩杯下跳動的心臟,那確實的脈動。」
「那個,對於我一直到了現在才展開的需求來說,是太過微小的東西嗎?或者是過於龐大的東西嗎?」
另一方面,留在那個心之封閉世界的「我」,則終於因為影子的種種際遇,而產生了悸動,「心」動搖了。
心一旦開始變動,牆也就隨之開始變化,牆內一切「我」的投射,也都產生微妙的變化—心動,則風就動、幡亦動,後場音樂已經響起,一切都要改變了。
其中一段,「我」作出決定後,與圖書館的少女說了「再見(さよなら)」,而不是之前說的「明天見(また明日)」的描述,使用了日文中微妙的語氣區別。因為日文中的「再見(さよなら)」是稍微嚴肅的說法,而正式的原型「珍重再會(さようなら)」更隱含有可能不會再相見的離別之意。相較之下,平易口語化的「明天見」則是代表我們的關聯很親近,這僅僅是例行的暫時分開,馬上會再見到對方。少年改變了語氣,終於跟自己心中的理想情人,跟自己永不長大的投射幻想,正式告別了。
要進入真實世界,未知的明天令人恐懼,會不會有人伸出手來接住我呢?會不會有個人像夢中的理想情人那樣無條件地理解並愛我呢?村上先生在小說中,鮮少這樣溫暖直接地寫著:「你的心就像天上飛的鳥一樣,高牆也無法阻礙你的心振翅飛去。……並且你要打從心底相信,你那勇氣可嘉的墜落,會有你的分身在外面的世界穩穩接住你。」
恭喜少年,恭喜烏鴉,恭喜卡夫卡,恭喜多崎作,恭喜阿始,你成年了。
▌小說家的天命—成為夢讀
最後,小說設定中,最令創作者同行為之著迷的,就是讀古夢了。
古夢到底是什麼?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之中,主角一開始讀不懂古夢,且必須先被刺傷眼球,才能獲得夢讀的資格,這一點極為接近於希臘神話中的預言者。或者說,當你原本的視野被打破之後,方能看見那些你以為不存在的事物。而小說中如卵形的古夢,往往操持以「我」聽不懂的異國語言,以過快或過慢的語速、不完整的影像訴說著故事,一邊發出微弱的光亮,夢讀只要一直注視著光亮,直到光消失、古夢說完自己的話為止。一開始,角色「我」以為那些古夢是牆中的人心的殘餘,因為要放棄自己的心,總會留下殘餘的力量、記憶、痕跡,最後,成為了城中的獨立圖書館。(等下,這不就是身心靈常說的宇宙「阿卡西」資料庫嗎?)
心屬於意志(WILL),意識屬於靈魂(SOUL)。生命會消逝,靈魂會消解,記憶會變成破片,語言會成為灰燼,可是,WILL是獨立於一切之外的。WILL比光更快,比原子更小,可以穿越時空,WILL遠在肉身意識與邏輯之上。直到生命告終,直到世界末日,WILL都不會消失,它會以各種方式自由來去。
所以夢讀,就是說書人的職責,也就是小說家的天命:要把那些需要被訴說的、尚未被訴說的,深藏在各種角落的,在歷史深處遭遺忘的故事,重新閱讀並敘說。讓那些未盡之志微弱地發出光芒來。有一天,那光芒將會穿越高牆,傳遞到另一個真實世界去。那些故事裡有真實也有虛構,有怨恨,有原諒,有永不消解的愛,有不存在的時間,有那靜靜落在海面上的雨,有藍莓馬芬蛋糕和小黃瓜三明治。
村上的小說之中,一直以蒙太奇手法穿插各種二戰題材,屠殺與傷痛,毫無意義的大規模死亡。我始終記得村上在《邊境.近境》這本旅行遊記之中,寫下一起親身經歷的超自然事件:村上在古戰場地上撿了一塊金屬片,帶回旅館,放在桌上,猜想那可能是炮管爆炸後殘存的碎片。半夜,本來躺著熟睡的他,突然被狂烈的搖晃震到地上去,站都站不穩。那是比任何地震都巨大的搖晃、巨響。他驚慌失措了許久,才發現,其實並沒有地震,搖晃的是他自己。
那會不會是一次夢讀?村上無意中帶回了一個古夢,而古夢向他述說戰場上炮擊的瞬間,讓人目盲耳聾失去方向感的極端搖晃,比地震更可佈。殺戮的意志,通常,不是出自於按下板機的人。
我在村上的所有作品中不斷讀到同等的搖晃,並且一次一次地,深深理解那樣的搖晃,我的古夢裡可能也有那樣的搖晃,畢竟我出生年離二戰不遠,畢竟我是走過二戰的人所生下的孩子,畢竟,我在這個時空裡活著,共享人類的集體潛意識。
這本小說正式成為我帶進墳墓的愛書前三名,因為我知道:我活在他人的意志之中,我展現自身的意志;我既是前場,也是後場;我既是一世古夢,也終將是某個人的夢讀。
深深地,謝謝村上先生,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大「夢讀」。
註:巧合的是,《城與不確定的牆》裡面,也有一位「子易先生」。
作者簡介
1984年生,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曾獲楊牧詩獎、府城文學獎新詩獎等。著有散文集《玩物誌》;詩集《如蜜帖》、《如廁帖》、《妖獸》、《失語獸》、《負子獸》、《雞卵糕仔雲》等八冊;主編詩選《媽媽+1》;藝術文集《藝術家的一日廚房》;插畫作品有《暗夜的螃蟹》、《虎姑婆》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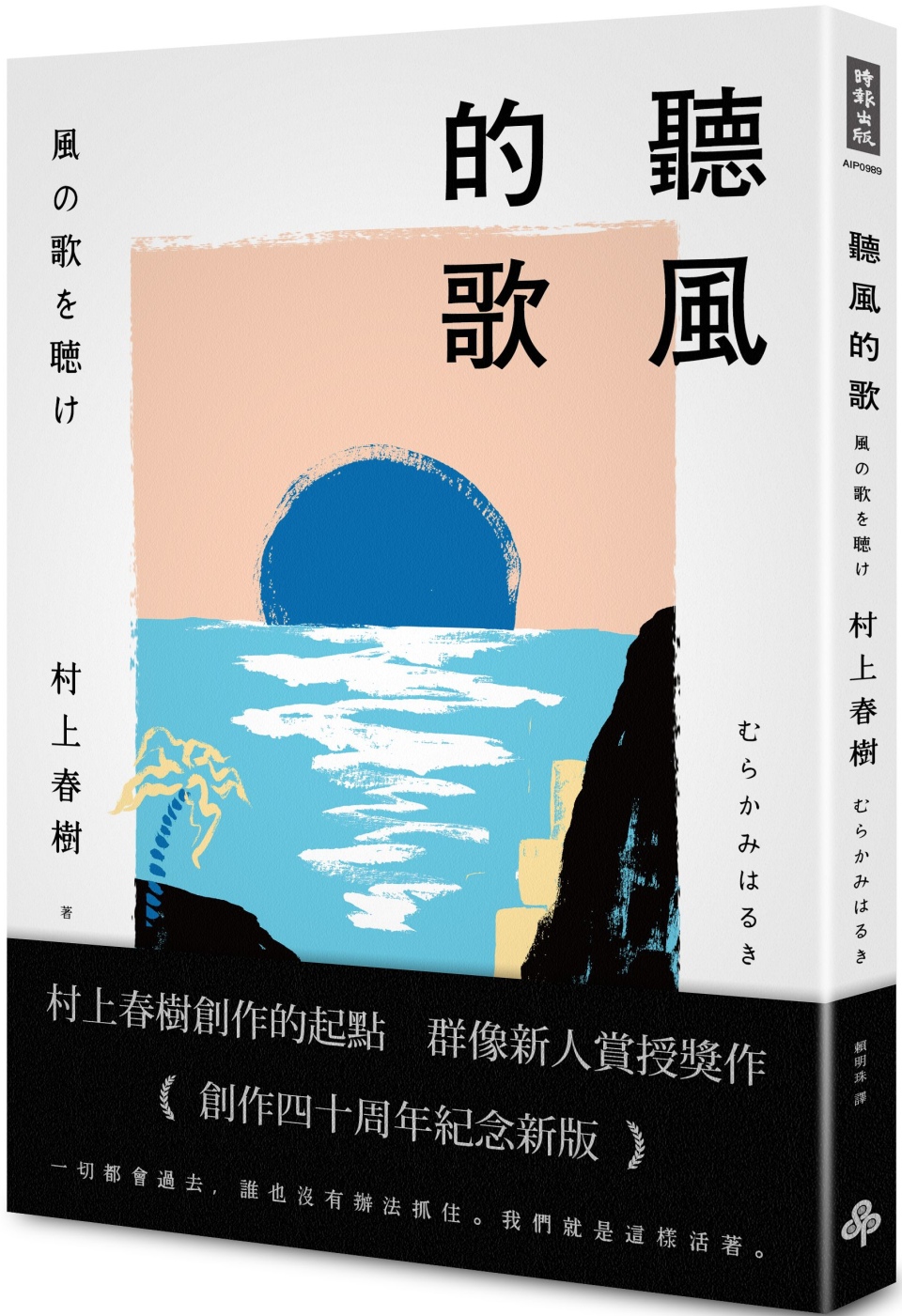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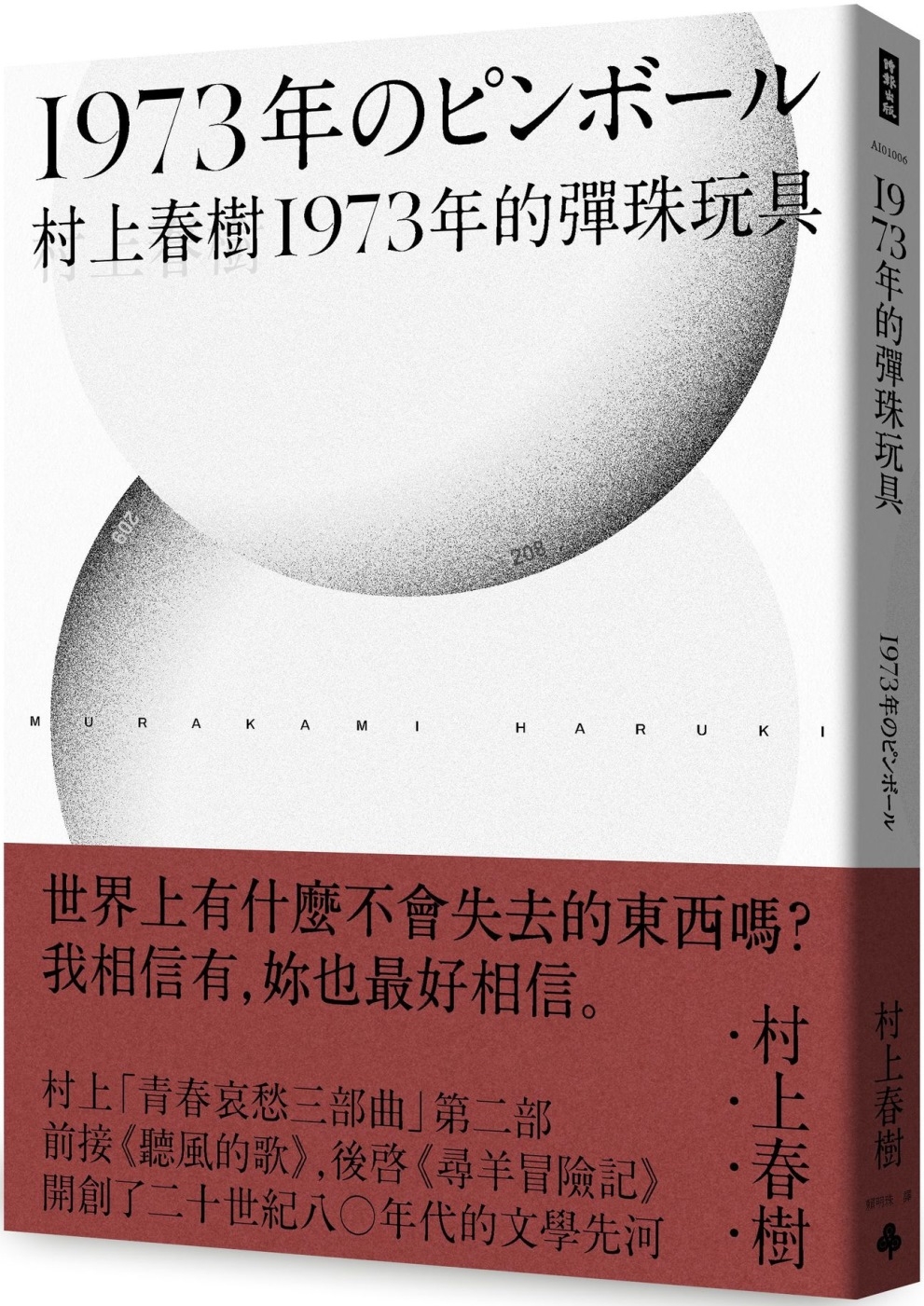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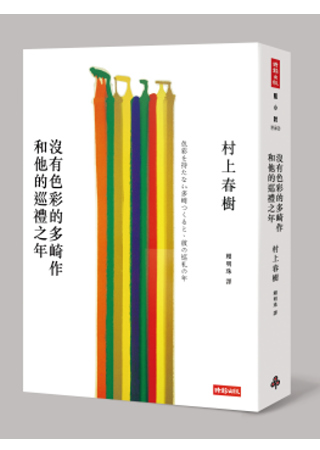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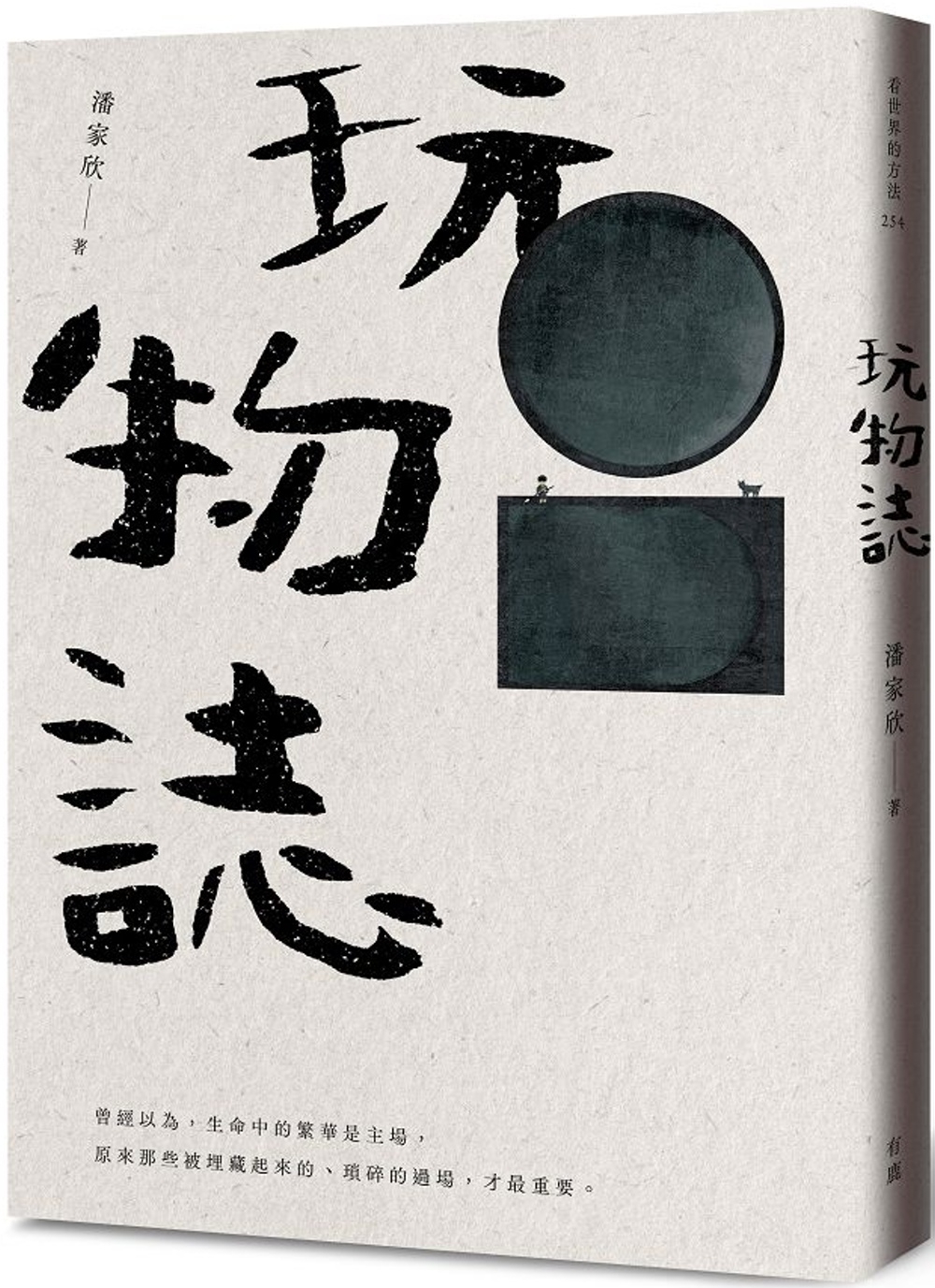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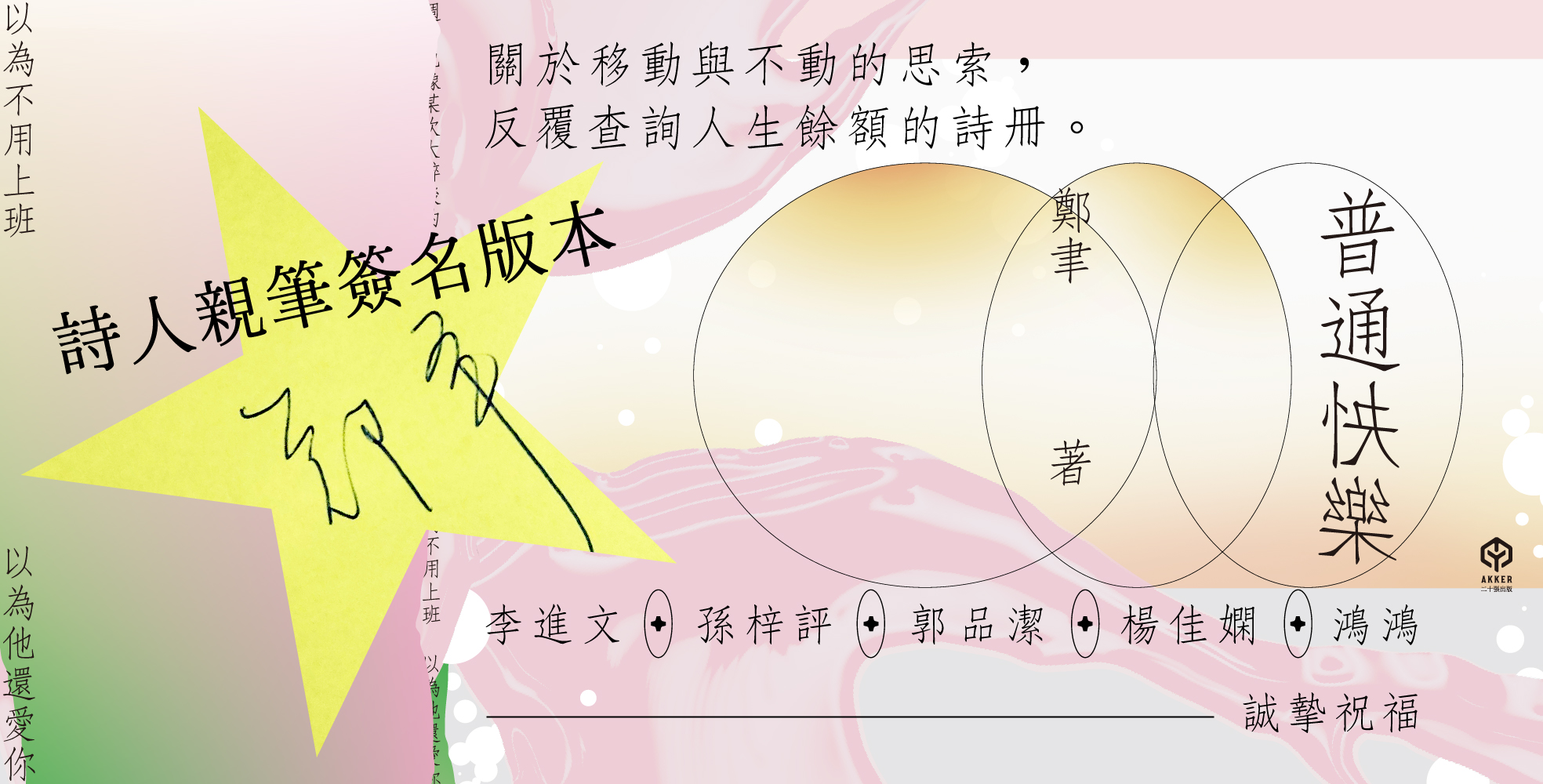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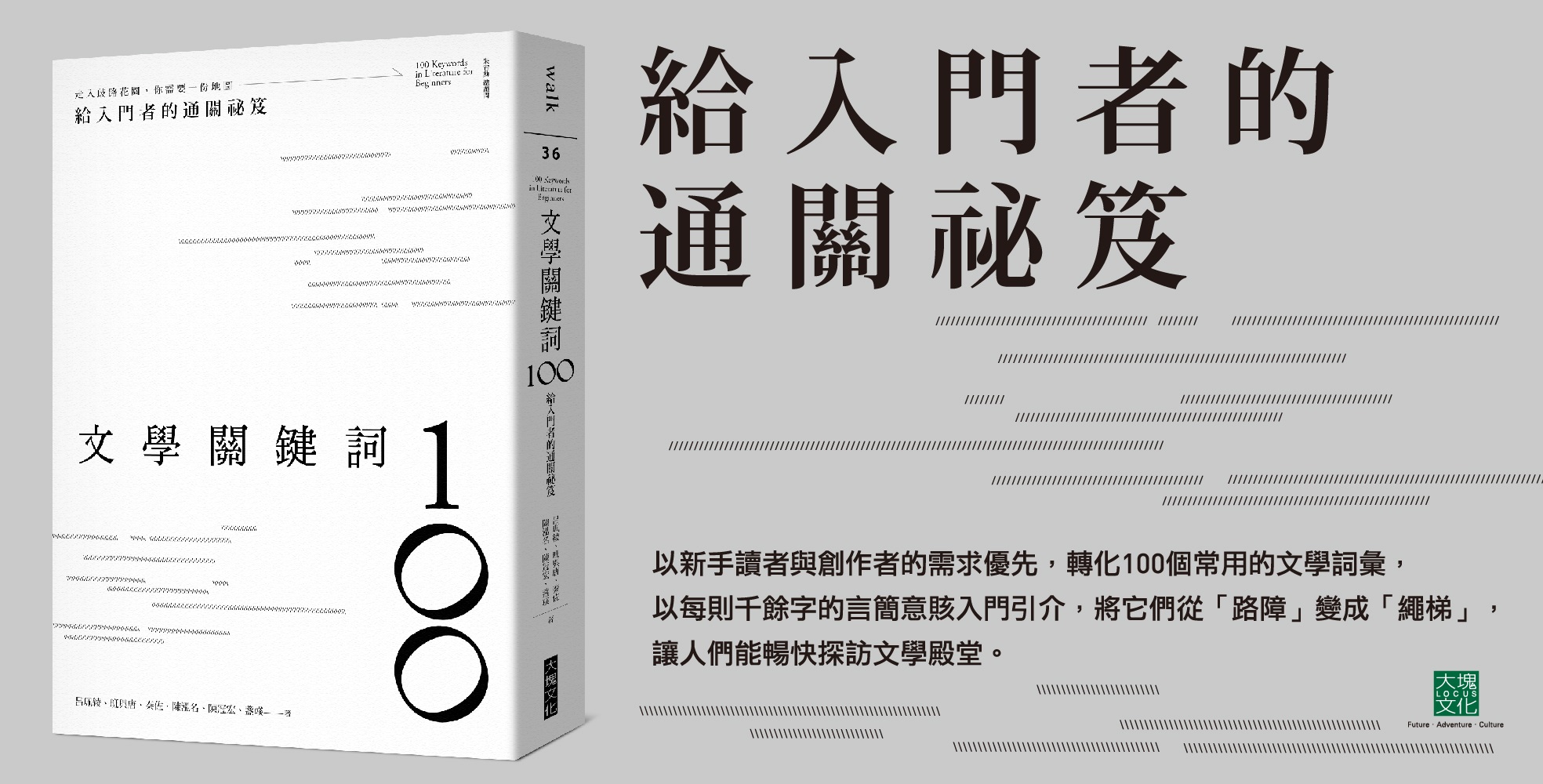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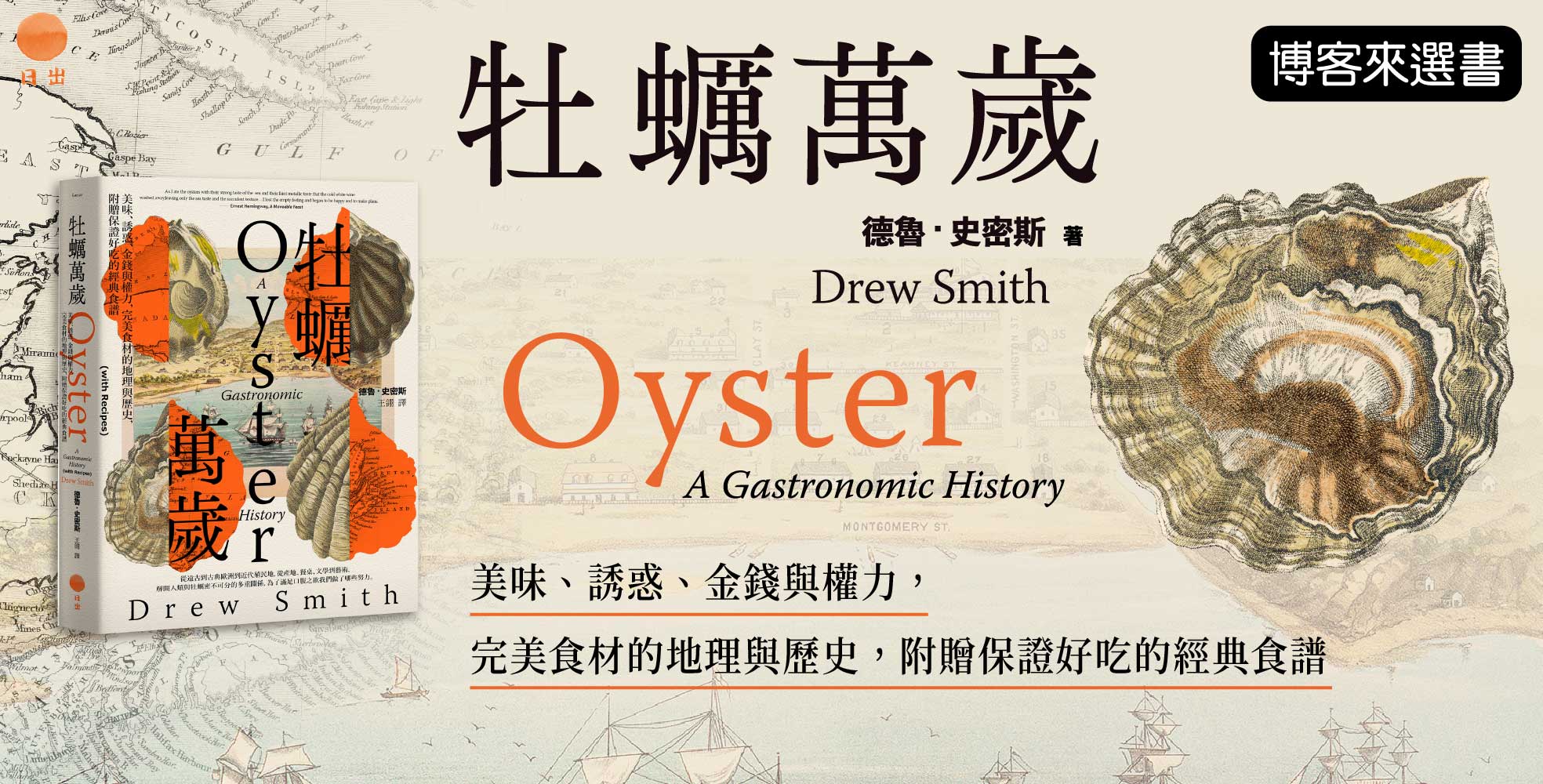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