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年很流行「人設」這個「人物設定」的簡稱,每每出現,後面通常都會跟著一個「崩壞」、「翻車」之類的負面語詞,要嘛是已崩已翻,要嘛是不能崩不能翻,總之,那聽起來就是個必須苦苦守住的假相——而所謂假相,則已經有了欺瞞的前提。
讀〈好孩子的哈欠〉時,我直覺想到的是,如果將它當成一個真實事件在網路上流傳,那麼在留言區中,想必會有不少「人設崩塌」這類自認一針見血的評論。
但我更在意的或許是,在所謂的崩塌之前,一定會先出現的裂痕,是從哪裡開始、如何發生、如何蔓延、又是如何被漠視直至崩塌的;又或許,我們也可以更追根究底一點,去追問這個「人設」是怎麼出現的?
高瀨隼子《好孩子的哈欠》裡,同名篇章就佔了全書三分之二,想來是個累極倦極的綿長哈欠。故事接近尾聲時,藏在句子裡的「我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讓人也打從心底累得無法言語,這強勁的後座力讓我差點就要回絕為這一篇故事寫點什麼的邀請,因為我每一個細胞都能感受到主角內心長期累積的那種累,累得我的哈欠幾乎都要逼出淚水。
故事的前後,都有一個因為「不願意避開走路時盯著手機看的人」而起的事件,兩個事件都來自主角直子的「主動不退讓」——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心理狀態,而且經常只能是心理狀態,他人難以舉證,卻可以輕易評價:「只是這麼點小事,讓一下不就好了嗎?」
而直子的「主動不退讓」,便是來自在此之前,無數的「讓一下」,也正是這每一次都落在自己頭上的「讓一下不就好了」,讓原本只是輕微裂開的淡痕擴張成故事最末的事件,以及直子心中如黑洞般的「累」。
我甚至還可以延伸想像得到,如果直子將她之所以那麼疲倦的原因說出口,那麼「讓一下不就好了」就會變成「不想讓就不要讓啊,又沒人逼你」。那是完全反方向的話語,卻擁有相同的「理所當然」本質。
這兩種理所當然都極為常見,而且經常來自同一類型的人,強大的資格感宛如盔甲包覆著他們,堅信自己無論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說出什麼樣的評論,都絕對不會錯。也正是這種類型的人,會在走路時盯著自己的手機,就像直子所言「他說不定都不知道別人有在讓路」,即使察覺到了前方好像有人,也篤定地認為對方會自動「讓一下」,因此自己只要繼續我行我素便能「就好了」。
「讓一下」與「就好了」分別落在擦肩而過的兩人身上,直到有人——通常是「讓一下」的那個人——意識到了這兩者中間有個兩面解釋的「不」字。
有的人一輩子都稱不上是壞人,但光是如此,就能讓想要對人好的那些人很累,非常、非常累。
讓一下不就好了?那麼為什麼不是他讓呢?為什麼總是我讓呢?如果我不讓了,就不好了嗎?誰會不好呢?我反正已經讓得夠多次讓得夠不舒服了,那麼別人不舒服一次又怎麼樣?
對於當代性別框架稍有理解的讀者,一定能夠輕易地察覺,在好孩子的養成中,性別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男孩被教導成「要去爭取」,女孩被教導成「要識大體」,就如同直子從小就被教導成某種內建「讓一下」的模樣,她是在下意識便採取退讓的無數次經驗之後,才似有若無地察覺到自己受夠了這件事,並且同時對此懷有罪惡感——「在避開對方的瞬間,我仍然覺得自己很假⋯⋯我希望成為一個總是以同樣的規則、同樣的尺度面對這個世界的人,但我做不到。」
直子發現了這個社會從她小時候就硬塞給她的那個人設,並且在遵循人設的同時,因為無法做到表裡如一而「覺得自己很假」,先其他人一步指責自己人設崩塌。讀到這裡,我好心疼,高瀨隼子筆下細膩穿過許多結構性思考直抵疲憊核心的描述,也同時喚醒了我長期以來為了成為「社會塞給我的那個人設」而努力壓抑的倦怠。
很難說這種體悟到底讓我感覺比較平衡還是加倍鬱悶,就像是這回讀了高瀨隼子的小說一樣——我很高興世界上有人寫出了深藏在結構裡那個令人不適的點,然而世界畢竟還沒有進步到我們指出了那個癥結,癥結就能被妥善解開的地步。
我決定先從小小的事情開始練習,比方說,下一次在「讓一下不就好了」之前,我要多想一下,在「讓一下」和「就好了」之間的那個「不」,有沒有其他可能?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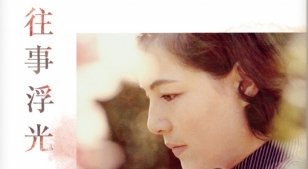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