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藥物價格上漲時,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特別是那些購買高免賠額保險或無保險的人,以及自付費用較高的人。」──美國醫療保健公司GoodRx
川普中槍、賀錦麗接棒出征……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地激戰中,而兩年前由現任總統拜登簽字生效的重大法案《2022年降低通膨法》,也在2024年8月有了重大成果。歷經一連串官司與爭吵,製藥公司們同意降低法案中要求的10種暢銷藥物價格,將於2026年正式降價。這是美國醫療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為藥價進行談判,並取得勝利,極具歷史意義。
平常享有全民健保福利的台灣人,若在美國就醫、吃藥,往往會被帳單嚇得瞠目結舌。2023年有位醫師受傷在阿拉斯加看了一次急診,沒投保的話要花費41萬台幣。《我失敗的美式生活》作者鱸魚是在美國定居的前矽谷工程師,也說太太肚痛住一晚急診後,即使保險給付90%,剩下的自付額仍要台幣9萬元,因此結論是「在美國我不敢生病,而且不到奄奄一息絕對不敢看急診。」
放眼全世界,美國的醫療支出是已開發國家中最高,2020年的總支出是4.1兆美元,吃掉了GDP的19.7%。雖然盤根錯節在整個體系中的問題很多,但最大的根源或許仍在於製藥公司訂出的高藥價。同一種藥,在美國比其他富有國家至少高上三倍,對庶民的經濟造成嚴重衝擊。為什麼出現如此荒謬的現象?《泰晤士報》調查記者比利・肯伯(Billy Kenber)長年採訪醫療、健保相關人士,在2022年推出《藥命之財:揭露全球製藥產業的漫天藥價與骯髒手法》揭發這個行業令人震驚的種種醜惡行為,入選該年世界閱讀日「促進全球正義的10大好書」,備受好評。
進入正題前,我們需要先對製藥產業有基礎認識。現代製藥產業起源自被稱為第一種「靈丹妙藥」(wonder drug)的盤尼西林問世,20世紀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死傷與經濟復興,推動了醫藥發展。抗生素結合有機化學的進步,人們積極擷取物質純化為藥物。50年代進入製藥研發的黃金期,當時的製藥公司洋溢著社會使命感。默克製藥(Merck)總裁喬治.默克(1894-1957)的名言是:「我們應該記住,醫藥是給所有人的,醫藥不是為了利潤。利潤是隨後而來的成果。」為了拯救所有患者,為所有疾病付出努力的製藥業,獲得社會的尊敬。
二戰後的製藥公司逐漸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研究為導向,專注開發新型藥物,自己訂定價格,在專利保護期限內賺取獨家銷售利益;另一種就是「學名藥」製造廠,學名藥又稱通用藥或非專利藥,根據無專利藥物配方的仿製品,劑量與療效相似,薄利多銷。國人常吃的止痛藥「普拿疼」就是原廠藥名,至今費用仍比同級學名藥貴2-3倍。便宜的學名藥讓更多人負擔得起,是理想的互補機制;然而,現代學名藥之於原廠藥的制衡力道益發薄弱,接下來,筆者整理《藥命之財》中幾個焦點案例,來解釋什麼半世紀以來,科技菁英淪為賣藥郎中,逐漸讓整體藥價失衡?
一、不開發新藥,而是買舊藥翻倍賣
因為聲名狼藉,現已改名的康格迪亞製藥(Concordia)有限公司,由一名前律師湯普森在2012年成立,他說,製藥產業最大的兩個風險是R&D(研究與開發),而他兩種都不做,因為他發現「舊藥的利益」──這些藥不流行,但有療效,仍有醫師和病患支持,於是他大量買下小型公司的舊藥後漲價。以1930年開始銷售的「腸賴泰」為例,2011年一瓶43美元,三年後變成393美元。康格迪亞收購此藥後,又再提高三倍。2019年十月,本書受訪者、工人凱希爾的恐懼成真了,腸賴泰不再是保險給付藥物,她已負擔不起這個對自身體質最有效的藥片,而腸賴泰的固定使用者有數千人。多倫多基金公司評論,康格迪亞的行為就是「套利,反覆進行,直到發大財」,藉由同樣手法,湯普森開公司不到三年,就擁有高達兩億美元的股份,年收近九百萬美元。
二、拿政府補助開發新藥,卻賣高昂藥價
伯洛夫.惠康公司的「齊夫多定」之亂,是現代製藥公司與病患、政府的一次激烈戰爭。愛滋病在80年代捲起公共衛生風暴,由於情況嚴峻,在政府與科學家努力下,讓第一種能夠有效治療愛滋病的「齊夫多定」(zidovudine)不用等待八至十二年的安全實驗,在兩年半內獲准上市。1987年推出後,每瓶100顆藥丸的價格為188美元,病患一年要花一萬美元藥費,是分析師當時最高估價的兩倍,成為歷史上定價最高的處方藥。
惠康執行長被傳喚到國會參加聽證會,惠康公司也被憤怒的患者團體包圍抗議,但他們依然「不對價格感到內疚」。美國政府聘請的律師甚至研究1910年的一條法律,嘗試推翻惠康的專利,讓藥物授權給其他公司。直到2001年底,在各方強烈反彈下,惠康終於將此藥的劑量減半並降價,費用為一年三千美金。根據參與聽證會的經濟學家研究證詞,即使是不需要服用齊夫多定的一般納稅人,也足足為齊夫多定付了五次錢:兩個階段的學者研究、國家衛生院的支出、孤兒藥物法案的減稅、醫療補助緊急法案(90年代由政府執行,替貧困、沒有保險的民眾支付)。如果沒有公部門先投入資源,惠康根本不會有成果,而惠康執行長在公開信中表示,國家單位在開發此藥時「只是稍微幫忙」。可怕的是,惠康只是開了一個先例,往後這種「全民買單,藥廠獨拿」的問題,仍不斷上演。
三、新投入的生物科技公司,破壞產業的道德規範
雖然有些公司會採取離譜的定價,但傳統製藥產業仍注重社會契約:平衡私人利潤和公共利益,惠康名聲敗壞的事件也警惕他們不要做得太過分,有一套定價與比價的公式。然而,科學的進步卻改變了產業文化,生物科技公司以全新的技術創造新藥,他們沒有需要保護的品牌名譽,不明白也不打算遵傳統製藥業的規範,於是藥價開始突破天際。1991年,治療罕病第一型高雪氏症(患者食慾減退、肚子膨脹、肝脾腫大、貧血)的藥物「賽瑞戴斯」,每位病患平均要付十五萬美金,一年內就為健贊公司創造一億美元收益,而開發此藥時有政府資助,他們付出的成本不到三千萬。
即便定價誇張,健贊公司卻不像四年前的惠康一樣被砲轟,因為罕疾病患太少,不像愛滋病友可以組成示威團體,得以遠離媒體焦點。生物科技公司的成功,讓製藥公司發現自己過去懶得甩的孤兒藥物其實具有龐大的經濟潛力。「孤兒藥物」通常指對罕病有效、但市場太小,製藥業沒有利益不願製造。於是美國在1983年通過《孤兒藥法案》,以減稅、加長專利獨佔、研究補貼等優惠,鼓勵製藥公司投入研發,卻很快地被濫用。而健贊的得逞,也讓製藥公司們有樣學樣,這種惡性循環導致往後無論是新藥舊藥都不斷抬價再抬價。

行銷人在乎的不再是開發耗時、投資報酬無法預期的新藥,而是要求研究人員專注在每間製藥公司已經建立完成「商業行銷網」之中的新藥,也就是已經擁有暢銷藥物的治療領域,開發這些暢銷藥稍微改良後的新藥,賣給同一群病患就好。90年代末以後,新型的「同質藥物」一再被開發,但完全無益於改善整體公共衛生水準。
本書作者還指出另一種糟糕的狀況,如今全球每年有數百億的支出用於開發新藥,但最後上市的,真的是我們需要的藥嗎?思覺失調症和失智症的開發幾乎毫無說得出口的成績,而在近五年,基本上2/3的新藥都是治療罕病的孤兒藥,或者癌症用藥,因為它們能訂出高價。在製藥公司的短視近利下,理應廣泛治療更多疾病的科學,被自私地限縮在少數真正需求的人,並壓榨著所有的健保資金。如此作法也讓人付出慘痛代價—新冠肺炎。
由於開發疫苗比一般藥物花費更高,大眾對於疫苗失敗的容忍度也比新藥更低,因此製藥公司投入疫苗的心力微乎其微。在武漢出現病例的一年前,大型製藥公司們對於早知其名的「冠狀病毒」沒有任何研究中的計畫。如果不是最後各國政府緊急投入上百億的資助與採買,BNT與莫德納等疫苗不會問世。然而就算人人對COVID-19心有餘悸,至今世界衛生組織清單上至少有16種沒有明確治療方式的病原體還在全球肆虐,其中10種尚未列入任何研究計畫,而下一波全球疫情隨時可能到來,這就是我們付出巨大醫藥費用的真相。
美國病態的藥價最具代表性的是胰島素,一般國家的糖尿病患一年的自付額是100美元,而美國是6000美元,導致美國病患必須從加拿大偷渡大量胰島素。高藥價的影響早已擴及全球,很多藥廠如果對他國政府的強硬議價不滿,往往選擇不給藥不合作,因為在美國境內的收入就已經十分可觀,不需要自己打壞價格。台灣今年底有兩款知名原廠藥:抗憂鬱症的「百憂解」和降血壓藥「安普諾維」要退出台灣,就是不願接受我國健保的藥物價格。雖然上述二藥已有替代學名藥,但有藥師指出,成分並非完全相同,有過敏可能的患者仍有使用原廠藥的需求。過高的藥價,讓台灣人有健保也難以使用到許多藥物,同樣受害。
過去因為定價系統複雜且晦暗不明,也因龐大的獻金和政治影響力,美國政客始終未能有效遏止藥價,幸好在新冠疫情期間,已經開出改革的第一槍。製藥公司絕非永遠都能為所欲為,康格迪亞和湯普森這類無良投機客,往往曇花一現後倒台並官司纏身;醫師們可以把價格離譜的藥物排除在處方籤之外、保險公司也能拒絕申請給付,當該藥有行無市,製藥公司只能乖乖降回應有的價格,但這需要大眾團結努力。比利・肯伯的《藥命之財》讓我們看見真相,也提供改革建議,例如:修改獨佔的《專利法》、設立公家學名藥製造商、設定已上市藥品的漲價上限等等。醫學驚悚小說在全球都很流行,但擁有深刻研究與出色洞察力的非小說醫學議題書卻很罕見,21世紀的人類一生中很難什麼藥都不吃,藥價爭議與我們切身相關,這本《藥命之財》充實地滿足了所有的問題與答案。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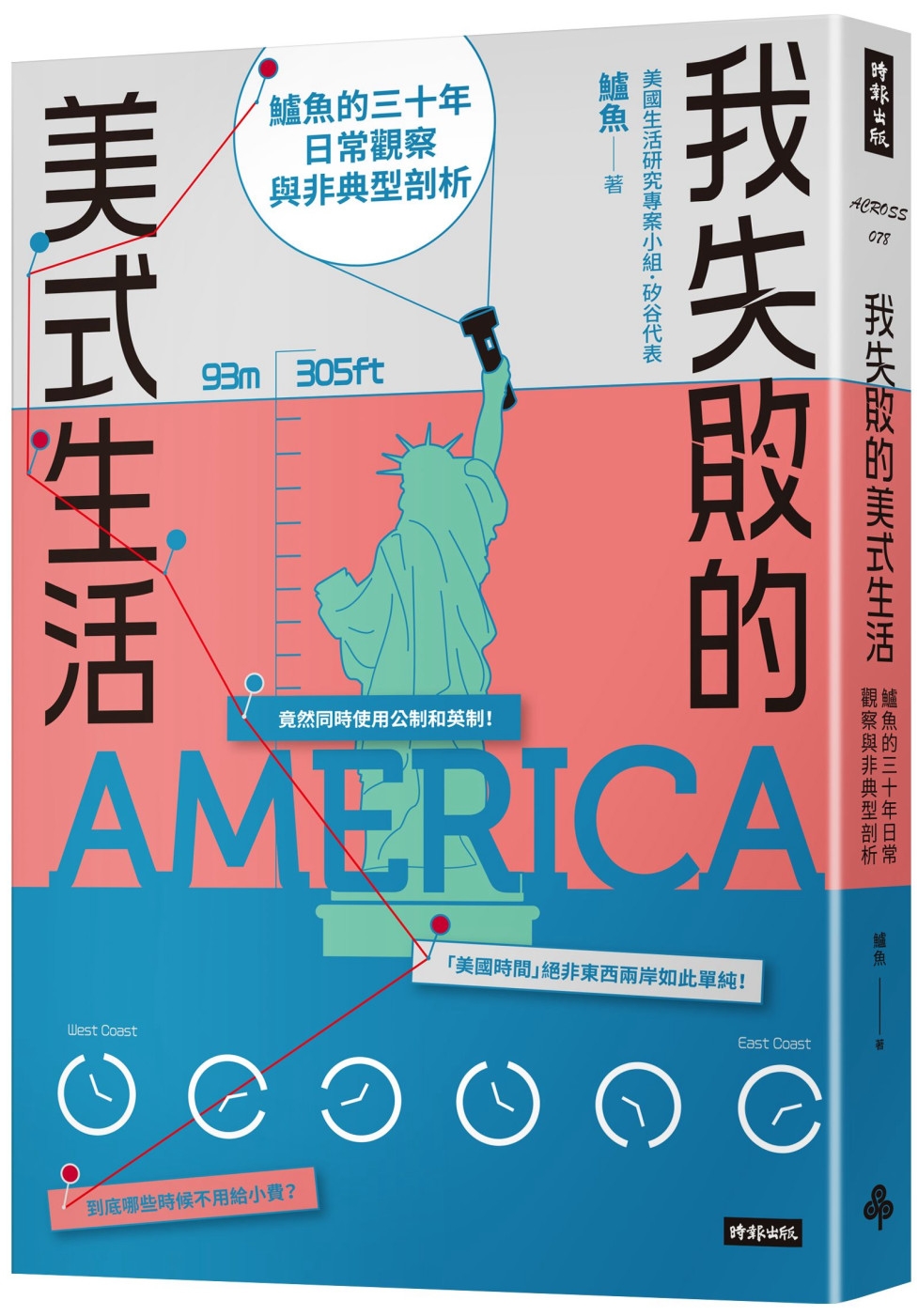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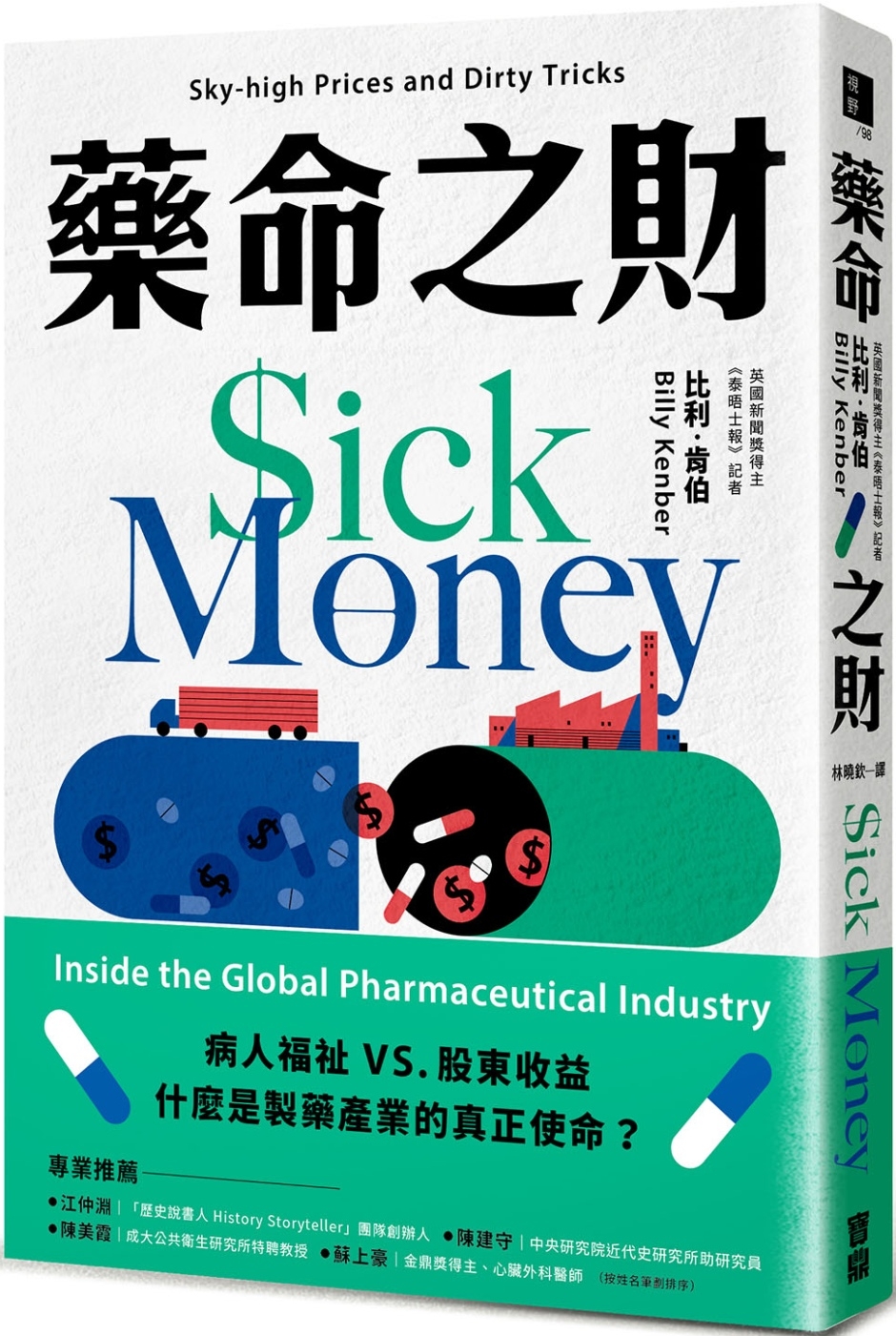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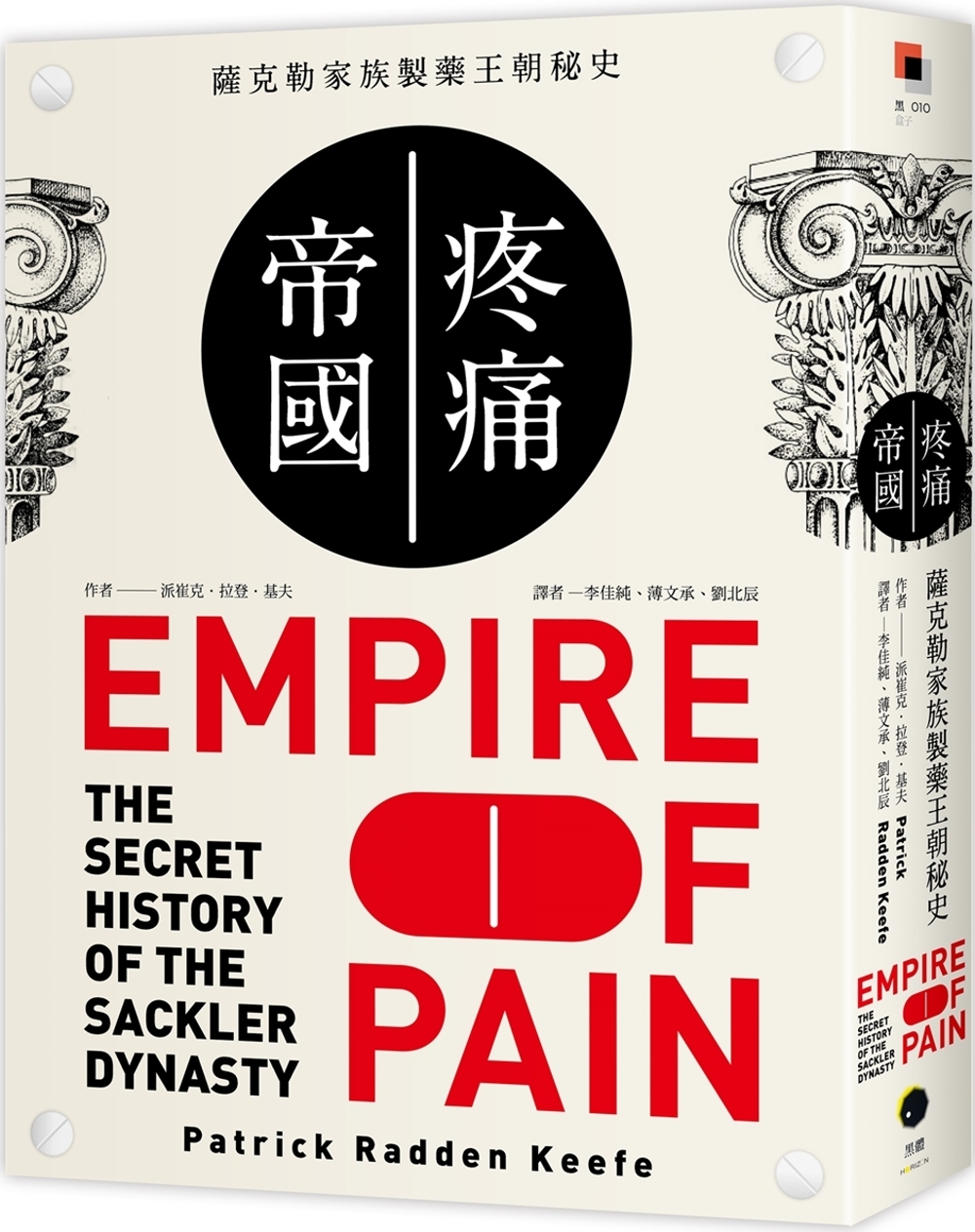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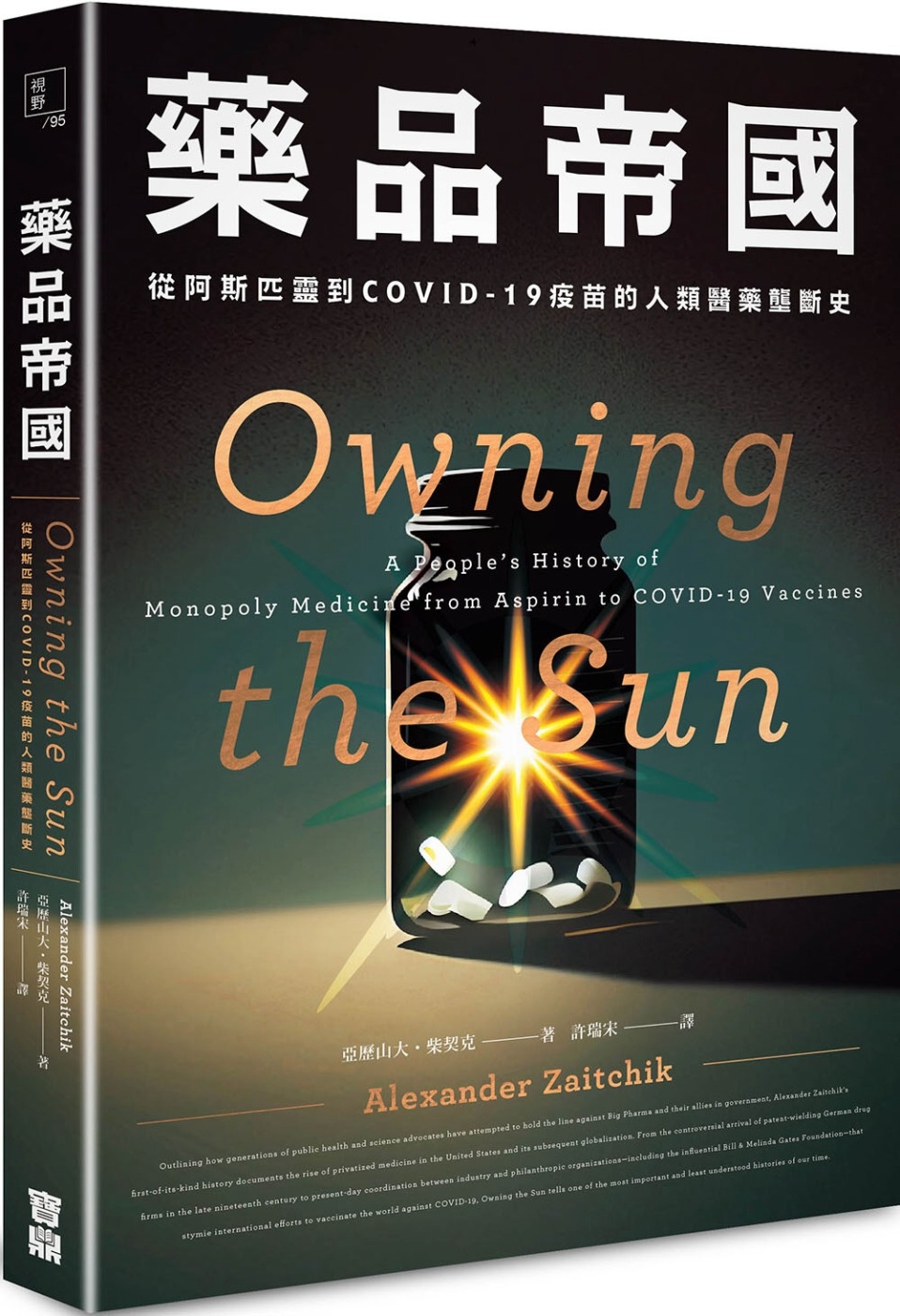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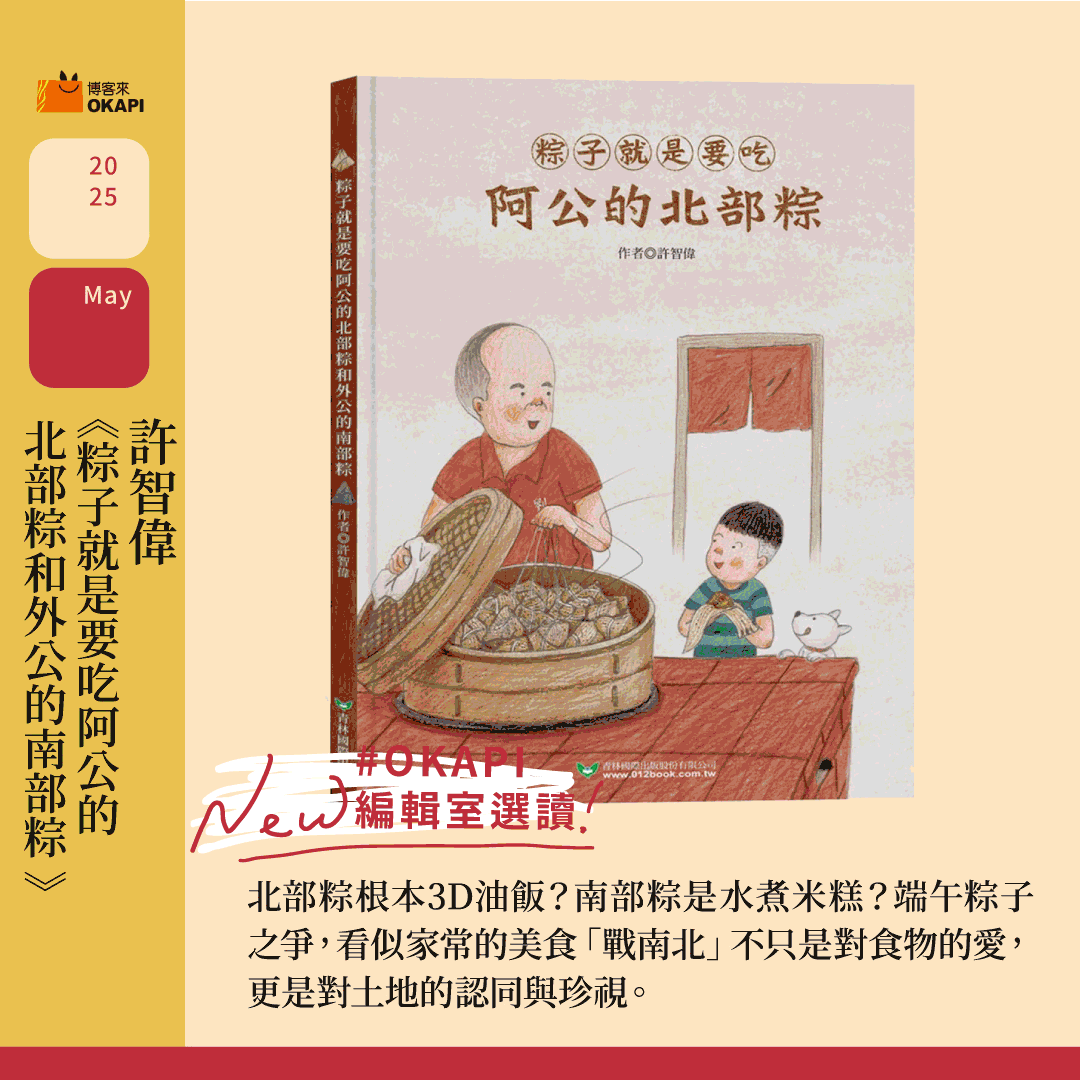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