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我們,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重複做著不完美的事情……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活著的感覺吧!」
──《機動戰士鋼彈SEED DESTINY》(2004)
「反烏托邦」(Dystopia)自20世紀以來是娛樂文化中重要的類型,從小說、電影電視、遊戲到音樂領域無所不包。2000年代後的美國青年文學(YA)在全世界流行熱潮中讓人印象深刻,《飢餓遊戲》系列(2008)、《移動迷宮》系列(2009)、《分歧者》系列(2011)形塑了一整個世代的思想。為什麼反烏托邦小說如此受到年輕族群喜愛?教育學家指出,這個主題很符合青少年的成長需求,提供了一個娛樂平台,讓開始關心社會、道德議題的青少年,得以吸收知識並提出質疑,將故事中的「反體制」帶入到現實世界的觀察。
另外,青少年尚未達到法定成人年齡,各方面必須聽從父母師長的意見,因此故事中的「權威」控制,很容易代入到自身。反烏托邦作品的主角很容易成為崇拜對象,那些勇敢、叛逆的特質,滿足了自己現實中做不到的事情。
反烏托邦並不限於青少年讀物,其題材多采多姿:戰爭、政治制度、氣候變遷、環境汙染、外星人、種族或女性議題,都是數百年來各種文本探討過的,甚至針對「流行病」的前瞻,也在2020年後呼應了新冠疫情。寫得好的作品擁有「預言未來」的價值,以看似誇飾的烏托邦呈現一個最糟糕、最絕望的未來,能夠對我們當前的社會提供警示,避免走向那種最壞的結局。
例如瑪格麗特.愛特伍名作《使女的故事》(1985)闡述強迫生育、禁止墮胎這類壓迫女性而帶來的恐怖,離奇的小說劇情曾令愛特伍飽受保守派批判,卻在摩門教分支 FLDS 統治的封閉社群中真實上演(見 Netflix 紀錄片《乖乖聽話:邪教裡的禱告與服從》(2022))。
「反烏托邦」的興起,最大的關鍵來自西方國家與共產國家的對抗。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世界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俄。共產主義(他們自稱社會主義)的理想為「資源共有、平均分配」,與資本主義追求自由競爭的理念截然相反,在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冷戰期間,「反共」便成為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主軸。前社會主義者、作家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1949)在這段時間被作為宣傳機器、反共先驅。而影響歐威爾寫出這本名作,被歐威爾大力推薦的葉夫根尼.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1920),也因此奠定很高的地位,後來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一起被封為「三大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的英語版發表在1924年,今年是這部經典問世100週年,至今讀來依舊鞭辟入裡,不顯陳腐。
《我們》背景設定在一個結束了「兩百年戰爭」的國家,一千年後,這個國家名為「一體國」(One State),生存空間被「綠牆」包圍保護,與野蠻的外部隔絕。國內所有的建築由透明玻璃製造,人人行動無所遁形。一體國由尊貴的「造福者」(Benefactor)和旗下部隊「觀護人」統治,被稱為「號民」的國民由編號組成,他們以最嚴謹的秩序生活在幸福中。
主角D-503是太空船「整體號」的開發者,他受命前往宇宙征服其他未知生物,為他們戴上「理性之軛」,把造福者這份「毫無瑕疵的幸福」共享出去。但D-503被反叛組織「梅菲」的女主角 I-330 吸引,追隨她的腳步後,逐漸對人生產生疑問與迷惘……
《我們》最經典之處是預見未來體制,很難想像,在薩米爾欽動筆的1920年代,科幻小說始祖 H.G.威爾斯與柯南.道爾筆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仍在活躍。普世觀念仍處於信奉科學、憧憬未來,而這位蘇俄人已經打造出一個比喻極權獨裁的科技國度。那時甚至還沒有「極權主義」這個詞彙。書中角色以歡快語氣歌頌一體國的美好制度,但那些段落讀來卻叫讀者打從心裡發寒:
「自由脫不了犯罪,正如飛車的運動與其速度是息息相關的:速度若是零,飛車就靜止不動;而人的自由若是零,他就不會犯罪,這可是顯而易見的道理。要讓人不去犯罪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不給人自由。而現在,我們才剛剛擺脫了犯罪──」故事中也不乏黑色幽默,例如號民將「火車時刻表」視為遠古流傳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時刻表上的數字完美地劃定了百萬人的作息,在同一秒鐘進行一致的行動;而「全民一致日」是相似於復活節的重要節日,號民們會年復一年將手上的選票投給造福者,選舉只是象徵大家有多團結的行為,他們認為古人的選舉結果不可預知,把國家建立在無法預測的狀況是可笑的盲目……
「手術局的成員是我們最優秀、經驗最豐富的醫師,他們直接聽令於造福者。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工具,其中出類拔萃的是有名的瓦斯鐘,究其根本也就是以前學校的老實驗:把一隻老鼠放到玻璃罐裡,用空氣幫浦慢慢地抽出罐裡的空氣等等。不過瓦斯鐘當然是更為完美的儀器,它使用各式各類的瓦斯,所以瓦斯鐘不再只是用來折磨無助的小動物,而是有一個高貴的目標:保護一體國的安全,換句話說,就是維護百萬人的幸福。大約是在五個世紀之前,手術局剛成立,有些笨蛋把手術局比擬為古代的宗教裁判所,這種類比當然是不倫不類。」
簡而言之,在這個國家只有 We,沒有 I,所有人遵循造福者訂下的規矩。當 I-330率領的反叛派開始掀起波瀾,造福者宣稱他們生病了,這個疾病叫「想像力」。科學局發現,腦中有個部位是引發想像力的中樞,只要用X光就能「治癒」想像力且永不復發。觀護人展開大追捕,最後發展成強制所有號民都須接受腦部手術,內亂一觸即發,夾在其中的D-503何去何從?
《我們》被當時蘇聯的審查機構列為禁書,直到作者逝世50年後(1988年)才在自己的國家出版。歷史學教授菲茨帕特里克指出,俄國革命期間的階級破壞、窮困混亂,讓那時俄羅斯文學的諷刺型相當盛行,而薩米爾欽的諷刺風格更為冷酷、嚴厲,他鄙視吹捧布爾什維克、那些自稱「未來主義者」與「無產階級」的新作家,小說中的「觀護人」是多次找他麻煩的祕密警察組織「契卡」(Cheka),而禿頭形象的「造福者」無疑是參照了契卡的頭子──列寧。小說中的「數字化」生活,直指革命家阿列克謝.加斯特夫(Aleksei Gastev)建立的「中央勞動學院」,這裡培訓工人得像機器一般工作。這部「政治極度不正確」的作品在海外出版後,薩米爾欽迅速成為國內的黑名單,從此四處流亡且飽受同行批判,直到1931年獲准移民。就歷史角度來看他是幸運的,如果持續留在國內,很有可能會在數年後的史達林「大清洗」(1936-1938)中慘遭酷刑喪命。
奇科幻大師娥蘇拉.勒瑰恩稱《我們》是「至今為止最好的科幻小說。」《紐約客》記者瑪莎.格森認為,《我們》不可思議地想像出日後德國納粹的暴行。《我們》與《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作者是親身經歷「烏托邦」殘酷的建造過程,並預見了這種獨裁統治發展到極端的恐怖,將對後世影響深遠。小說中玻璃房屋的全景監控裝置,彷彿預告了現代中國的數位警察系統;控制者藉由腦部切除手術操控人類意志的手段,在後來的經典名著《飛越杜鵑窩》(1962)的精神病院裡重現。或許更令我們佩服的是,在女性地位仍低落的時期,文學中的壯舉通常由男性擔綱,薩米爾欽卻安排由一名女性(I-330)發動革命、來影響盲目的男性,思想可謂前衛大膽。
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我們》當中無所不在的《聖經》意涵,使得D-503的存在意喻天真的亞當,而 I-330 就是主動探索禁忌的夏娃,出「伊甸園」的他們也是對於傳統宗教盲目信仰的批評。但無論後人如何進行哲學上的解讀,《我們》最不容忽略的,或許是那些為人性帶來光明的「愛」。作者雖然將號民編號,但主要角色都是獨立鮮明的個體,孕婦照養孩子的母愛、革命份子努力追求自由的熱情、D-503奮不顧身的戀愛,《我們》是「We」的悲劇,卻探討了各種關於「I」的愛。有別於《一九八四》的灰暗落幕,「綠牆」被短暫破壞,結尾革命的群眾越來越多,也為讀者帶來希望。
薩米爾欽鼓勵他人寫出「有害文學」(勇敢去挑戰、傷害當代價值的文學),雖然在異鄉巴黎抑鬱而終,但《我們》濃縮了這位偉大作家的觀察與期盼。正如他寫的:「今天注定要死,因為昨天死了,因為明天將會誕生。明天使得今天已經看到遙遠山峰的人們不滿,而永恆的不滿是永恆前進、永恆創造的唯一保證。」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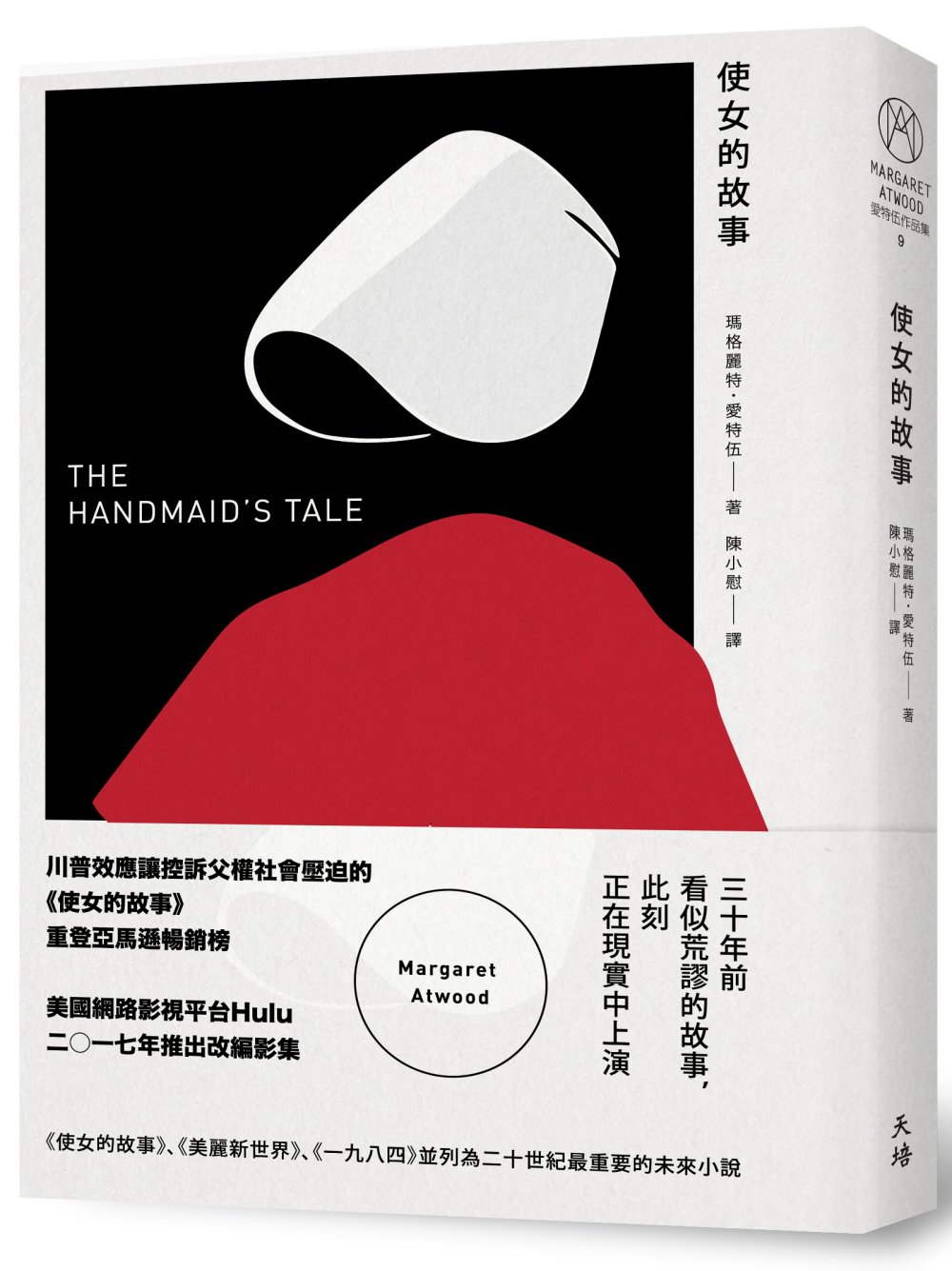
 乖乖聽話:邪教裡的禱告與服從
乖乖聽話:邪教裡的禱告與服從 俄國作家葉夫根尼.薩米爾欽(1884-1937)於1902年起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被捕而流放。1931年移民巴黎直到逝世。
俄國作家葉夫根尼.薩米爾欽(1884-1937)於1902年起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被捕而流放。1931年移民巴黎直到逝世。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