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素有真善美之說。美彷彿是最高境界。再後來,我們知道,美可以是多義的。然而,抵達了美,這一連串關卡就算破完了嗎?又,假若將順序倒轉,先有美,可以反推回去得到善與真嗎?
詩人潘家欣愛美,由收藏可略窺一二。翻開《玩物誌》,玉石、香、刀與珍珠,乃至筆墨紙硯(對老一輩文人雅士而言,這是飯碗兼娛玩),琳琅鋪排,樁樁件件都有講究。入寶山,普通人難免目不暇給,而師大美術系出身的她卻如數家珍,既能細辨志野釉在不同條件下的表情變化,又善繪,練得一手貼箔和金繼的好功夫,不僅物癮滔天,且一頭栽進去至今不見消停。
好東西人人愛,不過,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潘家欣並不擁寶自重,一方面坦承文化資本的累積必須仰賴金錢,另一方面,直言自己粗手粗腳,佩玉每每磕壞,換戴奇楠沉木墜淨化磁場吧,沒想到她將沉香木帶進浴室洗森林浴,簡直揮霍。愛物必先知物──所謂知,少不了要靠大量學識與實作經驗打下基礎──否則就算僥倖弄到了手,也只是徒得其形,談不上玩。
知物以外,還須自知。其實,自知才是最難的。人會隨著境況改變而不斷重新分配財力心力,年歲增長,昔日的心頭好也可能早已拋諸腦後,遑論時間空間有限,如何常保玩的餘興也是個問題。然而,物竟也經常反過來打磨原主,拓寬眼界胸襟,引導人正視自身缺陷和心魔,且在不幸毀損霉爛之際領悟有捨有得,物的來與去,自有一套神祕的質量守恆。是以玩家毋須一味追逐規格高品相精價錢貴的珍品,日常賞玩,合意投緣足矣。
知己知彼,方能免於為物所役的窘境(雖然,唉,這一類窘境在同好間往往被傳為佳話)。後記〈過場是最華麗的返顧〉中,潘家欣自言年少時曾以張岱為師,張岱《陶庵夢憶》:「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以此觀家欣,的確頗多呼應處。這路線恰與今時風行的近藤麻理惠《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形成對比,但人活於世,耽溺總比整理更有福,陳奕迅歌詞說的好,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
凡物皆可玩可戀,執迷反能得道。《玩物誌》明面上談收藏、談癖,實則內裡無一不是關乎藝──癖必須仰賴藝作為支點,藝則藉由癖獲得實踐。彼此互為一體。這是何以來到一切都必須精算的微中年,玩仍然不可或缺。
說句實話,玩向來不太受世俗鼓勵,中年尤其如此。中年的關鍵詞,是責任。職場家務育兒多頭燒,昔日的琴棋書畫詩酒花,隨著文藝女青年嫁人生子,難免變為柴米油鹽醬醋茶。儘管如此,家欣仍勉力擠出時間拉坏燒陶,立志燒滿一萬只茶碗,玩心堅定,令人肅然起敬。但玩不僅止於遊戲,我以為,亦不妨作游於藝解。而游於藝,何嘗不也是一心向藝?從烘豆切入創作的甜蜜點,在棋盤上逼視殺性和好勝心,一物扣一物,其實不斷繞回同一個核心。藝術不僅僅是點綴日常的花邊或糖粉,藝術於她,幾如護身符,護她行走人間而平安無恙。
當然,人身衰朽,遠非物可比擬──物的用與廢,雅與俗,須得歷經重重辯證,不能輕易論斷,而老化是如此有感且不可逆的事啊。此時此刻回望少年時,看什麼都好,流光熠彩,像敷著一層薄薄銀粉;而今,銀粉為現實磨損剝落,露出內裡。內裡不一定好看,可是,內裡使我們真正認清自身質地:是玉,便要受琢磨;是石,便要被砥礪;是蠟,便要忍耐高溫燒灼,人各有體,經歷千錘百鍊,方能成器,顯現出本來面目。一破一立,生命自有其韌性。
屢屢擺盪在微中年的感慨和創作者的進取之間,然後,關關難過關關過,藝術終會引領我們趨近善與真。家欣流連忘返處,在在證明了她作為藝術家的深情與血氣。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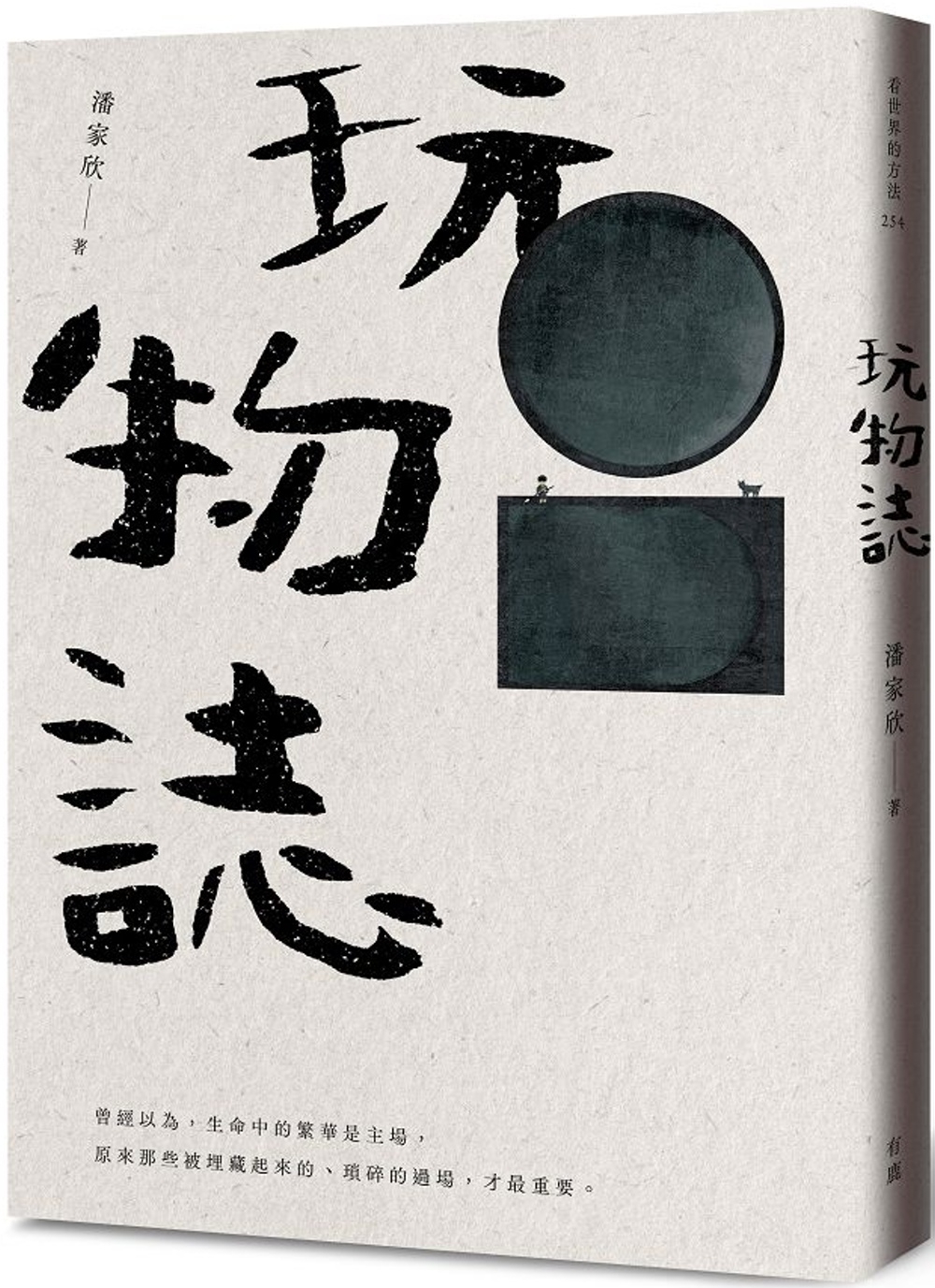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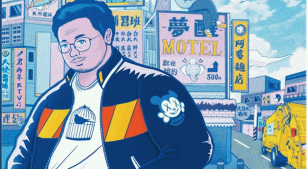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