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時候,翻譯如翻唱,文學譯者的使命是把歌詞唱對,但譯者並非萬用字典,知識難免有漏洞,偶爾會腦洞大開誤判原文,有意無意更會摻加個人詮釋。誤譯還好解決,認錯更正即可,不過,主觀詮釋的底線在哪裡?讀者能不能諒解?
主觀無底線最明顯的例子,是同一首歌的歷年翻唱版。上世紀末,愛爾蘭西城男孩(Westlife)推出翻唱曲〈陽光季節〉(Seasons in the Sun),浪漫悠揚的合聲傳遍歐洲,且容小譯者摘錄超譯如下:
唱到0:36那句「再見了吾友」(Goodbye, my friend)時,團員布萊恩.麥克法登(Brian McFadden)獨唱,還對鏡頭媚眼笑得好陽光。撇開詞義不談,單從這一幕來看,這版本是純情歌無誤。
老一輩歌迷較熟悉的是泰瑞.傑克斯(Terry Jacks)的1973年加拿大版,歌詞相近,同樣一一告別童年死黨、爸爸、女兒蜜雪兒(Michelle),旋律也唯美,隔年至少勇奪10國榜首。但進入千禧年後,加拿大版被CNN讀者票選為史上五大爛歌之一,被嫌曲調媚俗,歌詞過度多愁善感:「再見了吾友,適逢鳥鳴宛轉的春天,實難就此長眠。」此外,穿腦魔音如美國杯子蛋糕甜度破表,膩到味蕾癱瘓,令許多人掩耳急轉台。
甜膩加拿大版的前身一點也不甜。早在1969年英國,運勢樂團(The Fortunes)唱著相同的旋律,卻擺著苦瓜臉,幾度以法文 Adieu 取代 Goodbye,倒數第二段告別愛妻時竟苦笑一聲,唱著:「哈,雖然妳跟我朋友有一腿。」(2:50)但和更早幾年的美國版相比,英國版點到為止,還算仁慈含蓄。
金斯頓三人組(Kingston Trio)的1963年美國版是全球英文版的始祖,「再見」全以法文唱,民謠曲風時快時緩,慢的時候合音甚至近似送葬歌,完全不浪漫,訣別的對象除了爸爸外,好友艾米爾(Émile)、愛妻芳絲瓦茲(Françoise)都是法語人士才有的名字,臨走前更對老婆來個回馬槍:
以 Adieu 道別,人物取法文名,全因這版本是法翻英,譯者洛德.麥庫恩(Rod McKuen)是美國1960年代名詩人,他譜的電影配樂也曾獲奧斯卡獎提名。美國譯版情境大致承襲法文原曲〈臨終男〉(Le Moribond),卡司陣容以父親取代法文版裡的牧師,而且超譯頗多,例如向父親告解自己是個「不肖子」(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以及「但伸手可及的天星,其實是沙灘上的海星」(But the stars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都是美譯版的華麗新創作。
在1961年的法文原曲裡,比利時創作歌手沙克.布黑爾(Jacques Brel)以說書的神態演唱,每一段各含洋蔥。不懂法文的小譯者我綜合網民英譯版,再向《低端人口》譯者陳文瑤求證後得知,法文原曲依序向摯友和牧師訣別,請他們代為照顧遺孀,隨即語調急凍,冷冷對一個名叫安托萬(Antoine)的男子唱:「我剩半口氣,你卻活跳跳,令我恨透……因為我知道姦夫是你,也知道你會照顧我遺孀」,最後是原諒出軌頻繁的愛妻。人物、敘事、情緒鋪陳轉折宛如一則架構緊實的極短篇小說,越唱越激動,「我」即將魂斷春日,難捨難離,情何以堪,但請大家盡情狂歡熱舞,全曲「在我入土後」嘎然劃下休止符。法語人士深諳完整原文版的內涵,當然不屑二創的美國版,當然瞧不起斷章取義、避重就輕的加拿大版,怎能不鄙夷西城男孩唱到「死」字還深情倩笑?
 美國詩人歌手洛德.麥庫恩(1933-2015)。(圖片來源 / wiki)
美國詩人歌手洛德.麥庫恩(1933-2015)。(圖片來源 / wiki)然而,持平而論,翻譯分文藝和非文藝兩大類,文藝翻譯屬於一種創作,文創者都領有一份無形的藝術特許證(artistic license),可擺脫現實的牢籠,可撬開文法的手銬腳鐐。把「如同過往季節」(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翻成「猶如春去秋來的過客」是小譯者詩心大發而起乩,是為押韻而超譯,是以主觀擠壓實境。畢竟文藝非數學,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寬恕豪放妻的原版〈臨終男〉可被變調神譯成陰魂狠話,可轉而被二手三手詮釋為離情依依的〈陽光季節〉。看在特許證的份上,爺爺聽法文歌,媽媽聽加拿大版,女兒聽西城男孩,大家都戴上自己的耳機,各聽各的,用不著逐句比對,讓各家爭鳴,別再死守原版原意,且為譯者留一潭活泉。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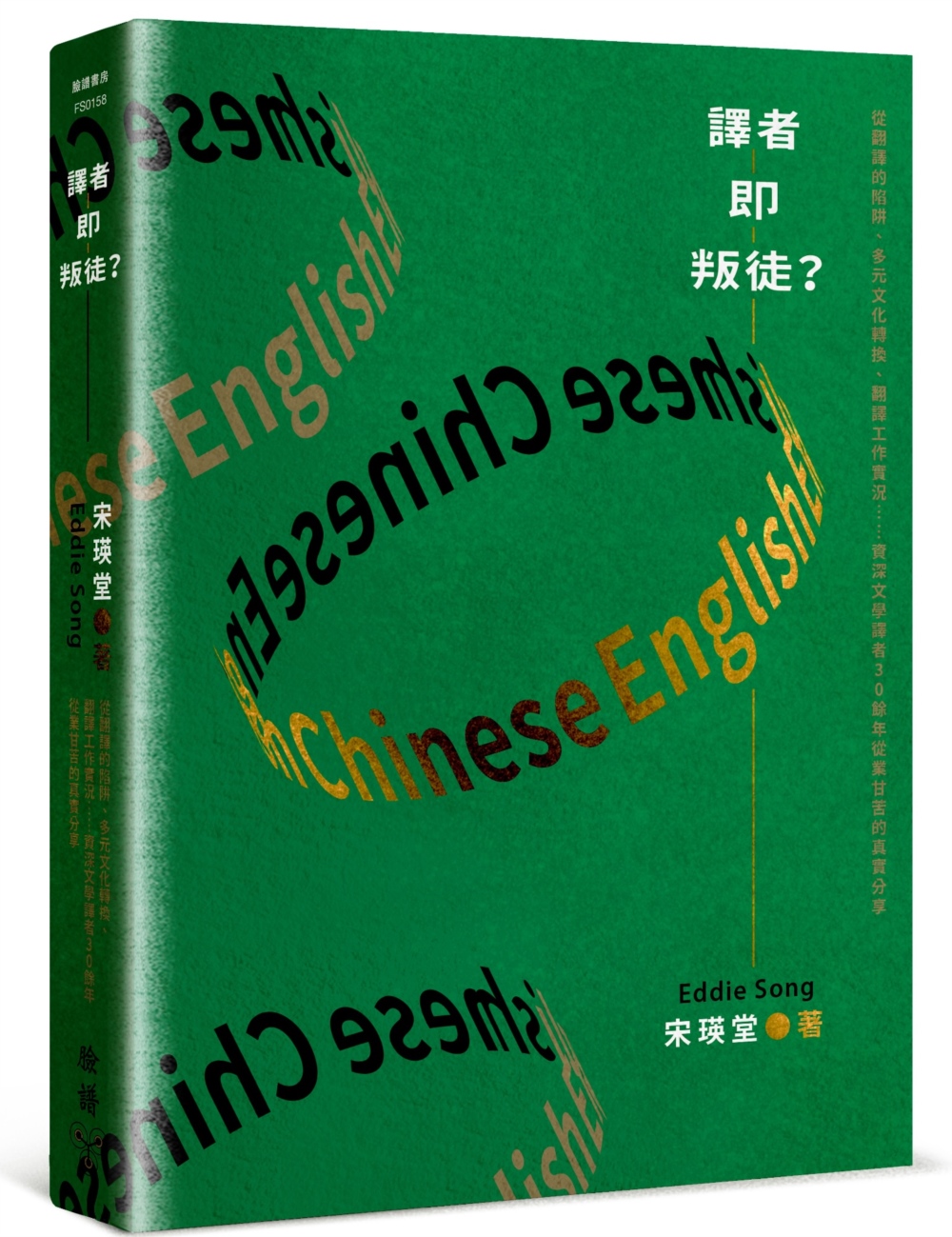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