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泳》收錄的七篇故事,是作家班宇的「昨日世界」,寫下那些被損害的、被侮辱的眾生面貌,呈現出極寒的殘酷現實裡,最後的一絲餘溫。曾經的印刷工人、變電廠工人、麵粉廠廚子、吊車駕駛、流水線工人,一夕之間失去身分與工作,被迫承擔起生計,面對生命的重荷...
陳栢青曾為雙雪濤《飛行家》撰寫推薦語、邀請作家路內參與文學直播節目「作家事」,以俏皮靈動的風格推廣文學著作,吸引眾多年輕讀者。新經典文化原先邀請陳栢青老師掛名推薦《冬泳》繁體版,他透過電郵回覆,表示自己早已購入並讀過簡體版《冬泳》,「很喜歡班宇老師特別的關注角度還有那種冷,能推薦他的著作實在太榮幸了。」我們於是規劃本次筆訪,邀請栢青進一步提問關於從樂評家到小說家的演變、《冬泳》成形歷程,以及小說裡喜劇段子所蘊含的悲涼命運。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擔任過出版社編輯,自2007年起書寫音樂評論和文化專欄,筆名坦克手貝吉塔。2016年開始小說創作,2018年以小說〈逍遙遊〉獲得「收穫文學排行榜」短篇小說首獎,進入大眾視野。同年發表出道作《冬泳》,獲得了嚴肅文學與普羅大眾的關注與認可,隨後入選2018年度《收穫》推薦青年作家、《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GQ》智族2019年度人物、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花地文學榜年度短篇小說作家、第四屆茅盾新人獎等,是目前最受矚目的青年作家之一。
2022年受邀,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進行交流;2023年以文學策劃的角色參與了電視劇《漫長的季節》的製作,為電視劇點綴出一抹濃厚的詩意,帶動了更多讀者對他文學創作的關心。同年,改編自班宇小說的電影《逍遙.遊》榮獲影展肯定,收錄於《冬泳》書中的小說〈槍墓〉也即將改編為電影。
已出版小說作品有《冬泳》、《逍遙遊》、《緩步》等。
陳栢青:第一次注意到你,是因為你過去的筆名「坦克手貝吉塔」。貝吉塔欸,是出自《七龍珠》吧。台灣翻譯「達爾」。賽亞人王子,M字髮線,少年早禿,永遠的男二號,兒子特南克斯一件牛仔短外套穿搭,從九零年代引領潮流界穿搭,妻子布瑪經濟獨立作風強勢,估計達爾在外頭打不贏孫悟空,在家也永遠不會登基成王。取一個筆名,就是發明一次自己,你可以讓自己成為七龍珠裡很多人,但為什麼偏偏轉生成貝吉塔?是一種「就算男二也能逆天改命打倒主人翁」的不認輸?一種搖滾範兒逆襲的叛逆?還是感到貝吉塔身上蒼涼的什麼?
又是什麼讓你出版《冬泳》時決定把名字從孤高的賽亞人王子變回了東北人班宇?
班宇: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漫畫進入國內市場,市面上流傳大量冠名為「海南美術攝影出版社」所發行的漫畫集,最早是《聖鬥士星矢》,每冊一塊九毛,約八十頁左右,分集與日本原版略有不同,風靡一時,銷量極好,不到半年,漲價為二塊二毛錢。其時,《七龍珠》問世,開本大小相近。整個故事很長,出了很多卷也沒有完結,如果說最初對於文學有何啟蒙,也許是每冊《七龍珠》書背上都寫著其他卷冊的名字,諸如:天下第一次武道大會,天下第二次武道大會,未來少年登場,阻止沙魯的陰謀,龍珠又丟了。看完薄薄的一本後,總覺得意猶未盡,而零花錢又很有限,下一冊或另一冊是那麼遙不可及,所以不免去猜想在這些標題之下蘊藏著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故事。《七龍珠》裡,孫悟空父子是主角,貝吉塔與特蘭克斯等,最多算是二號家庭,從那時起,我好像對故事中的主角天然不感冒,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當然,他們的故事足夠精彩,但你總會知道,無論歷經何種磨難,那些主角都會立於不敗之地。反而是那些次要人物,我覺得生動、有趣,乃至會產生一種深深的共情——也許源於我從未認為自己會是任何集體或者命運之中的主角。配角有著更深邃、更真實的部分,他們可以有缺陷,可以犯錯,也可以軟弱,一蹶不振,這令我倍感親切。此外,貝吉塔這個角色有狂妄、孤傲的一面,愛恨分明,也有著非常赤誠的感情,令人沉迷。漫畫裡到了他的那一部分時,忍不住要多讀幾遍。至於改名這件事情,可能我認為「坦克手貝吉塔」還是一個網路代號,用來標記書影音、插科打諢,與我正式書寫的內容有點距離。想要講出我的故事,還以我的真實面貌來敘述為好,從自己出發,所寫更為切實,近於貼身短打,於是換回了本名。
陳栢青:其實不需要你做背景介紹,讀你的《冬泳》可能比任何搖著小旗子的導遊都能更快帶領讀者進入上世紀末東北。裡頭角色們以為捧著國企鐵飯碗,結果遭遇時代的地震,堅不可摧的一切是那麼不經砸就碎了,還特別刺人。《冬泳》裡總是灰撲撲的男人們讓命運打趴又站起來,很硬氣的女人去哪打麻將都堅持披著貂。你是1986出生。《冬泳》裡大人面對時代惘惘的威脅時,你是十幾歲少年。我忽然意識到,這是文學版本的「爸爸去哪裡?」,那其實是你上一代人的視野和經歷,作為你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是什麼讓你把時空間坐標定位在九零年代與東北。是什麼讓你先說起父執輩的故事?
班宇:坦率地說,書寫源自一種不解。我重構當時的地理樣貌,還原生活情景,回憶彼刻的親人與敵人,無非是想讓自己再次陷入那團迷霧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代人的經歷是怎麼樣的,以及人們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進入池水之中的。儘管今天我們有無數的資料,也有相關的報導和影像紀錄,可這些仍舊無法全面、徹底地讓局內人知曉自身何為。我想,這個角度上,文學或許是個補充,這是大的層面。對我自己來說,不過是想弄清來歷,九十年代與東北,這是我最基本的成長時空,一切從此開始,所以我藉以小說之軀殼,以想像與記憶試著將一些情感聯繫起來。寫到後來,小說似乎成了某種本體——比如,它是我寫給父輩的一封封信件,關於罪與愛,深情和仇恨,猜忌與理解,雖然它們已經發表出來,但在心裡,我從未將它們寄出去過。這種另一重真實的矛盾。
陳栢青:以前特別喜歡〈梯形夕陽〉〈工人村〉兩篇,覺得那裡頭每一段落都是小品,像聽二人轉還是相聲。一套一套,每段都有一個哏。我看《脫口秀大會》都要人留意看東北的李雪琴,天生段子手。讀你的小說後覺得那裡頭段子之密集,自帶一整個琴團似的。我不知道上面幾行話在中國是讚美嗎?但在台灣那肯定是,沒人可以像你這樣寫。又短又密集,笑都是抿著,唇角卻帶刀。我極其羨慕你的語言天賦和幽默的能力。你在「豆瓣閱讀徵文大賽」獲得喜劇故事組首獎,我比較想知道,這喜劇感是自帶天賦,還是練出來的?寫段子有什麼秘訣嗎?
班宇:在我看來,幽默是一種至高的讚美。不能說有天賦,但也許跟地域性確實有那麼一點關聯。比如,在東北酒桌上,每個人要怎麼去講話有著一套默認的守則——並非尊卑排序,而是按照發言的精彩程度:一分鐘之內,如果你說的話毫無笑點,或所講的故事略顯平淡,所有人的注意力就會被無情地轉移走了(東北人在短視頻平台很受寵,不知是否也與這種氛圍相關)。所以,我們必須逼迫著自己以最為短促、精煉的語言來表明態度,或者完成一場敘事。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能由於東北人的表達欲與表演欲的確很強,熱衷於模仿和講述,對於度過漫長而寒冷的季節來說,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陳栢青:接上頭的繼續問,你要真刻意,一個人就是一場脫口秀大會。但《冬泳》裡頭真正厲害是,底蘊是悲涼的,東北的黑冰白水,走在上面嘎嘎有聲,前路隨時會裂開,於是情節裡那些黑色幽默的段子,那些笑聲,好像是刻意掩蓋就將沒頂的一切,又好像怎麼都不服輸,要和命運叫板。小說便生出一種魔幻的味道,你寫出一種「比原本的什麼更大的感覺」──那就是生存的底蘊吧。例如〈盤錦豹子〉中,原來東北家裡人出殯要摔盆的,越響越好。於是你寫那已經被生活打倒在地的男人,在父親葬禮上拿出醃鹹菜的罈子,怎麼都摔不破,旁人真急了,跟著嚷,替他急,想助威的恐不只是為破罐子瓦摔,還有他整個人生。那真是非常厲害的小說場景,哭寫得像笑。悲劇和喜劇一罈之隔,是什麼讓你感受到小說該這樣寫?和你對經典的閱讀還是生活遭遇有關?好好寫喜劇不行嗎?
班宇:問題真好。經典也好,喜劇也罷,都是讀者的一次定義。說個感受,我在每一篇小說起筆之時,都有著一種衝動,或可描述為想要寫出「比原本的什麼更大的感覺」,雖時常力有不逮,在有限的空間之內,我還是想觸及更長一點的時間、更廣闊一點的地域、更多一些的人群,也即超出故事範疇的那一部分。對我來說,那是使得小說成為小說的重要環節。我小說裡的人物總是在說話,話趕著話,話連著話,自顧自地說著話,而在話與話的空隙之間,正是我們生活的全部密度。
陳栢青:《冬泳》裡有非常好的人物,是鋼鐵廠鐵漿銅汁澆灌出來,摸得到眼淚的形狀,雖然也是生鐵味的涼。你是從人物想出這些故事來,還是故事兜著兜著有了這些人物?
班宇:還是以故事為主,人物緊隨其後。我一直不太理解一個說法,就是人物是塑造出來的,在我的經驗裡,只有工廠零件是需要塑造的,以特殊的材料加工打磨,需要精確的尺寸和重量。人是一種不斷變動的存在,切實地出現在你面前時,展示為固體,而其精神有如液體,四處奔流,在他轉身離去後,又化作記憶一般的氣態。如何去捕捉這種不確定性,並加以描飾,使之成為可供理解的一部分,也許正是小說的另一重精神宗旨。
陳栢青:你以前是樂評人。成了寫作者。我好奇,你評音樂的時候,最看重是什麼?那現在寫小說,拿來衡量自己作品「有這個就成了」的關鍵是什麼?可否用《冬泳》當例子?那你看別人小說時,又拿什麼來衡量「這是我的菜」?
班宇:〈冬泳〉這一篇確實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典型案例。這篇小說我寫了一段時間,全文的起點,也即咖啡館場景、人與事物,我都很熟悉,地點就在我家樓下,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經常會去,不是寫作,基本在跟朋友閒談。偶爾觀察咖啡店裡的其他顧客,會覺得這個空間已經被東北人進行了一些功能化的改造——不只是喝飲品、談工作、友人小聚之地,同時,也肩負著相親角、錄像廳、輔導教室、寵物寄存處等多種功能。這點很有趣,我想可以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小標誌,至少映射出來一些社會需求。
小說的前半部分很平,我寫著也覺得略有乏味,因為只知道起點,還沒想好到底要說些什麼,寫了一萬五千字,我開始恐慌,因為似乎可以一直這樣寫下去,不過是更加平白的當代場景講述,不存在超越性的部分。於是,我停了幾天,那時是冬季,一次午飯後,窗外開始飄雪,並非大朵大朵的雪花,而是地上席捲起來的冰粒,細如針尖、如灰塵,掃在臉上一陣刺痛,我想到了小說的結尾,即一個人從岸上進入溫暖的水中,再次起身時,已經來到另一座的無人河岸上。這與我目睹的此刻相似,不是美麗的雪花輕盈地覆蓋在大地上,而是一次亡命式的背棄與席捲。之後,我將小說中間的一部分推翻重來,最終形成現在的樣貌。
第二個問題,在閱讀時,小說的語言對我來說可能是比較容易判斷出來的選項,語言也代表著政治、審美與生命力,如果語言是好的,或者至少過得去的,那麼我願意把接下來的時間交付給這位作者。
陳栢青:《冬泳》小說集大熱於2018,之後你又出版了數本小說。台灣在2023年末終於盼來你的第一本繁體小說。這是台北到東北的時差了。昨夜轉開Netflix,你擔任文學策劃的《漫長的季節》也上串流了,冬泳都還沒游到對岸呢,《漫長的季節》我一晚全追完了(還問下一季呢),這也是台灣到班宇的時差。那你自己呢?從小說賣得火熱後,親愛的賽亞人王子變身地球作家,生活有什麼改變?有什麼體悟?
班宇:確有感觸。最深刻的一點是,大家都認為我的生活會有許多改變。每次被問及時,連我自己都有點質疑,是不是我的生活應該發生一些劇烈的變化,但實際上是幾乎沒有。最大的變化之一,出於想要得到更多的閱讀、書寫時間,從原公司離了職,不錯,的確日常會有一些文學活動與採訪之類,不過這些維持的時間也都非常短暫。更多的時刻,我還是自己待著,聽唱片居多,也看看書。所以,我的體悟就是,大家對這一代作者的生活也許存在著一些無法說清的想像與誤解。
陳栢青:對台北有什麼印象?這問題不會問雙雪濤,他說出口我一定秒懂。可你呢?請聊聊你對台灣文學的接受經驗或印象?
班宇:實在談不上特別的印象,也許是一些小吃?畢竟舒國治的《台北小吃札記》還是讀了兩遍。不過我從前是一個重度樂迷,所以看見這個問題時,第一反應是臺灣九十年代的那些樂隊:Double X、濁水溪、廢五金、四分衛、脫拉庫、夾子等,馬世芳先生的節目也聽過很多期,常聽常新。台灣文學的話,最早的閱讀可能是張大春先生的《城邦暴力團》,簡體版發行時,堪稱當年一大文化盛事,幾乎人手一套吧,那已經是2011年了。也是同一年,讀到駱以軍先生的《西夏旅館》,結結實實地沉迷了一陣子,小說的語調實在獨特,那段日子裡,連作夢時都彷彿能聽見其中的聲音,縈繞不止。
陳栢青:我出生台灣中部小鎮,從小一心只想去台北。告訴我,那是什麼心情、什麼讓你留下?成為作家後,東北對你而言又是什麼?你筆下都是東北,你想帶著「東北」去哪裡?
班宇:我小時候非常嚮往北京,作為首都,作為文化的中央,核心之核,對我的吸引力難以言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以幻想著北京地下音樂/文學/電影生活度日,竭力搜集著一切與此相關的書籍、唱片、影像資料。為何一直沒去成呢,原因很簡單,沒錢。家裡過日子都比較吃力,沒有這樣的旅行預算,太過於奢侈了。讀大學時,總算有了點生活費,於是約著朋友一起去了北京,坐了七、八個小時的客車,到達時已經是傍晚了,連忙乘地鐵去「無名高地(當時的一間 livehouse)」看了一場龐克演出,結束後,朋友發了高燒,我們還跑去醫院打了個退燒針,值班大夫睡眼惺忪,很不情願為我們服務。從醫院出來,我們又去喝了個酒,鄰桌女孩一直念著一個電話號碼。當夜沒錢住宿,我們就在速食店待了一夜。快二十年過去了,我與這位朋友也失去了聯繫,我很想念他。從那時起,我去北京比較頻繁,主要是去看樂隊的演出,直到十年前,我有了一種感覺,如吹萬樂隊的一首歌曲所述,「北京在下沉」,下沉的同時也在升起——與此同時,我所在的城市也經歷著劇烈的地殼變化,不久,它們來到了同一水平面上。站在此處或彼處,向著四周看去,平坦與光潔一望無際,那些與生俱來的傷痕統統消失不見了。
東北對我來說,顯然是一個起點,不可避免地,我也要承擔著部分粗暴的誤解。每當有人與我談起小說裡的東北時,我都會產生一種恍惚之感,無論東北還是小說,在這樣的講述裡,似乎都在變形,亟待重塑,而我又是無能為力的。如果說我能將筆下的「東北」帶去什麼地方,我想,或許有點傷感——我的墳墓可以嗎?窮盡了所有的嘲諷與解構,在一次次的背叛與爭辯過後,在全部時間之後的時間,最後的最後,我仍想為之保留一點點的尊嚴。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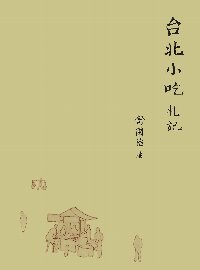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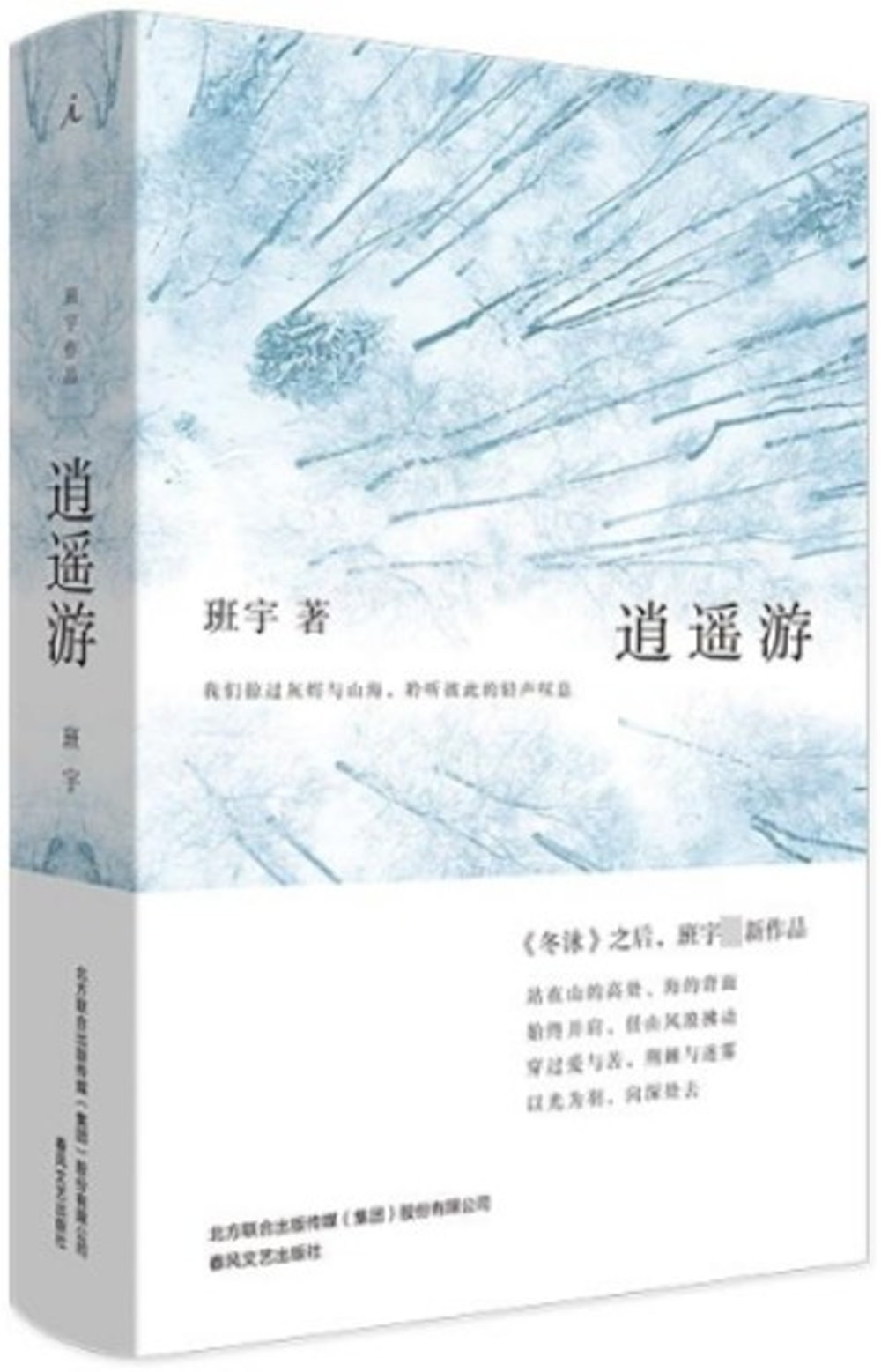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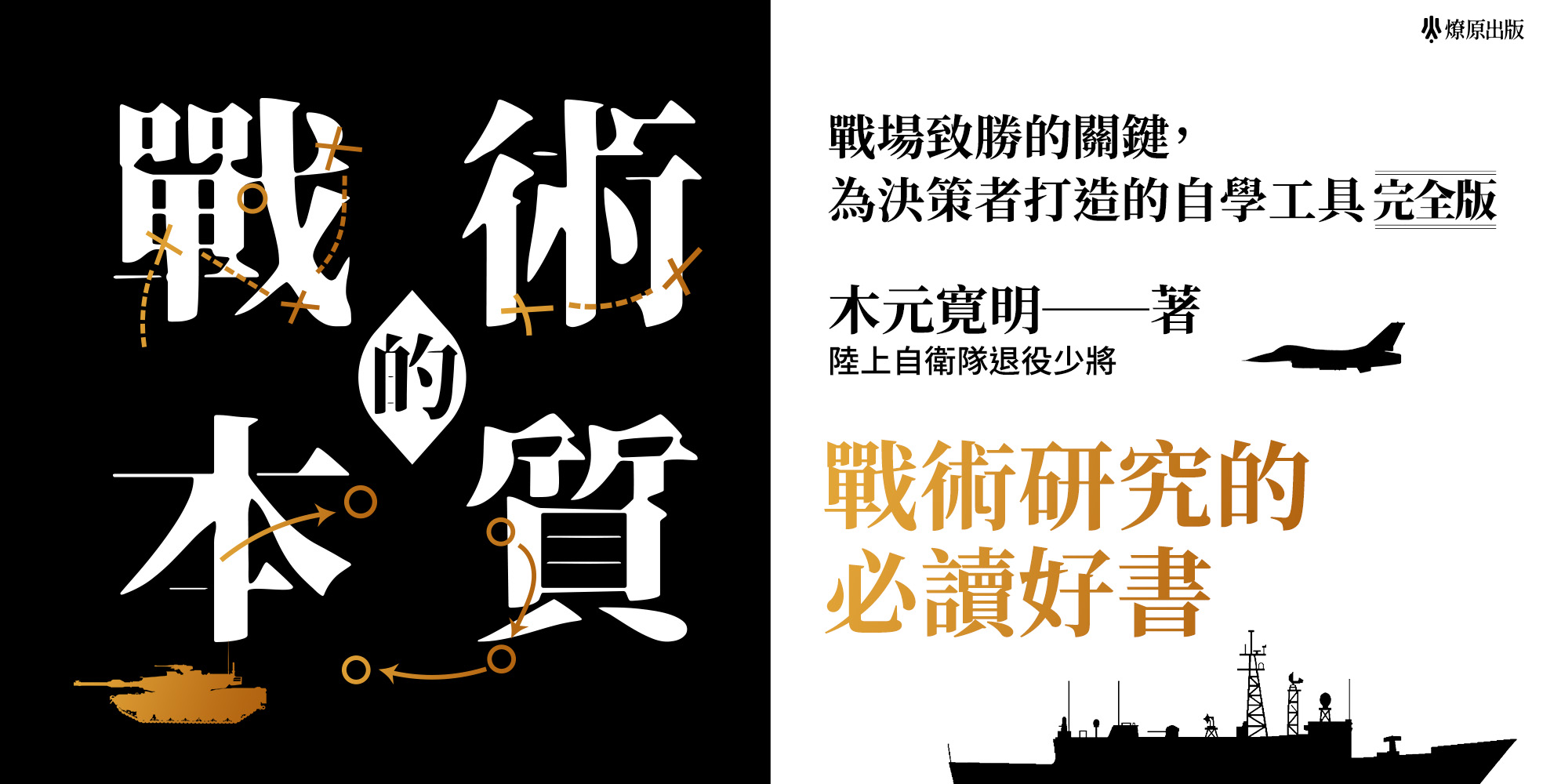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